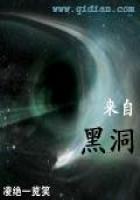“去不去吴城?我非常犹豫。吴城离我父母所在的洛城当时有4个多小时的路程,偏僻落后。我是独生女,妈妈身体一直不大好,我不想离得太远。可是我的父母思想太传统了,他们就盼着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记得爸爸当时劝我,‘去吧,放心,我和你妈还年轻着呢!还能相互照顾呢!’我终于坐上汽车驶出了车站,泪眼模糊地看着搀扶在一起、越来越小的身影。”萧雨的眼睛里一片雾气。
“到单位报到,五十多岁的老何局长特别和蔼可亲,告诉我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何局长的女儿常年在外地工作,他和夫人把我当成了女儿,对我很好,经常叫我到家里吃饭。”
“到吴城的第一个冬至,是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何局长又叫我到他家吃饭。,陈阿姨开了门我才发现房间多了一个人。”萧雨平静的诉说着,说到这里有些伤感。
“他有些瘦、很高,笑容很温暖、很干净。”他们知道,孟晨出场了。顾飞按照萧雨的描述对照上次见过的孟晨,怎么也对不上号。
“他后来说,见到我的第一眼,就认定了我是自己的伴侣,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就不会放弃?”萧雨笑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说的只能代表当时,说的人早就忘了,听的人却永远的记在了心里,何况诺言的保质期恐怕是最无定期的。
“在吴城的第三个冬至,我们领了结婚证,元旦举办了婚礼。我们接受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像所有新婚夫妻一样,许的是一生一世的幸福美满。婚后第三年,我怀孕了,他从老家接来了父母。我生了个女儿,我们都很喜欢。可是公婆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见我生了女儿态度就变了,当着他的面是一套,背过他又是一套,让我苦不堪言。老太太话里话外让我再生一个,而且必须得是儿子。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思维方式不同,凑在一起生活很不容易,别的我都能忍,唯独这件事,我没有一点办法,那时的压力真是好大好大。”
“我每天往返在单位、菜市场、家,除了工作,推掉一切应酬,全心全意抚养珠珠,双耳不闻家外事,几乎与世隔绝。家,这个本该温馨舒适的地方,纠结了我太多的无奈和烦恼。”
“我最郁闷的五年却是他顺风顺水的五年,我感受到他职位上升带来的荣耀,同时更感觉到这个曾经细致周到的男人越来越自大、越来越自我,家里的两位老人更是他独断专行的催化剂。我感到自己完全沦为了他的附属品,没有话语权、没有存在感,在他的心里也变得无足轻重。”
“他每天衣冠楚楚匆匆离家,披星戴月回家,想和他说说话,他已经睡着了。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他的工作我参与不了,我的烦恼他体会不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麻木无味,让人厌倦。”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现在想来就是他当上局长不久之后吧。以前我抗拒有关他们之间的事,现在想来,像墨院长说的,我并非没有一点错。软弱、自闭,就是我的错。”
“可是他有更多的错,即使他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决定换一种生活,他也应该坦白,而不是隐瞒、欺骗,把我的信任和容忍踩在脚底践踏,如果他坦白了,我一样会放手,不用再一次被别人践踏,他连为我保持可怜的尊严都没有做到。”
“可是我不恨他,也不恨那个女人。对我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也不后悔,我相信我能把握住以后的人生,也希望他能如愿得到属于他的幸福。”萧雨平静地说完了,原来并没有她想的那么痛苦,她淡淡地笑了笑。
什么是真正的解脱,放下怨恨也是解脱了自己,成全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顾飞不懂家庭生活,通过萧雨才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繁复的家事,头一次觉得自己欠缺了什么。默默给萧雨面前的空杯续上茶水。
他是孤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独来独往,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他欠缺的正是这人间烟火。
“该我了?”闻美兰自觉地问,倒豆子一样快人快语,“我师范学院毕业当了老师,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孩子。两地分居,苦乐自知,完了。”大家还没反应过来,闻美兰已经结束了她的故事。
闻美兰无辜地看着大家,“是啊,我的人生太平淡无味了,确实没有你们那样感人肺腑的故事可以说的,你有吗?”问齐芳华。
“我吗,是有个故事,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说过。”齐芳华一向独立、强势,从她们认识她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真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看到大家都睁大眼睛等着听故事,齐芳华笑了,“你们呀,真够八卦的!”
也许太久远了、也许已经无关紧要了,她语气平淡地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人,这辈子总会遇上个渣男,我就比较不幸,刚参加工作就遇上了一个。我执拗地和父母对抗、搬出家里和什么都没有的他住在一起,就等着挑个好日子结婚,他却为了追求他的锦绣前程,飞快地撇清了我们的关系,抓住机遇娶了领导的女儿。”
“那时候的我伤心欲绝、无依无靠,连最亲的人都嫌弃我,我当时死的心都有过。也就多年的同学—大军不顾风言风语四处走动,甚至为了我和家人断绝关系、陪我调到了很远的吴城,让我重新有了活下来的勇气。我是怀着孩子嫁给大军的,那个孩子后来没保住,可是我却不能生育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悲痛,齐芳华对那段历史已经没那么忌讳了。
“这么多年,我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唯有工作能麻痹我的神经。大军是个好人,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可是我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他面前是展露无遗的,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他对我越好我越自惭形秽、对他就越冷淡,他却处处让着我,看我脸色。”
“我对他心存感激,可真的产生不了感情。结婚十五年了,大军对我无微不至,都说开车的脾气不好,可他真心对我好。都说他配不上我,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配不上他。”
“今年年初,我在省城参加完会议,在酒店茶餐厅等朋友,我看见那个人渣了。他面朝我走过来,我当时惊呆了,以为他认出了我,慌忙低头看手机。我挺可笑的吧,他怎么可能记得我?他当然没认出我,没有半步迟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坐在不远的地方。”
“岁月真不公平,对男人特别优待。他几乎没太大的变化,盛气凌人、光彩依旧。可是我,面对面他也认不出来了,或者心里根本没有我存在过的痕迹,他的视线明明从我身上扫过去的。我就那样麻木地坐着,耳朵不由自主地听着。他的声音还是那样醇厚,就是多了些上位者的气势。他见的是她的妻子,尽管声音压得极低,我还是听到了,他又辜负了一个女人。她的妻子情绪非常激动,把茶水泼到了他的脸上。我听到她愤怒地说,你就是条狗,改不了****!贼心不改,始终如一!打了老娘的脸面还要老娘给你擦屁股!最后他们协商好了,双双离去,像一对模范夫妻。”
“我想,老天爷可能可怜我,给我这个机会认清他的丑陋嘴脸,断绝我所有的念想。以前他就是扎在我心上的一根刺,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在意那个人,总是为那个人的错找各种理由,骗自己。你们说,为那样的人我值不值?我逝去的青春该向谁讨要?我是不是自讨苦吃?”
大家沉默地喝着清香的荷叶茶。
齐芳华放下茶杯,笑的有些勉强,“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陪着我,对我这么体贴!”
闻美兰诧异地看着齐芳华,萧雨的心快速跳动了几下,紧张地握着手中的茶杯,顾飞也抬眼看着齐芳华。
“昨天我检查的时候,他们就古里古怪的,我要是连这都看不出来还混什么?再说自己的身体自己也有感觉。”齐芳华笑着说。
“什么情况?”闻美兰迫切地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乳腺上有肿块还能是什么病,无非就是良性、恶性。”齐芳华轻描淡写地说。
“啊?”闻美兰张大了嘴,和萧雨初闻时一样的震惊。
“没什么,妹妹们,认识你们一场,你们这样为我费心,我还是很欣慰的。”话说出来,齐芳华反倒释然了,伸出手牢牢握住萧雨和齐芳华的手。“姐姐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你们可要好好珍惜自己、要活得有价值!”
“确诊结果还没出来,别乱想!”萧雨劝慰道。
“是的是的,一定不会的,肯定是良性纤维瘤,我前年还拿掉过一个花生粒大小的呢!”闻美兰说。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齐芳华苦涩地说,“我就是有个遗憾,以前任着自己的性子不愿意去检查,没给大军生个孩子!如果真的有什么,他一个人怎么办!”
“如果这次是老天爷和我开的玩笑,我一定不再荒废生命,一定要给大军生个孩子。”齐芳华有些悲怆地说,她心里没有大军?放不下,这就是答案。
萧雨心中悲凉,忍住眼里的泪水,喃喃地说,“一定有这个机会。”
顾飞神情恍惚,人生苦短,每个人都是命运这盘棋上的棋子,机会在你面前不珍惜,后悔时又没有机会了。
错过方知后悔,错过才知珍惜。
萧雨的电话响了,给悲伤的气氛增添了一些紧张。
目光齐齐地看向萧雨,萧雨稳住颤抖的手接通了电话。
听清墨成池的话,萧雨的精神一下子松懈下来,疲乏地靠在椅子上,双手无力地垂落,手机掉落在松木地板上也不知道。
齐芳华以为是最坏的结果,她笑了,命运弄人,她现在想通了,却是太晚了!
萧雨听到墨成池在电话里清清楚楚的宣判:“良性。现阶段确认为良性肿瘤,需要尽早摘除、定期观察,你可以放心了!”她看向齐芳华,喜极而泣,含糊不清地说着,“我就说,你这么好的人……”
齐芳华的泪水默默地顺着脸庞淌下来,“是的,老天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再错过了。”
顾飞拾起地上的电话,电话没有挂断,还没放在耳边,就听到墨成池焦急地声音传出来,“萧雨,怎么了?萧雨!快回话!”
一丝嘲讽在顾飞脸上闪过,他对着电话缓缓说,“没事儿,萧雨激动地傻掉了!我们都在这儿,你要不放心就过来吧,我们在荷苑。”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笑墨成池,还是在笑自己。
他,墨成池,这些年来什么时候紧张过一个女人?为一个女人做这么多?不要拿方案做借口,一切不成立的逻辑都成不了借口!为什么笑自己?没错,萧雨重新把他们带回人间体会喜怒哀乐爱恶欲。他,顾飞,也想要这样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