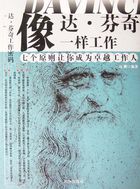辰时,李家,大雾。
李晋打开大门,看着门口林子难得一见的鬼天气,伸了个懒腰。不远处,一个火红色的身影正在缓步走来。
李晋并不在意,反倒是打了一盆水,朝着迎客的门槛泼洗。待到外面那人走至近前,李晋才抬头招呼:“回来啦。进来歇歇吧。”
来者,乃是一身疲惫的红孩儿。前些日子,李棠亲自下令,要他前去接引牛魔王;红孩儿倒是听话,足足在边界守了三天三夜,但却没有等到自己的目标出现。没想到第一个任务,自己便是铩羽而归,真心是触了霉头。
“路上遇到了几个人。”红孩儿抬脚,刻意跨过了湿漉漉的门槛:“他们看我穿着李家制服,不由分说便杀了上来。”
“常有的事儿。”李晋倒是平常心:“咱执金吾嘛,有几个仇家,难免。”
“一共十六人,身手都不错。”红孩儿掸了掸身上的灰末,摊开双手掌心,事无巨细地向李晋汇报:“杀了三个,烧了九个,打残了三个。领头的我放跑了,如果需要追寻幕后主使的话,我这便去追。”
李晋抬眼望了望;红孩儿左手手中,捧着一把灰末,看来应该是烧死的那些人的残骸;而另一只手里,则是握着一股微弱的火苗。这火苗像是一个小人儿般有手有脚,看动作正在狼狈奔走,似是伤得不轻。
“不用追不用追。”李晋急忙摆手,然后搂住红孩儿的肩膀,附耳说道:“我跟你说,这李家什么都好,就是规矩太多。你身为执金吾,想出门追凶吧,先要请示老爷子,他又得向家主请示。家主点头了,你又要去禀报二当家立个字据啥的,说好归期。再然后呢,你又得去找李征……总之,简直是麻烦透顶。”
红孩儿看了看手中火苗:“那,便做了数?”
“做了数呗。”李晋耸耸肩,倒是轻松:“敢干这种事的家伙,无外乎就是二十八宿、狮驼国或者天蓬,寻来寻去也是这个结果。迟早都要干掉的,何必弄那么明白。”
说着,李晋又看了看外面的大雾,嘟囔一句“为何还没散掉”。
红孩儿点点头,瞬间握住了右手。二三十里外的地方,腾然迸出一道赤红色火柱,包裹着一个逐渐变成粉末的身影,如同蛟龙破天一般窜向了天空。
即便在大雾之中,这道赤红色光芒也叫人瞅得清楚,仿佛白昼的烟花。办完事,红孩儿拍拍自己两只手掌,多谢了李晋指点后,朝着自己的寝室走去。
倒是李晋愁眉苦脸:只是叫你算数,你这么招摇,一会儿吵醒了小姐有你好看!
不过……李棠看到这烟花,说不定会满心喜欢。然而此刻辰时刚到,并无多少人注意到远处的这股惊艳。
看到这道烟花的仅有寥寥数人,其中便有那早早起身站在登天塔窗口朝外眺望的白象。而他身后,餐桌边上正坐着大快朵颐的青毛狮。
“南边,咱安排的伏兵全被灭了。”烟花散尽,白象两个手指并在一起,掐指一算之际却在手中迸了一股子不灭的火苗。他并不慌乱,只是打开随身的酒壶,将火苗装了进去。
青毛狮头也不抬:“灭了便灭了,多大点事。老三呢?”
“昨晚说是去探望朋友,彻夜未归。”白象说道。
“大事临头,却还使小性子。”青毛狮脸色不悦,一口咬断了手中的烧骨,嚼在口中咔咔作响:“什么探望朋友,还不是去跟小白龙那厮混喝酒。”
“听说不是那小白龙。”白象打开纸扇,似是百无聊赖:“是一个半年前在京城新认识的,昨日被袁天罡打伤了。”
青毛狮坐直身子,嚼了几口嘴里的酒肉,忽然间单手将面前的铸在地上的大理石餐桌连根拔起,随手朝着窗外扔去。
白象看着这一幕,虽然见怪不怪,却也还是皱眉:桌上是两人份的早点,自己可是丁点未动呢。
“你是他二哥,素来就知道溺爱他,也不说管管!一国正事不理,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外面同不三不四的家伙鬼混!”青毛狮暴跳如雷,张牙舞爪地大吼着:“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他娘的,老三呢!?我剥了他的皮!!!”
白象皱眉,刚要开口,却见得一只锋利的爪子朝着自己面门扑来。这一击决然大意不得,白象飞快张开自己的鼻子,左突右绕,灵巧避开锋利的五爪后,从侧面层层卷住了青毛狮的胳膊。拦下这一掌后,白象即刻熟练地抬起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果不其然,那青毛狮已经理智全无,看到自己无法再朝前近身半步,朝着白象张嘴便是一声贯彻长空的炸雷咆哮——
不仅房间内四方的窗户棱尽数稀碎,就连整个登天塔也跟着微微摇晃。
“大哥,你犯病了。”白象看着青毛狮猩红的双眼,松开自己捂着耳朵的双手,摸向了腰间的葫芦:“莫急……”
此时,房外传来了敲门声。
一队执金吾全副武装,分两列埋伏在房间门口。而上前敲门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被吵醒的大器。
木门吱呀一声开了,白象独自走了出来,将身后的房门虚掩。
“咋回事啊,叫得跟挨千刀似的这么响。”大器抬手,擦了擦自己左耳流出的血迹——他昨夜便是窝睡在这一层的门口处,刚才近在眼前的炸雷,几乎震聋了伏着地板的那只耳朵。
“许久不出门,水土不服,八成是老毛病犯了。”白象打开手中的白纸扇,说得自然:“惊了各位,实在抱歉。眼下我已让大哥服了药,一会儿便好。”
说着,他眼神左右一瞥,扫过一众执金吾。
“啊?你说什么?”大器歪着脑袋用另一边耳朵凑了过去,几乎顶在白象面前,嘴中同时大声喊道。并非大器有意挑衅,而是他真的没有听到。
“贵客若不介意,”一个女声开了腔,随即执金吾中有一人上前拦住失礼的大器,手中捏着的乃是跟李棠那支相似的桃木嫩枝,说话也是轻声细语:“在下倒是会一些偏方医术。”
“六萬,你倒是先治治我的耳朵才是!”大器同这手握桃枝的姑娘大声说道,同时挤在了中间,将其与白象隔开些许:“我咋觉得我这边耳朵听不到了呢!?”
哦,原来这是那李家负责接应的六萬……白象倒是听过对方名字,人却是第一次见到。并非六萬在外多有名气,只是女的能入执金吾,确实少见。
先礼后兵,虽说众执金吾已经给足了白象面子,却依旧没有丝毫打算散去的意思。
“倒是不必麻烦……”白象明白,对方信不过自己的一番说辞;他也不多做辩解,只是推开了身后虚掩的门。
那握着桃枝的六萬顺势上了半步,准备一探究竟——
房间正中摆着白象的酒壶,塞口处不断钻出形态各异的妖兵妖将,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拼了性命厮杀着。
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只见那青毛狮全无霸主风范,反倒是像一只野兽一般扑来扑去,不断斩杀着面前的妖兵妖将。
双方实力悬殊,斗下去的结果,一眼可见。
一个缩在后面的妖将,手握一把雕花巨斧,忽然看到旁边的门开了,便一跃而上,朝着门口便是一劈。握着桃枝的六萬略微慌乱,急忙抬起手中桃枝一挡,桃枝却被那斧头劈成了两截。眼瞅着斧头就要劈到脑袋上,一只只有三根手指的手从六萬背后伸出,一把抓住了砸下来的斧刃。
“疼疼疼疼疼!”出手之人,正是大器。只是这一招空手入白刃实在鲁莽,霎时间大器的手心已经皮开肉绽,脸上更是疼得扭了筋。六萬正在担心,却听得那大器附耳轻声说道:“我替你挨了一刀,之前打叶子牌欠你的银子咱今天两清了啊。”
六萬素来脾气最好,多年前赢了大器不少银子也从未讨要。没想到,大器倒是一直记在心里。但是,眼前这妖将实力绝对不俗,这大器又惨叫连连——万一因为这点银子而叫自家手足搭上一只手的话,六萬心中怎可能过意得去。
“让开!”里面那妖将急切切怪叫,脸上更是狰狞,全然看不出五官。他双手同时握住斧柄,想要将兵器从大器手中拔出去。
但任凭妖怪用尽了力气,却依旧没办法将雕花巨斧从大器的三根手指里抽回去——
“让开,让开……”那妖将终是没了力气,嘴里面的话,反倒是带了哭腔:“求你……我家里还有老母,还有……”
下半句话还未说完,这人的身子已经悬空,半截都在青毛狮的血盆大口之中。青毛狮略一用力,便将这妖将囫囵吞了进去。
一众执金吾都被这一幕惊住,离青毛狮最近的六萬已经失了三分神色,手不禁向腰间一摸——大器眼疾手快,登时按住了六萬的手掌。
“哦?”里面的青毛狮忽然打了个哈欠,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似乎这才看到门口众人:“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哎呀,李大器你个穷鬼也在?”
“诸位……”白象抬手抱拳,对一众执金吾说道:“家兄顽疾顿起,让诸位费心了。”
“我又……?”青毛狮似乎不大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搔着自己脑袋问道。
没人接话。
“诸位不必惦记:家兄这病,倒也并无大碍。要么我家老三在,要么杀几个人便好。发作了,便要再隔上个把月才会再犯。”白象说着,走进了房间,将酒壶塞紧后挎在腰间,继续解释道:“而且,诸位千万不必忌讳;我兄弟并非啃食同类,这些都是我练出来的妖兵妖将,并无灵性,单单专门为了给我大哥治病。”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大哥他脾气性子没来头的大?”大器倒是性子实在,一语道破:“这病要么是吃饱了撑的,要么就是……六萬,咱家有没有妇科大夫?”
外面的执金吾刚刚缓和的心一下子又被提到了嗓子眼:此番言语,实在火上浇油。
青毛狮没有生气的意思。他脑子慢,全然没懂大器的一番奚落。
白象也只是眯着眼笑了笑,知道大器并非有心,所以并不生气:“惊扰了各位。若是家兄再犯,定会请大器陪他玩两把解闷。”
大器听到这里即刻点头,嘴中连连说“好,好,好!”
既然相安无事只是误会,一众执金吾便退了。临下楼时,心细的六萬凑到了大器身边,开口道:“手有事么?”
这番温柔算是闯了祸;大器赶紧抱住自己的手掌,又开始哭喊。
“咱银子清了。”六萬猜到对方心思,皱眉说道:“都多久了,反正现在也没人打叶子牌。二筒走了以后,咱连四个人都凑不齐。”
大器即刻破涕为笑,甩甩手上血迹,一脸轻松只说没事。
“你我谁去禀报老爷子?”六萬见大器并无大碍,心下安稳不少,即刻提及正事。这白象的招式,六萬也略知一二;白象素来身居狮驼国军师一位,掌管着帜下大军。而白象身边的酒壶,乃是法宝“方寸”,可容纳千军万马而有余。
可以说,白象乃是身怀重兵坐在了李家。
“十四个妖将,七十来个妖兵。小场面,没必要惊动上面。”大器打了个哈欠,倒是不以为意:“人家万一说,这里面是药,这酒壶不是方寸,只是个普通药壶,咱能有什么说辞?再说了,登天塔里的事情,老爷子早就知道了。要是有吩咐的话,老爷子一定一会儿便到。”
六萬想了想,也是这么个道理,便不再理会。
众人散去,只剩下了大器依旧驻守。他抬手看了看手中的刀伤,继而瞄了几眼白象的房间。
二筒,六萬和七条,以前皆是李家下人,而且三人均是大器的“牌友”。三人打小青梅竹马,抛开一直与六萬眉来眼去之外,二筒与那七条还是亲兄弟。三人本事不错,先后都进了执金吾,算得少年得志。二筒更是颇得家主赏识,数年之前被安排了重任,去了不知道哪里落地为细作,探听情报。而七条则是跟了二当家当近身,六萬则是做了执金吾中的军医。大器呢,被李棠派出去守山,大家来往便少了一些。
大器记得很清楚。
印象里,自己欠了豪爽的二筒总共五两四钱银子。印象里,二筒惯用的也是雕花斧子。印象里,二筒的老母亲手艺非常不错,包的饺子那叫一个香。
君令如天。老人家寿终正寝之前,二筒也没有回来见最后一面,只有七条带回来了二筒的一封信,信里面说哥哥在外面一切都好,不用家母惦记。老人家最后含笑而终,老爷子亲自出面张罗了丧事,也算圆满。
关于二筒的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
大器打了个哈欠,抬起头对着房梁说道:“老爷子,你早知道了是不是?”
没有任何回应。
大器耸耸肩,似不在意,嘟嘟囔囔道:“既然知道了,早早说了才是;执金吾不长命,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何苦让六萬一个姑娘家的守活寡。”
大器摇摇晃晃,宿醉的感觉,再一次涌了上来。
此时犯难的,自然还有那听到自家大哥青毛狮一声吼叫的苏钵剌尼。平日里听到大哥发了脾气,苏钵剌尼必当立时回去领罚,让大哥数落几句也就做了数。但是眼下,苏钵剌尼却不大走得开。
归根结底,便是因为眼前的吴承恩。
吴承恩是今早卯时醒来的,元气已经恢复了大半。睁开眼后,吴承恩第一眼便看到了苏钵剌尼,登时面露惊喜。而青玄在一旁,看到吴承恩又缓了过来,总算是安了心。
那苏钵剌尼是入了夜后悄悄来的,只说是担心吴承恩身体;吴承恩当即帮着玉兔姑娘介绍了一下,嘴中说道“朋友”二字时,自豪语气毫不吝啬。之后,吴承恩便要青玄帮忙张罗些吃食,总不能叫朋友饿着肚子。
青玄见吴承恩恢复正常,不再杀机腾腾,总算长出一口气,便去了客房的后厨准备。玉兔姑娘也是不顾一夜未睡,帮着青玄去打下手。
吴承恩见二人离开后,即刻拉着苏钵剌尼,摸着黑便出了门。
“咱这是哪去?”苏钵剌尼不禁有所疑惑。
“去找那二当家。”吴承恩头也不回,只是迈步:“算账。青玄的事情,不能就此作数。你得帮我。”
苏钵剌尼心中虽然对此等乐事很感兴趣,却也有些失望:“也罢,我可以帮你。”
吴承恩啊……打不过便叫我去,这……朋友二字,可不是这么用的。
“嗯,要有办法,也不会烦请你。一会儿还要麻烦苏公子帮我做个见证。”吴承恩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李家执金吾太多,我也怕有了误会让李棠生气。我也没别的意思,只同他单打独斗,讨回青玄的帐便作罢。”
只是请自己做个见证?苏钵剌尼听到这里,不由欣喜万分:自己果然没有看错吴承恩!但是细细一想,苏钵剌尼不禁叫苦连天:他倒是不怕得罪那狗脾气的袁天罡,陪着吴承恩去了便去了;但是,吴承恩如果真去了的话,万一惹得那小矮子真动了气,基本便是与送死无异。
这不是请自己去作见证,这是请自己去帮他吴承恩收尸啊……
不过,奇怪了……想到这里,苏钵剌尼心底一直有一个疑惑,自打京城开始便不得而解:按道理来说,吴承恩的本事也不算太差。到了这般境界后,理应能够察觉到自己与对手之间的差距。但是,别说那袁天罡了,吴承恩连他这个名震天下的苏公子都似乎毫无察觉……
看他急冲冲的步伐,难不成真得觉得自己有胜算?别是昨天撞到墙,自己的朋友成了傻子吧?
“吴承恩,你去的话,八成会丢了性命。”苏钵剌尼思来想去,还是开了口。报仇这种事,苏钵剌尼自然支持,更不会阻拦;但是报仇和送死,完全是两码事。
没想到吴承恩倒是乐观:“你的意思是,我只有两成胜算?那便够了。我还有一招没有露过,到时候保管要他跪地求饶……”
苏钵剌尼不禁愣住——他的意思是,只有两成几率那袁天罡指不定会看在李棠的面子上留吴承恩半条命。
苏钵剌尼停住了脚步。
“吴承恩。”苏钵剌尼收了平时的笑脸,严肃说道。
“怎得?”吴承恩不晓得为什么一向吊儿郎当的苏公子忽然这般语气,自然是有些迟疑。
“随我来。”苏钵剌尼思忖片刻,对吴承恩说道。
一前一后,吴承恩随着苏钵剌尼,走到了李家大门附近。苏钵剌尼抬手一挥,大门便骤然大开。待二人出了门后,苏钵剌尼照旧一挥袖子,门便从里面闩住。
门房里熟睡的李晋,似乎毫无察觉。只有哮天从窗口探了探头,发觉是吴承恩后,哮天摇了摇尾巴,刚想叫出声,却被李晋一个翻身,抱在了怀里。
站在林子里的苏钵剌尼左右看了看,随即双翅一展,化作飓风飞向天空。片刻盘旋后,苏钵剌尼即刻落下——随在他身后的,还有凭空而至的漫天大雾。
吴承恩一下子仿佛遁入幻境,不晓得苏钵剌尼这是要干什么。
“不大想叫别人看到。”苏钵剌尼耸耸肩,站在了吴承恩一丈距离远近。
吴承恩大惑不解:“苏公子,你这是……”
“出招。”苏钵剌尼淡淡说道:“你放心出招便是。”
“你……是想要切磋一下?”吴承恩猜测到了七八分,只是他掏出龙须笔之后略有犹豫:“能不能等几天?我一会儿还要去了结与那执金吾二当家的恩怨,现在并不想节外生枝。”
“不不不,不是切磋。”苏钵剌尼摆手说道:“哪里来的那么文绉绉的较量。世间险恶,只有厮杀,没有切磋。”
“没来由的,为何你突然……”只凭着苏钵剌尼忽如其来的一番话,吴承恩自然更是出手不得。
“我总算明白了。”苏钵剌尼伸出了一只手,在自己面前平伸:“你是被你师兄青玄呵护过头了。蛋里的鸡崽,看不到豺狼虎豹,看不到鹰击长空,自然更不明白什么是天,什么是地。水陆大会,本是最好机会,奈何青玄只打算领着你一直在客房暂居,为的就是避开天下群雄。你们师兄弟的事情,我一个外人,不便多说。只是今日,我便勉为其难,替你师兄告诉你何为天地,以及这天地间……”
何为天下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