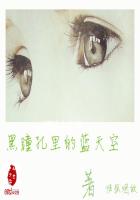两人走到衙门口,正要进去,却听有人喊道:“公子快过来。”只见龙二站在另一处街角,使劲招手。谭嗣同急忙过去,龙二说道:“我见你和心五都不在府内,便出来寻你们。正出衙门,见三人从门口经过,穿着和我们无异。听到他们中间有人低声说话,口音却和我们在关外遇到的那些挖金的日本人一模一样。我正准备偷偷跟过去,见你们回来了。便先告诉你们,只见他们往北走了。只怕这些人又是来干坏事的。”
谭嗣同都不用想,小日本不是来干坏事还能做什么。连忙随龙二往北追去。
远远看到那伙人走进了一家书店。谭嗣同要龙二两人留在外面,自己一人款款走了进去。
只见那三人走进了里屋不见。屋里只有一个伙计闲极无聊的玩着鸡毛掸子,说话听不出日本口音。便假意四周翻看摆着的书籍。倒没发现什么蹊跷。只是奇怪架上有许多介绍四川,西藏等地风土人情的书,还有这些地方的老式地图。按门归类,十分齐全。按理书店除了四书五经等典籍,还有一些小说。或者西洋的新式书籍,这些书是很少人看的。不知这店主干嘛要进这些书籍。
正寻思间,见一人从里屋出来。此人穿的破破烂烂,脚上一双草鞋,头发像茅草蓬着。两手满是污垢。手指虬壮,显然常年做的劳苦工作。偏偏两眼充满戾气,不像寻常吃苦的良善百姓。这模样显然也不像识字的货,更不会来买书。偏偏里屋跟着走出个掌柜模样的人,还把此人颇为恭敬的送了出去。谭嗣同心知其中有鬼,只是一时还找不到头绪。见屋里就剩自己一人,显得突兀,便借口没有自己想要的书,退了出来。
谭嗣同领着二人回衙门,边要龙二多监视这间书店。这里肯定是日本人的一个据点。只是一时还猜不到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日龙二过来告诉谭嗣同,刚看到一群日本人出门了。谭嗣同正准备过去探个究竟,不想张之洞叫人来找自己。只好先去见张之洞。
看谭嗣同来了,张之洞问道:“你多久没见你父亲了?”
谭嗣同听此一问,暗暗惭愧起来,从那年回湖南起,算算有两年多没去甘肃见父亲了。低头说:“快三年了。”
“天下之大善,孝也。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你应该去看望你父亲了。”
谭嗣同答是。
张之洞又说:“其实我是有一事要你去告诉你父亲,他经略甘肃多年,对西北形式比我了解。我最近收到军情,英国人正在从印度往锡金囤积兵粮,有觊觎我西北之心,估计不久就会对西藏不利。你去告诉你父亲和谭忠麟,最好有些准备,和驻藏大臣文硕及早联络,早做安排。李鸿章不敢备战,估计会打压文硕,靠朝廷又会是割地求和的结果。你把我的意思传达即可,如何定夺他们自会有主张.”
“我马上动身。”谭嗣同听说英国人又要搞事,心中怒火中烧,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每一个都是狼子野心,想着沿海,垂涎台湾,染指东北,如今英国人竟然又把手伸到了西藏,这支离破碎的国家,哪里还有一片净土,一处安宁!
“如果英国人真的入侵西藏,该打还是该和,大人自己会如何决断?”谭嗣同还是想听听张之洞的意见。
“想都不想说打,那是****,想了说打,那是无知,三思还说打,那人说不定是个汉奸。”辜鸿铭从里面出来说道。
“那辜先生的意思不打才是爱国?”谭嗣同知道此人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
“打是打不过的,结果无非死一些炮灰,然后割地,赔款,求和。”辜鸿铭毫不客气说道。
“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张之洞说:“辜鸿铭说话虽然难听,却说的是事实。藏区是个********的地方,长期以来,只是臣服于中央,其实是独立自治。那里的最高统治者是世袭****,以教义统治百姓,并不重视军事经济民生。也不直接听命朝廷。首先打不打仗,主要还得看那****的意见。****是当地的行政长官,也是精神领袖。他若不想打,不开战就已经输了。打不打的赢,从各方面分析,也都是机会渺茫。英国人已经集结了二千精锐兵力,都配有滑膛枪,大炮,显然有备而来。藏区朝廷没有驻军,那些藏民武力装备还是原始的弓箭长矛和火铳。显然不足以和英国人抗衡。但是战争也不完全取决于武器,兵力。一次的输赢也不能决定长期的战局。西藏是奉行宗教的地区,只要****坚持抵抗,民众大多会追随他们的领袖顽强抵抗外侮。此乃人和。藏区四面地处高原,四面都是高山,横断山脉,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脉拱卫四周,进出寻常车马难行,何况是行军作战。此乃地利。而今冬季将临,喜马拉雅山更将天寒地冻,飞鸟难渡。此乃天时。如此天时地利人和都全了,只要安排调度妥当,坚持长期抗战,甘陕再予以支持,藏地自保还是有希望的。”
分析完局势,张之洞其实并不乐观。深深叹了口气。一个国家自己没有能力拱卫国土,寄望于当地的领主自己的觉悟和能力自卫,只觉得可悲而且荒唐。琉球就是如此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在越南本来朝廷已经击退了法国人,可依旧把宗主权拱手相让。如今西藏的形势又岌岌可危,面对这千疮百孔的时局,张之洞只觉得无力回天。心想如今若能把自己把持的两广局面经营好就算万幸,也无暇他顾了。
谭嗣同当日收拾好行李便要辞行。张之洞把他带到书房,打开一口陈旧的皮箱,在里面翻出一卷书轴。递与谭嗣同:“你运气还好,我刚从当铺把我的一些字画书籍赎回来了。这里有林则徐的一副亲笔手书,我现在赠送与你。望你能好好体会林公胸襟气度,将来有他那样的见识气魄和成就。”
谭嗣同徐徐打开字卷,微黄宣纸上写着一行行书,上面写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字迹以魏碑入行草,法度稳健而飘逸,自成一家。铃有瓶泉居士印,正是林则徐真迹。忙惶恐说道:“林公是我朝第一贤人,只有大人可与比肩。此定乃大人心爱之物,晚辈愧不敢受。”
“我来我这里也有半年了吧,帮我行走谋划,出了很多力,应当谢你。可你知道我虽然人称钱屠,其实寒碜得很,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送你了。赠你林公手迹,是我见你宅心仁厚,又敢于任事,见识学问都异于寻常之辈,所以才以衣钵传你,要你继承他的风骨为人,忠诚谋国的精神。你只当体念我深意,发奋努力,力求做一番事业。怎可还推诿!”
谭嗣同心中激荡,不再推辞,郑重收好字轴,双膝跪下说道:“晚辈谨记大人教诲,此生必当以国家为己任,为民生谋幸福,学林公精神,虽万死而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