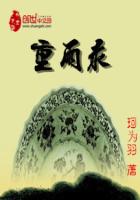第三类人物是一批青年叛逆者。觉慧是高公馆中的第一个叛逆者,同时也是众多叛逆者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有巴金自己的影子,作家对于这一人物表现出了特别的偏爱。觉慧是一个活泼勇敢、好学上进的青年,他从《新青年》等书刊中汲取“五四”新思想,逐渐形成了人道主义思想和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追求。他因参加学潮而被祖父囚禁,这不但不能挫伤他的锐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反抗专制权威的勇气和信心。他积极联络进步青年,创办报刊,宣传新思想。他蔑视等级尊卑观念,大胆与婢女鸣凤相爱。他坚决反对封建长辈的意志,支持二哥觉民反抗不合理的婚姻。目睹长辈们的胡作非为和一个个年轻女性的惨死,他诅咒这个家庭及其所依附的专制制度,喊出了“我要做一个叛徒”,毅然走出家门,远赴上海,参加了革命工作。《家》中的觉民虽然与觉慧最为亲近,也与觉慧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他尚不是一个彻底的反叛者,他还有犹豫、有顾虑。而到了《春》和《秋》,通过在实践中不断锻炼,觉民的思想逐渐成熟,成了高家大院最坚定的“叛徒”。成了青年人中的领袖,不断在大院中播撒着新的思想火种。经过坚决斗争,他与琴的爱情也日益稳固,两人互相支持,互相勉励,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淑英是思想转变最大的一位,她在兄长的影响下,逐渐接触并接受了新思想,但对于将这些思想付诸行动,她却顾虑重重。为了反抗父母为她包办婚姻,在觉民与琴的一再说服和直接帮助下,她终于下定决心,东渡上海,与觉慧会合,走上了新的道路。高家的新一代子孙,一个接一个突破封建樊篱,冲出封闭压抑的家庭,走向广阔的社会舞台,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存在,“激流三部曲”才真正成为了一条奔向大海的激流,而不仅仅是一支封建家族衰亡的挽歌。
除了以上三组人物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无法归入上述类别,但他却是“激流i部曲”中极其重要,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这就是觉新。“激流三部曲”中写得最见功力、最为成功的人物是觉新。这是一个思想矛盾、性格复杂的人物。巴金倾注全部心血塑造的觉新这个人物,不但是“激流三部曲”中写得最为深入细致、内涵最为丰富的人物,而且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典型形象之一,“觉新性格”早已突破小说所规定的具体环境,成为了那种人格分裂、失去自我、具有双重性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甚至超越时空,成为了“站在中间的人”的典型代表。毫无疑问,觉新是巴金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觉新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受过“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也曾经拥有过美好的理想,但长房长孙的身份使他过早地肩负起了大家庭的重担,特殊的处境和软弱的性格,使他信奉“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以敷衍妥协、委曲求全来换取暂时的相安无事。他是一个青年,却没有青春。他热恋过表妹梅,却顺从家长的安排扼杀了自己的爱情,使梅表妹落得个凄凉悲惨的下场;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瑞珏,却听任别人将妻子摧残致死:他暗恋着蕙表妹,却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实感情,反而做了将蕙表妹推向坟墓的帮凶;他看不惯长辈们的所作所为,却没有勇气抵制反抗,而是一味地姑息忍让;他明知这个腐朽的大家庭行将崩溃,却仍然不放弃挽回的努力,以求“对得起死去的爷爷”;他在内心深处羡慕并支持弟弟们的反叛行为,却还要帮助长辈们压制他们的抗争;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旧势力妥协退让以求息事宁人,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威逼。他是一个最不幸的人,初恋的表妹死了,心爱的妻子死了,唯一的儿子死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让他的心痛上加痛,但他还要担负自己对大家庭的责任,他还要逢场作戏,强颜欢笑,在陪客饮酒打牌中消磨时光,麻醉灵魂。他勤勤恳恳,辛苦经营,为了大家庭而殚精竭虑,却要忍受长辈们和弟妹们的埋怨和指责,而他自己所得到的,却是妻死子亡的苦果。同时也应看到,觉新虽然懦弱怕事,处处敷衍,但他也有反叛的一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将觉慧和淑英送出了家门。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两面人”,一个“矛盾体”,他既是旧势力的“帮凶”,又是叛逆者的“保护伞”;他一方面清楚地看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去赴这样的命运,因此他是一个清醒的牺牲者。作家对这个人物是既怨又怜,既爱又恨,既鞭挞又同情,这种感情是极为复杂的。巴金是以自己的大哥为原型塑造觉新这个人物的,在写作过程中大哥自杀身亡,这给了巴金巨大的打击,他本想让觉新也以自杀来了结一生,但最终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安排了婢女翠风去陪伴觉新,并让他说出了“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的话,使读者看到了他获得新生的希望。
“激流三部曲”中,《家》的影响最大,被公认为巴金的代表作,同时也是这一组三部曲小说中最富激情的一部。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巴金曾有过这样的概括:“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法语:我控告)。”《家》的确是一部控诉之作,家族制度的腐朽凶残,封建家长的专横霸道,不肖子孙的腐化堕落,无辜生命的屡受摧残,新生力量的横遭压制,一幅幅画面无不诉说着一个声音:这个惨无人道的制度必须消灭!《家》基本上属于“青春型”写作,颇能代表巴金前期创作的典型风格:热情,直率,单纯,浅近,情感汪洋恣肆,宣泄无余,文字一气呵成,较少锤炼,整体上有一种强劲的冲击力,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却又不耐咀嚼,缺乏余味。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家》还不够成熟,但另一方面看这恰恰是它的优点,直抵心灵的文字,让作者与读者达到了一种直接的沟通,作者忘情地写作,读者全身心地投入,共同营构起一个激情洋溢、大喜大悲的文学世界,并且从中得到极大的艺术和情感享受。因此,《家》虽然不是巴金思想和艺术方面最成熟的作品,却是拥有读者最多、影响最为广泛深入的作品,一提起《家》,人们会自然想到巴金,一谈到巴金,人们首先会想到《家》,巴金与《家》这两个名字已经密不可分地共同铭刻在中国文学史册和千万读者心中。
在《家》问世七八年后,巴金又陆续写完《春》和《秋》,作为《家》的续篇。这两部作品延续了《家》的内容和主题,仍然是表现封建家族的衰落和青年一代的反抗,不同的是激情的因素明显减弱,作品风格趋向沉稳平实,疾风暴雨式的戏剧性冲突大大减少,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占据了小说的核心。一般论者喜欢将《家》与《红楼梦》相提并论,认为巴金在小说结构上借鉴了《红楼梦》的艺术方法,二者在的主题思想上也有相通之处。事实上《家》与《红楼梦》在艺术风格上差异甚大,而真正继承了《红楼梦》艺术风格的,是《春》和《秋》。在这两部小说中,巴金以徐缓从容、细密绵长的笔调,描写了大家族崩溃之前青年知识分子与“家”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描写了青年叛逆者一步步成长的历程,描写了高家日渐衰败直至解体的整个过程。小说整体上笼罩着一种萧瑟悲凉的挽歌气氛,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对旧家庭既痛恨诅咒,又有某种留恋,对它的分崩离析既感到快意,又流露出怅然若失之情,正是这种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使小说显得更加真实感人。《春》和《秋》的艺术贡献,还在于对觉新性格的进一步挖掘充实,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和心理活动的展现,使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有立体感,也更加动人。总体而言,《春》和《秋》两部小说单从它们所表现出的艺术功力来讲,是稍胜于《家》的,但不足之处是情节展开过于缓慢,结构也比较松散,缺乏起伏,没有高潮,这些都影响了小说的总体水平。所以说,《家》仍然是“激流三部曲”中最成功的一部,评论家和读者一般将《家》而非整个“激流三部曲”看作巴金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是不无道理的。
《憩园》和《寒夜》
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巴金的创作风格有了较大变化,大致以1942年为界,巴金作品的描写对象由英雄转向平凡的小人物,激烈抗争的勇士变为生活重压下萎靡的灵魂,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变为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激情奔放的浪漫抒情变为沉郁冷静的客观写实,这表明巴金的文学创作开始由青年写作进入中年写作。
巴金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直到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主要有两类题材:一类沿着《家》的路线,继续表现封建家族的衰落,主要作品有《春》《秋》和《憩园》;另一类反映抗战期间的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主要包括《火》《第四病室》和《寒夜》。
中篇小说《憩园》和长篇小说《寒夜》被公认为巴金后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从对主题的挖掘深度上讲,还是从作品的艺术功力上讲,这两部小说都超越了巴金以前的小说,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20世纪40年代初,巴金回到阔别近20年的老家成都,所见所闻令他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尤其是《家》中克定的原型——早年荒唐而后来潦倒的五叔的死,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由此而思考了许多问题,并且萌发了以此为题材创作一篇小说的念头,于是就有了三年后的中篇小说《憩园》。小说写的仍然是封建家族的衰落这一题材,因此可以与“激流三部曲”一道归人家族小说系列,但《憩园》与后者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就是作家关注的焦点有了根本转移,他不再单纯地描写旧家庭的腐败与衰落,而把主要着眼点放在了对传统的家族制度的反恩和对人生、人性的探索上。事实上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神·鬼·人》时,小说主题与风格就已经略有变化。他在小说《神》中强调要“掘发人性”,“把这人的心挖出来看一看”。巴金在抗战后期创作的短篇小说《还魂草》和《某夫妇》以及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在展示平凡人物的生活、反映普通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思考民族的前途命运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显示出他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改变。在《第四病室·前记》中,巴金通过小说人物陆怀民的话,指出《憩园》的写作意图是“发掘人性”。虽然作家的自我阐释并不能代替读者阅读文本的感受,但毫无疑问,将《憩园》仅仅看作家族小说是远远不够的,那样会限制对它的全面认识。
《憩园》是一篇构思缜密、技巧圆熟的十分精致的作品。小说通过“我”——黎先生,巧妙地将先后居住在大公馆“憩园”中的杨、姚两家的命运有机联系起来,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互相映衬,使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同时也在两相呼应中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憩园的老主人杨梦痴是一个靠祖宗吃饭的旧式大家庭的纨绔子弟,他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恣意挥霍祖上留下的遗产。家道中落后,长子给他谋了一个办事员的差事,但他积习难改,既嫌位卑薪薄,又搞营私舞弊,结果被辞退。将家产全部荡尽之后,他被妻子和长子赶出了家门。长期无所事事、衣食无忧的生活已使杨梦痴丧失了基本的谋生能力,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又使他不愿也不屑自食其力,于是他沦落街头,成为乞丐,最后发展到偷窃,结果被关进监牢,染病而亡。憩园的新主人姚国栋是一个新式贵族,当过教授做过官,他虽然很鄙视杨梦痴这样的败家子,但他过分的溺爱却把儿子小虎推向了纨绔子弟的道路,杨梦痴的悲剧在小虎身上重演了。小虎仗着家里财大气粗,在父亲的纵容和外婆的娇惯下,赌钱、看戏、摆阔、逃学,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最后溺死在江中。小说通过叙述两个家庭的悲剧故事,有力地揭示了传财不传德的家风之危害,金钱财富不但不可能“长宜子孙”、福荫后代,反而成了祖宗套在子孙脖子上的枷锁,使他们养尊处优,不思进取,其结果必然是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导演出一桩又一桩人间悲剧。小说中,巴金通过不安于现状,憧憬着新生活的姚太太万昭华与“我”的对话,强调只有“活着为自己的理想”才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在《后记》中,巴金又重申了这一题旨:“谁见过保持到百年、几百年的私人财产!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来极渺茫、极空虚的东西——理想同信仰。”
《憩园》虽然写的是家族和家庭故事,但它的主旨并不在于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也不仅仅是为颓败中的封建家族唱挽歌。写《憩园》时的巴金,思想和心境与当初写《家》时相比已经大不一样,虽然他写的仍然是《家》中的那个高公馆(只不过换了名字叫憩园)、也就是他的家——李公馆,人物也是《家》中出现的高克定(只不过换了名字叫杨梦痴)、也就是他的五叔——李道沛,但在着笔的时候他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不再像写《家》时那样单纯,而是五味俱全,他对自己曾经鞭挞过的这个家和这个人,既愤恨又怜悯,既针砭又同情,既感慨又惋惜。他抨击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具体的人和制度,而是一种扎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传统观念,一种为害甚深却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事实,甚至是一种深入的人性解剖。《憩园》给人的不再是痛快淋漓的宣泄,而是深长悠远的思索。可以说,《憩园》是巴金对生活的一种新的发现和领悟,一种新的思索和探求。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与“激流三部曲”、《憩园》一起成为作家自我评价较高的作品,同时也是得到评论家和读者一致好评的优秀小说。《寒夜》以抗战胜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小人物汪文宣的家庭悲剧,深入思考国家、社会、家庭、人生和人性。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巴金以他独特的人道主义目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看到了被胜利的光明所遮掩了的黑暗:“‘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着‘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