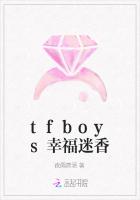为了答谢沛耕,尔槐特意做了一些糕点让巾戴带去学堂,并且邀请沛耕和他的父母到山庄来做客。巾戴在一旁看着尔槐忙忙碌碌,嘴里叼着一根草,心不在焉地说:“姐姐,这不是我们的山庄,邀请他过来合适吗?”而尔槐呢,仿佛事先准备好了的样子:“我已经和怀竹伯母打过招呼了,运腾大叔也同意了,父亲母亲也……”没等她说完,巾戴就摆摆手打断她:“这么说你已经征求了全部人的意见?”“差不多吧。”“姐姐,你还挺用心的——”巾戴说完,提着糕点就出门了,尔槐琢磨着弟弟的话,琢磨着琢磨着突然有点羞怯。
巾戴成功地邀请了沛耕以及他的父母亲,他们答应次日晚上拜访山庄。尔槐听到这个消息时,眼睛都发着亮光,一脸的兴奋,开始忙碌起来,巾戴看着姐姐不寻常的样子,就想先泼她一盆冷水:“姐姐,人家明晚才来又不是晚——”“我现在就开始准备——”尔槐激情不减,不理会巾戴还在说些什么。
巾戴无聊地走到花园里,心里还牵挂着另外一件事情。今天苏穗没有来教他学习,因为小姑娘发烧了,巾戴已经整整一天没见到她了。
“要不要去看她呢?她会不会已经睡了?”巾戴边想边走,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走到了苏穗和奶妈的屋子外面了,屋子里还亮着灯。“奶妈恐怕还醒着——嗯,那我就去问问她笑北怎么样了。”这么想着,巾戴伸出手想要推开门进去,然而他的手还没碰到门,就听到一声尖叫声,再注意一听,发现那声音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
“出什么事了?”巾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第一想法就是冲进去看看,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步也没有挪动。周围轻悄悄的,今晚的灯笼仿佛特别地少,只有远处几盏灯悬挂着,在苏穗的屋子外面却一盏灯也没有,这个小地方的所有光亮都来自月牙的月光,清冷微弱的月光,照得远处的大榕树好像一个怪巨人。巾戴突然发现自己置身在如此黑暗幽邃的环境中,一股冷意慢慢涌上心头,他甚至想拔腿离去,但是又怕屋子里发生什么事情。就在他踌躇着的时候,屋子里再次传来尖叫声,但这次伴随尖叫声的还有断断续续的话。
“啊——走开!你走开!”巾戴的心紧紧地揪着——“这是笑北的声音,还带着哭腔。”
“孩子,怎么了?”一听到这声音巾戴心里突然一惊,额头渗出的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下来,他尽量屏住呼吸但是做不到,剧烈起伏的胸膛使得他的呼吸急促,粗粗的呼吸声在寂静的黑夜如此地清晰——“那不是奶妈的声音,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走开,走开——放开我——啊——”苏穗晕了过去,巾戴捏紧了拳头,紧紧咬住嘴唇:“我要救她!”就在他准备冲进去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小个子以及对方的大个子。
“不行必须想个办法!”里面还传来那个男人的声音,刻意压低,刻意改变的声音,伪装过的声音仿佛他伪装过的外表让人不寒而栗。
巾戴看到这条走廊尽头有一堆高高的木头,他慢慢溜过去,用力将一根木头举起来,举过头顶,用力往一扔,“咚”地一声巨响,屋子里面安静了下来,巾戴捏着鼻子,躲在木头后面,大声叫喊起来:“救命啊——救命啊——”声音凄怪可怜,屋子的门突然打开了,从里面迅速跑出来一个人,一个强壮的人,比普萝奶妈强壮的人,踏着一双光滑的靴子,即使在微弱的月光下也闪着光,还有——
“怎么了?”第一个循声跑来的是普萝奶妈,过了一会儿怀竹跟在她身后跑了过来,接着几乎所有人都来了,巾戴悄悄从木头堆溜出来,躲过众人的视线,循着刚刚那人的脚印,但是脚印却在将近厨房的地方消失了,巾戴一个人站在偌大的庭院里,不禁瑟瑟发抖。
普萝奶妈怀抱着苏穗,抚摸着小姑娘憔悴的脸庞,苏穗的眼角还带着泪珠,奶妈的眼泪扑簌而下。
“别伤心,我们一定查清楚!”运腾坚定地说道,眼睛里闪着锐利的光芒。
“是啊,别太惊慌,有我们呢。”大胡子一直都在旁边,看着一幕幕,眉头紧皱。
众人应和他们俩人的话,希望抚平奶妈的心情,同时也要驱散山庄的恐惧气氛。奶妈点点头,擦去眼泪,向众人道谢。人群很快便散去。
这是普萝奶妈二十年来第一次落泪,为了自己疼爱了多年的小公主的安危,在她看来,她宁愿自己流血也不想苏穗流泪。
夜半时分,苏穗醒了,一睁开眼睛,小姑娘先是挣扎了一下,眼泪已经涌到眼眶了,小手不住颤抖着。
“是我,我是奶妈啊。”
“哦奶妈啊——我的奶妈。”孩子悲痛地叫着,紧紧抱住奶妈的腰,“刚刚——有一个人,那么像你。可是他不是你——那是个男人——你一直抓着我的手。奶妈奶妈——呜呜呜——”
普萝奶妈抑制住眼泪,心疼万分,小姑娘的话让她的心紧紧地揪着。
“别怕我的孩子,我会保护你,不让你受伤害!”奶妈对苏穗说,也是在对自己说。
“那男人一直问我是谁——问我是谁——呜呜呜——我多么盼望你来啊——可是你没来——奶妈——呜呜呜呜——”
外面冷冷清清的月光在慢慢褪去,月亮被乌云遮住了,仿佛普萝奶妈的面容被忧愁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