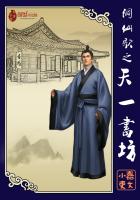“这、这上面怎么会是我的名字?!”我触了电一样,指尖从屏幕上倏地收了回来。刚刚被扩大了的那行字迹,也缩紧了身子,“嗖”的一下变回了先前的模样,它像是被我的声音吓得缩成了一团,在一片绿晃晃的光亮中聚成了几个小黑点,隐藏了起来。
张恨火已经失去了先前的激动和兴趣,左手支颐,用病怏怏似的无力嗓音说道:“谁知道呢,你要问我,还不如问问你自己好了。”
我知道,他说要我问自己,当然是问另一个时空的那个“我”。
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用两根镊子般的手指把已经藏起来的那行字迹,又从屏幕上绿色的沼泽里夹了出来。它又一次变得清晰而令人迷惑。“大唐?这个人,不,这个我,写的难道是一个唐朝的故事?这里内容你都看过了么?”我瞧了瞧张恨火,眼神也不敢稍微对指尖下的字迹有所放松,生怕一个不留神,它就从此消失不见。
“看倒是看了,现在大概有九章了吧,可和唐朝连个屁关系都没有!看来你在那边儿,也不是个写小说的好材料。要不然这密语应验的时间,我早就知道了。”张恨火嘿嘿地笑起来,说道:“拖、拖、拖,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倒是快点更新啊!我可等着呢!”
“得了得了,谁也没你这个大文豪会写东西,我这无名之辈怎么敢和你比!不过,你不觉得有点不对么?”我琢磨着“自己”写的这个故事和扎加利密语的关系,问道:“假设,我是说假设啊,假设这个故事后面写的是和唐朝有关的内容,那它和扎加利这个西方人有什么相关呢,这一中一西,南辕北辙,毫不搭边儿。你确定‘我’会在一个唐朝故事里,告诉你一条西方咒语的应验时间?”
张恨火保持着先前的姿势,盯着PAD屏幕对我说道:“这里面更复杂的事情,我当然不知道。不过就时间来看,扎加利生活的时代和唐是一个时期,没准这中间有什么关联呢。或者,扎加利到过唐朝?”张恨火任由他的想象天马行空,说道最后一句时,连自己都笑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反正是你写的嘛,只要是你写的,早晚还是会告诉我的!”
“看来你对我的信心,比我对‘自己’的信心还要大呐。”我看见张恨火重新再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不住的颠了起来,不知道他是不是想以此悠闲的状态,来表现对那个“我”的信心。“你这颠来晃去的毛病,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我随口说道。
“唉唉唉,话说清楚,谁颠了?”张恨火满不在意地说,眼神探向窗外浓密的黑暗中。
“你没颠,这桌子难道自己在挠痒痒不成?”我玩笑地说了一句,张恨火看了我半晌,像是明白过来了什么,脸色都变了样子。他摆正了姿势,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从桌前向后退去,我看见他已经完全从座位上离开,桌椅却仍然兀自抖个不停。
“地震了?!”我叫了起来,拉着张恨火就想往外跑,却被他一手反拉住。
“君闲,先别急!你把PAD从桌上拿起来,再看看。”张恨火的口气坚定又充满了猜测。
我把冒着绿光的PAD从桌子上拿起来,发现桌椅都停止了震动,但那高频率的震感从忽闪忽闪的绿色里释放出来,让我拿着它的手,也经不住颤抖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张恨火道,迫不及待地想让他说出自己的猜测。
窗外的雷声越滚越近,一声近似一声,一声烈过一声。
窗子上的雨滴汨汨的流着,流成了一道道陌生的符号,在飘忽而过的电光之下闪闪发亮,仿佛在某一刻,它们就要全部从窗上挣脱飞离,在如此寒凉、孤独的夜里布下一张大网,将蜷伏在里面的人们,一网打尽。
“雷声越来越响了!难道,难道竟然是今天么?”张恨火似乎不是在回答我的疑问,而是默默的独自推理,如同一个樵夫在黑夜中行走在陡峭的悬崖边上,危险又精妙。突然,他猛地从我手中夺过了PAD,把它死死按在了桌上,桌子便猛烈的抖动了起来,情况比先前更加激烈了。
张恨火只用手指点了几下,便迅捷打开了“我”写的故事,我看到那上面的字迹正像急速喷涌出的泉水,又像猛烈迸发着的火山熔岩,不可遏止的滚滚而来:
“张恨火打开了故事界面,自言自语的故事以高速的叙述姿态开始‘讲话’,我紧忙凑了过去,看见上面写着四行字:
黑林深处
扎加密语
雷电之夜
归梦之时
真没想到,雷电之夜密语应验的时间,竟然是我的生日!”
张恨火看了屏幕上的字后,猛地捏住了我的胳膊问:“君闲!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我被他突然的一捏一问,竟然愣住了,毕竟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过生日,就痴痴地说道:“我的生日是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对,八月十五。”我不知道是被张恨火狂热的眼神惊住了,还是被PAD上突如其来的讲述搞晕了,把一个简单的日期,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三次。
“今天是,是十四,不对!”我感觉张恨火抓着我的手激动地抖着。他的话还没说完,墙上的老挂钟就嘎吱嘎吱的响了,那只眼睛血红、毛色暗灰的猫头鹰从老巢里钻了出来,紧紧的俯视着资料室,“咚”、“咚”、“咚”,它的响声让一切都变得安静,那是十二点钟的钟声。片刻之后,仰头看着挂钟的张恨火大笑了起来!
“君闲!雷电之夜密语的应验时间是今天!是今天!”张恨火说到一半,便一手拿起桌上的PAD,一手拽着我跑出资料室。
他头也不回的往前冲,我听到身后开始想起了巨大的响声,便不自觉的回头看去。只见资料室里的桌椅、书架都开始胡乱地“舞蹈”了起来,那是伴随着整个资料室、或者说是整个阁楼的剧烈晃动而来的。浓密地拍打在窗上的雨滴,猛烈的亮了又亮,两道锋锐尖刀一般的闪电,蓦地从窗外斜刺了进来,玻璃窗一下被击得粉碎,地板烧焦出了一道深痕。
黑色的风从碎了的窗口一拥而入,资料室的文件和纸张四处飞扬,它从八卦模样摆放的书架间进行抄掠时,那些经典的论著纷纷跌落悬崖,摔在地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
巨大的晃动中,我觉得脚下软绵绵的,一脚踏实一脚踩空,一直被张恨火拉着冲到一层楼梯口的转角。
闪电落在阁楼四周不远的地方,我们来到大厅上时,阁楼正门在雷电的几次袭击下,“轰”地被劈开了,随着“呜”的一声闷响,两扇经历了百余年沧桑的古旧阁楼大门,像是两具倒在地上、身着重甲、已经死去的武士尸体,沉重又苍凉。
张恨火不去管那么多,拽着我向门外冲去,跑到阁楼大厅中央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
一道巨大的闪电落在门外不远处,像是一束一扫而过的露天剧场镁光灯,片刻的光亮就映照出了门前那个被拉的长长的身影。
面对雷电之夜的到来,我虽然比张恨火后知后觉,但也相对清醒,借着雷电的一瞬,我已经看清了门口那人的面目,随着几道闪电接二连三的落下,张恨火也认识了情况的危急。
门口站着的那个人,或者说是它,眼角已撕裂到耳畔,扭曲的鼻子上盘着一条小蛇,嘴张开着,探出来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把尖刀,蓝色的脸庞似笑非笑,头上的两只角,竟足有一米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