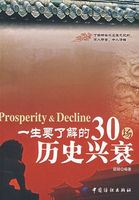新上任的银牛录额真总想把大家的生活搞得好一些,以显示自己的本事,坐穩自己的位子,聪明的他想到了打猎,若大的无人区里,经过二百多年的封禁,域内大树参天,野草沒(m0)人,野生动物漫山跑。苏瓦延边门左右五十里虽只是禁区很小的一个角,可在这里打些猎物还是沒问题的,只是怕上峰知道怪罪下来。听人说其他边门也干过这种事情,也沒咋的。他想:跟打生衙门搞好关系,到时候给他们送点礼,进点貢,他们就会睜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了。这些年收成不太好,物价上涨,原来一吊钱买到的东西,现在得用两吊钱。可薪俸还是那么多,不搞点外快,维持生计越来越不容易了。当然,打生衙门的那些人也是一样,他们也琢磨着捞些外快维持生计,故瞞着上峰捞点外快,大家都心知肚明罢了。何况,这地方山高皇帝远,上峰一年也来不了几次,自己人不说,谁知道他们在这干了啥事呢?
想明白了,银牛录额真就召集手下人开会,大家一听,当然都赞成,只是有些害怕,怕把事弄漏了,被上峰怪罪下来,因为私自在禁地内打猎是要治罪的,也听说过别的边门干过这事也沒怎么样?这年头,称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们干了沒咋的,咱们干了也不能咋的。何况,现在各家的生计都入不敷出,不搞点外快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既然大家都同意干,世忠就和大家商量捕猎的方法。怎么捕呢?当然没有人家皇家打猎的那些强弓快马,拌绳大网,只能用挖陷阱、下套子、安夹子等土办法。
一开始,他们抓住一些狍子呀,兔子呀,狐狸等一些小动物。有肉吃了,有皮卖了,分到钱了,也沒什么事,大家美滋滋地当然谁都不会让上峰知道。越干越有经验,越干抓住的猎物越多,他们就越往山里,越往森林深处进军,当然抓住的猎物就越来越大,什么野猪哇,狼啊,熊瞎子也抓住过。当然是不能抓活的,把猎物,特别是大一点的猎物都在陷阱或夹子、套子上把它弄死,拉死的回来,当然是怕它伤人。
祸还是来了,一天晚上,那天是腊月二十,长生刚从西段巡逻回来,六个多时辰走了一百里路(来回各五十里),当然累乏了,回来吃点饭就倒在被窝里睡觉了,刚到亥时,银牛录额真十二岁的小嫩(妹妹)萌萌就跑来敲他家的门(他们两家是邻居,离得最近)。
“长生阿珲(滿语,哥哥的意思),长生阿珲(哥哥),睡着了吗?”长生被喊醒,赶紧开开门。只见那小姑娘惊惶地说:“我阿珲(哥哥)到现在还沒回家,不知他去哪儿了?”
长生说:“今天安排我们两组四个人往东西两线巡逻,剩下的人除了守边门,沒听说安排干别的事呀?我到牛录所(牛录办公和人员集合的场所)去看看,也许是有什么事情缠住(意思是有事耽误走不开)了,你别着急!”
萌萌说:“我也去。”长生让他回家等着,安慰她不会有什么事的。小姑娘平时就愿意和长生玩,这次也不放过。长生见推托不下,就和萌萌一起到了牛录所。
牛录所里一切如常,边门早已关闭上锁了,两个当值的旗丁还没睡觉,正在灯前闲聊。长生一问,两人都说银牛录额真上午还在这儿,说他下午到捻子上(陷阱、夹子和套子捕猎的地方)去看看,有沒有收获,快过年了,弄点好东西给大家过个好年。
长生问:“他一个人去的吗?”
答:“他说他自己先去看看,有收获明天再和大家一起去收拾,如果没收获,不是让大家白跑一趟吗?”
长生一听,坏了!这么冷的天气,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他一个人这么长时间沒回来,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当然那两个旗丁也想到了这一点。长生说:“你们两人在这当班不能动,我把萌萌送回家就招呼其余的人一起去找。”
长生把萌萌送回家,安慰世忠额娘(妈妈)不要着急。他赶紧去找另几个旗丁,好在都住在一个屯里,一会就在长生家集合了,分成四个组,每两人一组分别到四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有两到三个捻子)去找。
长生和比他大两岁的赫长有一起到最远的那个方向上的那两个捻子上去找。两个人,出门就跑,已经快到半夜了,天还飘着小清雪,天气嘎巴嘎巴冷,别说是别的危险,就是冻也受不了哇!他们只是想:快点跑,早一点找到就多一分希望。跑了四、五里路,找到了第一个捻子,那是个钢絲套子,原样沒变,当然是沒套着猎物,就急着往下一个捻子奔。那是个离家最远的捻子,还有三、四里路,他俩连累带急,浑身都冒着汗,喘着粗气,皮帽子和胸前的衣服上都挂起了厚厚的白霜。跑是跑不动了,只能拼命地快走。快到下一个捻子了,老远就看见那个捻子——陷阱的大坑的盖已被掀开,陷阱的大坑敞着口,象个吃人的大嘴,在周边雪地的反衬下,看得十分诧眼。两人心里一紧,都不由自主地向大坑跑去,没到坑边,就看到了躺在雪地上的世忠,两人扑上去,伸手一摸,一切都完了,人凉得比雪还要凉,趁着夜色,看到世忠的脸上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冰冷的象不光滑的冰,“血!”两人异口同声地说。赫长有用手到世忠的口鼻处去试试,当然是枉然,人都冻成冰了,出的血也冻成冰了,那还能有气了。两个人连吓带累,一屁股就瘫到了雪地上。
两人歇了一阵,缓过神儿来,就商量着把世忠的遗体弄回去。他们用随身带的防身的刀(这是旗人男子的习惯,也是旗丁的装备),砍了些树枝和滕蔓,脱下一件单衣撕成布条,绑了一个爬犁,把世忠的遗体放到爬犁上,把布条搓成绳子,拴在爬犁的前边,两人并排拉着,踉踉跄跄地,直到天快亮时,才到家。
突如其来的祸患震憾着这个小山村,这些旗丁和家属们的心都颤抖着,呜咽着,那么好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是为大家死的,全屯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来为他戴孝守灵。一连好几天都下着大雪,刮着大西北风,把树林子、房子等那些高一点的东西都吹得“呜呜呜”地响。
发送(安葬的意思)出去之后,大家回过头来一分析:猜想银阿珲(大哥)可能是被一头较大的野兽撞死的,他到陷阱的那个捻子去看,可能刚巧一个较大较凶猛的野兽(如老虎或熊瞎子)正在陷阱的坑里掙扎,见有人来,便更疯狂起来,以致一跃从坑里跳出来,银阿珲(大哥)躲闪不及,被那个大傢伙给撞伤了,伤得不能动,那地方又罕无人至,天又那么冷,是被冻死的。
说起这个银世忠,也够可怜的,虽然已经二十五岁了,仍未婚娶,原因是家境较差,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不到四十岁的阿玛(爸爸)就因病去世了,扔下额娘(妈妈)、他和刚刚六岁的小嫩(妹妹)萌萌,好在有世忠的薪水和额娘(妈妈)的辛勤劳作,勉强维持着生活,当然沒钱找尾伦(滿语,媳妇的意思)。也不光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咋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旗人找尾伦(媳妇)比较不容易,旗人中,生男孩多,生女孩少,这也是北方民族的通例,第二是旗人特别重男轻女,男丁生下来就吃俸禄——国家给发晌——发工资,一直发到老,女人却不能;第三是旗人不和其他民族通婚,大清国法律规定“旗民不交产”,目的是保证旗人的血统纯正,从血统上保持独立,不被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溶合和同化,旗人只能在旗人的圈子里找旗人的姑娘为尾伦(媳妇),选择面太窄。特别是他们这个守边门、住八旗营子的旗丁,远离他们自己族群的密集居住地,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边门一隅,找尾伦(媳妇)是个大难题。
这世忠遇难,虽然沒丢下娇妻幼子,却扔下了老母弱妹。可怜的世忠额娘(妈妈),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是痛若摘心,肝肠寸断,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年幼的萌萌好象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哭都找不着调了。可有什么办法呢?人死不能复生啊!
因为世忠是干违禁的事死的,当然也不敢向上报实情,只说是有病死的,所以当然不能按因履职而亡处理,只能算是病故。当然在丧葬和抚恤上也是沒有优待的。设在吉林街的打生衙门,离这里有二百多里路,也沒来人吊唁和核实,只是考虑着再安排一个牛录额真,不能耽误了看守边门的事而已。
赫长有当上了这个边门的牛录额真。说起来他为当上这个牛录额真还颇费了一番心思,使出了一些手段。论说赫长有在这个牛录的旗丁中,论年龄他不算大,比他大的有二、三位;论做旗丁守边的时间他不算长,有两、三位比他时间长;论干事能力是一般,特别是威信不高,因为他有点小心眼,好占小便宜,所以大家都有点不怎么喜欢他,好在为了在一起共事,大家多的时候是让着他的。这回他当上了牛录额真,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前几天他出了好几天门,听说是到下九台他那克出(滿语,舅舅的意思)家去了,大家都知道他那克出(舅舅)是下九台边门的牛录额真,而且和吉林打生衙门管事的人关系不错,肯定是通过他那克出(舅舅)给打生衙门的人送礼了。尽管大家对长有当这个牛录额真即不佩服又不舒服,但这个官人家是当上了,只好“人随王法草随风”地混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