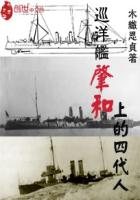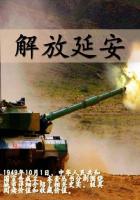你看,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一分钟前我还看着那些老同志们为祖国的未来而忧心忡忡的样子;听到马克同志点我名字的时候我还茫然了一分钟;再过一分钟我才发现,自己正坐在不曾敢想的位置上,而我至今不知道金主席选我的理由。
也许你不信,当时我想的,只是把这重要的位置交给其他同志。
人民大会有六百多位代表,内阁有二十三位老同志,朝鲜主体委员会里的其他四位都比我优秀。
之所以不坚辞,除了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当我四处打量周围的时候,迎上了马克耶布卡同志坚定的眼神。我顿时明白了,我不仅是一个人民军战士,还是有着伟大的白头山血统的革命者,肩负着常人不可比拟的重任。
在前线奋勇杀敌也是保卫家园,在后方领导朝鲜人民抵抗侵略也是保卫家园。即使挂冠而去,至少也应该留到击退敌人后。就这样,我怀着激动与犹豫的心情,接过了马克同志手中的“领袖弹”。
但如果我当时意识到,我得在这里坐很长的时间,我一定拒绝。
——摘自盟军前副总司令冯·艾斯林自由元帅的孙女艾露尼著朝鲜第二任国家主席金岩柏大元帅的口述回忆录《重上将军峰》
就算戴着高级心灵屏蔽装置,甚至让我感应不到他,我也能看出金岩柏满腔犹豫与不情愿的阴晴。
别头疼……若有更好的人选,我不会考虑你。我真想这么说。
虽然个个犹豫不决,但在面面相觑一阵后,其他人没有也向金岩柏起立敬礼,大喊:“主席好!”
那个华裔元帅的声音格外大。
金岩柏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口。气氛相当压抑,便装胖子有点幸灾乐祸。
达夏进门时,看见的场景就是我把手搭在金岩柏的肩膀上,弯下腰对他轻声耳语。重新站直了腰板,金岩柏惊异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一边微微点头,一边问达夏:“怎么样,通讯连接吗?”
“没问题了,指挥官同志……”
“别向我汇报,”我的嘴脸微微上扬了一丝,“向朝鲜代主席,平壤代总司令金岩柏同志汇报。”
“……是……”达夏的眼神告诉我,她不太清楚我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重新向金岩柏敬了个礼说:“通讯已经重新连接。但能力有限,只能恢复师级通讯。”
金岩柏站了起来,陈天杰和艾米莉也紧张地回过头,一惊一乍的反应让房间里的其他人目瞪口呆。
“怎么了?”达夏疑惑地问。
“我感觉到了爆炸,”艾米莉犹豫地说,“振动异常强烈,虽然杂乱无章,但没有移动的迹象。”
陈天杰向我点点头:“刚才一瞬间从那里散发的热量太强了。除了爆炸,我想不出别的可能。”
爆炸吗……我感应了一下。此刻我们离领袖地堡已经有了很长的距离了,生命讯号不是很清晰。
脑中的领袖地堡内部图正在慢慢消失,消失的还有尤里部队的生命讯号。我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金岩柏,暗暗为领袖地堡惋惜。
“没有追兵了。”许久我才评论了一。何止没有追兵,入侵的尤里部队和盟军都完蛋在地堡了。
看到几个人一惊一乍,桌前几位脸色也变得阴晴不定。一个矮小的西装男子抬起头,疑惑地打量了一下我们,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看来战后需要‘重建家园’了,”我耸耸肩,拍拍达夏的肩膀说,“你该汇报各部队情况了。”
达夏如梦初醒地拍拍脑袋,尴尬地清清嗓子,打开手上的档案本:“四分之一的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但在领袖地堡里的军官们返回各自岗位后,有组织的反击已经开始。驻在北部的主力稳住了战线,东西两部依托地下工事挡住了敌军进攻,只有南部形势不理想。”
“等等,”我抬头问,“为什么南部不利?地形不好吗?”
按理说,尤里部队是从南往北打过来的,南面的守军才是身经百战的部队,怎么会在其他方向稳住战线的情况下还会形势不利?
“可能是通讯不良或线路繁忙……众所周知,平壤的无线电通设施比较落后,而我们在地下……”
“所以呢?”我直直地盯着达夏,打断达夏语无伦次的回答。
达夏吸了一口气,轻咬着嘴唇。第一节车厢方向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朝鲜士兵对着达夏耳语了一番,达夏报以惊讶的眼光。
“发生了什么?”开口的是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中年人。此前西装矮个子、便装胖子、华裔元帅(通过某种难以描述的方法,我得知他们分别叫张龙山、金日正、姜尚海。而现在开口的那个叫郑浩然)个个心猿意马的时候,只有这个穿黑风衣的家伙闭口不言。
“这个……”达夏微微顿了顿,迟疑了一下。我搬过一张椅子,“列车里装着的是平壤军民的希望。都具备着听这份报告的权限。”
“两个坏消息,先说不太糟的,”达夏再次翻开文件,“平壤南面的守军……目前为止,没有回应的电文。如果不是大范围无差别电磁脉冲攻击……那就是说……”
“别往坏处想,”我立刻打断道,“说说有什么更坏的消息。”
我看到金岩柏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再一抬头,才发现其他几个人造神的眼神也都不太对劲。
“没什么,”陈天杰直视着我说,“只不过……达夏同志的第二个坏消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与看到陈天杰眼中的五角星同时的,是听到了身后的四声爆炸。
走到达夏身边时,她好奇地问我:“你跟金岩柏说了什么?”
“这个啊……”我不露痕迹地笑了笑,“我说:‘现在如果你手足无措的话,把一切交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