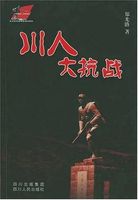“现在是1987年3月8日10点26分。第七十个妇女节将在两小时后结束。”金岩柏笑着说(作者注:盟军以1907年纽约纺织业罢工为妇女节的开始,联军以1917年莫斯科纺织业罢工为妇女节的开始)。
“没事,”我笑着回答,“我会把你那份破坏帝国主义兵痞过节心情和机会的道歉传达一下的。”
调侃后,金岩柏关闭了通讯。
远处已经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金岩柏在走廊的天花板搭了一层蜘蛛网,算着时间,也该落下来了。那个蜘蛛网我刚才试过了,简直比新式防弹衣的纤维还坚韧,而上面的黏液。除了金岩柏自己,基本没有办法摆脱它。
前三个打头阵的尖兵发出了惨叫,想从到处是黏液的蜘蛛网中摆脱出来,但跟在他们后面远远跟着的战友们立刻四散隐蔽。我不需要露头,只把枪伸出门口,对准那三个倒霉蛋开火。
双眼不看着射击目标,仅仅把枪伸出掩体射击的行为,简直像未经训练的中东游击队。但对于不需要双眼而只需要生命讯号就能够定位的我而言,这个方法,无疑会让敌人万分头疼。
三个尖兵倒下了,其他敌人立刻开火。我收回枪,子弹擦着门框飞过。
影视剧中常常有一个镜头,就是一群人齐头并进地在走廊里推进。但现实中就是送死。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像现在这样火力交叉掩护,士兵交替推进。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再这么压制下去,我会被他们牢牢堵在门后。
算准前两个的位置,我从左侧门后打了个滚,滚到右侧门后的同时开火,这两个三米外的出头鸟扑通倒下了。
一颗手雷滚到了我脚下,我立刻推门进入房间,两秒后汽浪掀飞了我。房门稍微运气好一些,仅破坏了门锁。
没关系,只要不死就行。忍着屁股的疼痛,我用刚才的办法又定位到了两个士兵离开了掩体的敌人。再次从门后伸出了枪,杀死了这两个冒失者。
就在这时,突击步枪在“哐当”一声的外力攻击下,被人打飞了。再想捡起来,又一颗子弹飞了出来,突击步枪被打到了更远的地方,捡不到了。
“是狙击手!”我愤怒地转过身,狠狠地捶了一拳墙壁。对面是个高手!
要知道,我伸出枪的动作仅仅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瞬间,露出的狙击面积也不大……对方竟然也能捕捉到这一瞬间,并且将目标击落!
虽然狙击手的位置只有两百米,但就算换做我,也不保证能够做到。
也许是觉得我没有枪了,前面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突击小组,向我所在的房间前进。他们哪来的勇气这么想?
走到门口,他们四个犹豫了一下。第一个人的手放在门上,第二个人似乎要阻止他。在经过了一番争论后,他们撞开了并没有锁起来的大门。因为用力太大,前面两个人跌在了地上。
“‘白鼠二号’,这里是‘烧杯五号’,听到请回答。”第三个进门的人接起了腰间挂着的对讲机。
他愣了一下,看了一眼其他三人做出的“没有发现”的手势,肯定地说:“这里是‘白鼠二号’。目标失踪。”
“消失了?”对面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震惊与怀疑,“你是说,‘疯熊’在我们众目睽睽下,从密闭的房间里逃了出去?还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但这是事实!”“白鼠二号”听起来相当理直气壮,“‘疯熊’的确不在这。他可能——糟糕,啊——”
之后的惨叫,是我从房顶上落下来时一刀刺进他头盖骨的声音。“白鼠二号”的脑袋经不起重压,在匕首的深入下炸出满天的脑浆撒在了周围。
好在当时我已经离开原地并拔出了手枪。“白鼠二号”背后一个士兵还楞在原地,我给了他肚子上两枪。
前面两个这才反应过来,匆忙向我举起突击步枪。我把“白鼠二号”还没倒下的尸体踢过去,把他们的步枪击落,向两颗惊慌失措的脑袋开火。
可是子弹只打出了一颗,左边一个家伙对着我手中发出“咔咔”声的空手枪愣了一下,立刻从腿上拔出手枪。
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是直接跳了过去,地上捡起的尖头钢管刺进了他的肚子,直视着他充满不甘与不可思议的瞪大的双眼,扭了一下脑袋。
“白鼠二号”的对讲机此刻还在声嘶力竭地疾呼:“这里是‘烧杯五号’!‘白鼠二号’听到请回答!重复……”
“你们的名字可真奇怪,又是白鼠又是烧杯的,”我拿起对讲机,用朝鲜讽刺道,“还有什么新奇的名字吗?比如胶头滴管、培养皿、玻璃棒……”
“马克耶布卡,你这个混蛋!”对面大吼道,“你是个暴徒!恶魔!”
“告诉你们指挥官,知道你们最大的破绽是什么吗?”我讽刺道,“明知我在平壤,竟然不取消行动。对了,还有件事:谢谢你们送来的枪。”
我捡起一支突击步枪,朝着对讲机打光了一个弹夹。枪声如暴雨般在走廊上响了起来,而且还更杂乱了。
但是我不担心这个。手表的分针慢慢地下垂到正下方的“六”上了。只要再等一分钟……他们就等死吧。
这是相当漫长的一分钟。这一分钟里,敌人的子弹一直倾泻在门框上,或者与门框擦肩而过。我不仅要躲在盟军子弹无法击中的门后,还要时不时开枪还击,以防靠得太近的盟军特种兵摸进来。但这一分钟里的敌人学聪明了,再没有哪个觉得,靠火力压制推进到门口,就能让我束手就擒。
但他们只聪明了一分钟。我感觉到四个盟军想从另一条楼梯迂回到楼上的控制室,还感觉到没由来的颤抖。
防御系统又要启动了。和上次不同,这次我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
“来得真是时候,”我看着头顶上一闪一闪的红色警示灯,想象着金岩柏满脸幸灾乐祸的样子,拿着对讲机说,“但我记得机枪子弹打完了。”
“但还有激光栅栏啊。”金岩柏的语气听不出一丝一毫的高兴之情。
“那现在……说说监控室里是什么情况吧。”我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外面隐隐约约还有刺耳的惨叫声,但是没有走近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很糟糕。四百多个警卫,大部分牺牲了……损失可谓惨烈,”金岩柏的声音渐渐变得凝重,“更糟的是,参加宴会的高官和地堡维护人员大部分被俘。大部分人质在大厅里,一些重要人质单独关押。如果大厅的人质牺牲……平壤城将处在脑死亡的状态。”
“朝鲜谚语说‘领袖为脑,国家为躯,群众为四肢’。可以这么说,躯壳损失再大,脑袋还在就行,”我慢慢扶着墙壁站起来,边站边说,“所以你们金主席在哪?是什么情况?”
“你问到关键处了,”金岩柏说,“伊戈尔同志在我这,详情让他说吧。看来敌我双方都把金主席弄丢了。”
上一秒我刚刚扶着墙壁站起身,还在舒缓有点麻木的筋骨。现在是彻底“缓过来”了。沿着走廊向控制室奔跑的时候,我听见了一个呻吟的声音。
算了……反正被腰斩的人只有一分钟的寿命,我没空给他们一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