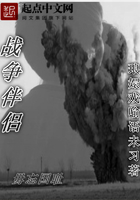白炽灯光闪到了眼睛,光线不太强,定睛一看才发现是应急灯。墙壁并非白色,或者说,曾经是白的,但现在肮脏不堪,烧焦的痕迹盖住了墙壁和天花板应有的颜色。
我所躺的是一张医院里常见的单人床。被子是新的,上面粗制滥造地画了一个红十字,活像教堂墓地棺材上的十字架。这里应该有过吊灯,现在只剩下了几个窟窿……
习惯性地去摸台灯开关,床头柜上空空如也。回头看了一眼,我拍拍脑袋,笑话自己怎么会认为这间房间里怎么会配备台灯。虽然很简陋,但房间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外面的走廊上听不见喧哗吵闹声。
“吱呀——”与此同时,门被人推开了。护士进来时惊叫了一声:“报告首长,七号床的病人醒了!”
七号床——我回头看了看头顶上。果然是一个大大的数字“7”。只是外面的人,说的是汉语吗?
没过多久,护士后面跟着一个穿“绿军装”的军官(之所以说是军官,因为他身上散发着军官的气息。只是这个“气息”不太像联军的),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大夫。
大夫没有拿听诊器,仅抓过摸了我的一下脉搏,再让我张嘴用手电筒查看了一下,问了一些我的身体情况,就明确地对那个“绿军装”点点头,汇报道:“病人之前是疲劳过度导致的昏厥,没有损伤。”
“你去吧。”医生敬了个礼出去了。我与在床头柜放下水杯的护士眼神对上的一刹那,后者似乎羞怯了一下,随后快步跑出了病房。
至于她的心思……啧,不用看了吧,看看这位站在病床前的“绿军装”军官,我大致就明白了。
“想起来了……”我轻轻叹息,“都说中国人在追求‘全面发展’,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从外交部跳到国防部,跨度还不小啊。”
“不敢当,”他和蔼地笑了笑,伸出一只手说,“也许我们该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谭维惠,但准确地说,上次见面时,我的身份并不是外交部官员,而是中央调查局在瑞士的‘情报武官’。看到那位姬芸同志了吗?她其实是军医。”
“谢谢你的介绍……呃,中校同志。”我看了一眼他军装上的军衔。中国在流行一种仿二战款式的绿军装,甚至取代了西装和其他的民族服装。而军人的不一样之处在于,他们会在肩章上标明军衔。
“坐吧——那个,抽烟的话请回避一下——我在中国认识的人不多,陈天杰算一个(谭维惠的手抖了一下,刚塞回衣服内口袋的香烟盒没拿稳,连同打火机一起掉在了地上),你算一个——但我知道的是,你不是来专程看望投靠了‘在近代史上抢去我国大片领土,欠下我国累累血债’的‘同胞’吧。”
“的确,”谭维惠捡起了落在地上的香烟盒,拿着香烟盒掸了掸衣服说,“联军王牌部队‘风暴小组’总指挥官,排行第一的精英战斗兵马克耶布卡少将大驾光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林主席也会在中南海接见一下阁下,然后苏联大使馆的同志把您送回莫斯科……但这只是最好的情况。”
“这里难道不是丹东吗?我记得离北京不太远吧?”我问道。
“知道现在的情况吗?”谭维惠说着,猛地拉开了窗帘。窗外依然是黑夜,但这里一定是市区。
中国的城市基建水平与其宣称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严重不符。即使是丹东这样的小城市,在灯火管制下,至少可以看见无数的路灯和探照灯,在黑暗的上空闪闪发光,勾勒出整个城市的繁华景象。
但我错了。的确,光亮是有的,但那是若明若暗的火光;探照灯也是有的,但那不是城市里照耀天空的装饰性灯光,而是真正用于照明的军用探照灯;漂亮的高楼和还在翻新建筑物的脚手架都不见了,只剩下满地的残垣断壁和还来不及清理的尸体。巡逻队穿梭在城市的地面上,直升机呼啸着从上方飞过。要说有什么新鲜玩意,也许只有一条条看不清的标语了……
要不是还有夜视能力,我想我也只能看见飞机和探照灯的光芒,和火光边三三两两围着的士兵。
“经过了十个昼夜的激战,我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终于解放了丹东市区,消灭了当地所有的尤里部队并向城内的各聚集地组织发布了整编通告——这个是昨天的新闻,”谭维惠如背诵教科书一般如数家珍,“但是今天凌晨开始,回应我们的却是那些聚集地头领们一致的进攻。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到盟军国家的支持,还有些人对于‘加入苏联或日本国籍’抱有幻想……然而北京方面不同意就本地政体和管理模式上进行谈判。整整一天了,战斗仿佛刚刚开始一般胶着。”
“政体……第一次听说聚集地仗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时的出力程度,在自己所在国家的土地上修改政体的。这可真是奇葩。”
我扶着头,诧异地看着谭维惠。听说香港英国人的聚集地组织的确和解放军达成协议,香港建立特区……但是没过几天,前者就全体丧生于尤里部队的反击之下了。
这是中国内政,我没兴趣评论,更没兴趣关心谭维惠话里话外的“民族大于意识形态”论调。
“你不会想说把我送到北京的飞行器都没有吧?还是说,我得帮你们解决什么麻烦来支付机票钱?对了,跟我来的还有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女兵,你们找到她了吗?”
“我们这里没有固定翼飞机了。几年前天气控制器的破坏导致了这一带气候混乱,本该天朗气晴的丹东此刻还处在暴雪季。别考虑奢望着飞行器,从中国一侧抵达丹东的所有道路都已经在山体滑坡中坍塌了。想回去的话只能往南。”
“这算是别无选择吗?”我冷笑了一声,“南面难道风雪不大,还是说,新义州有飞行器?”
谭维惠叹了一口气说:“你带来的那位似乎不太适应这个环境。放心,等天气和局势都好转了……”
“哦,那我就不走了。反正也就是在这住一个多月。能躲开苏联宣传机构一个月,也是件好事。”
果不其然,谭维惠进行了一分钟的天人交战,同意了我的要求。
“拜托了,”谭维惠露出了一个虚伪的笑容,伸出一只手对我说,“我给你准备了战友。这是你的目的地,只要摧毁了当地的尤里部队,从济州海峡到长白山将没有尤里部队,你可以安全去北京。”
“太多人反倒碍事了——对了,”坐回病床上时,我突然向已经告辞的谭维惠提问,“你难道不好奇,我怎么出现在丹东的吗?”
“是挺好奇,”谭维惠笑着说,“可你会回答吗?自从北京的讯号中断,只要不损害我们安全,再不可思议也不会刨根问底。”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抬起头,看着谭维惠的眼睛,用阴冷的声音问,“要是我……待在丹东,你想怎么让我去平壤?”
“还以为你不会提了呢……我想过你击落三架解放军直升机的事,但洛马诺夫应该不会买账……不过,你不会放弃一个机会的。”
谭维惠脸上宽容的笑还没有消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档案(没错,他的内侧口袋塞得下A4纸)放在床头柜上,敬了个礼就出去了。
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由状态下现存最积极的自由派代表”的第二次会面,到此结束了。
两次,他都没给我以真诚的感觉。碍于对方坚定的意志力,我看不到他的具体想法,也看不见他的过去。等他的生命讯号渐渐消失了,我才拿起那份档案。仅看到那张照片,我就再平静不下了。
“汤腾凯……你欠我好多解释……”收起档案,我确定了一件事:无论谭维惠什么想法,也无论他怎么做到的。他一定是个危险人物。
还有汤腾凯……你可别把我要的答案,带进平壤的烈士公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