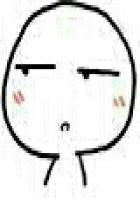男人们猛吸着烟沉思着,女人们依弄着秀发发着呆。朱琴鼓弄着双眼直望着屋顶,一脸通红。刘芳有些痴呆地望着我,一脸显出了毫无主张的模样,芳寸己大乱。我又点燃一支烟,手又习惯地抚摸在头上沉思了起来。
刚扌吵吵闹闹的场面游到了远方,死寂的场面展现在眼前。但这一切都是活动的,人人的脑子都在转动,每人的表情各一。刘芳把头伏在我肩上,脸紧贴着我的脸,低声跟我说着;
‘‘阳阳,十万是不是高了一点?他们的伤情本就无什大碍,这钱出得是不是有些冤?这工地正在半途,也正是大用资金的时候。天呀,突然抽出这二十万再加上拿去医院的就近三十万了,你叫我怎么办。‘‘她眼中的泪顺着我的脸流着。
我用手轻抚着她的秀发‘‘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亊一定照办,露出你的笑容吧,这钱我全出了。麻烦你站直了,老板嘛得有一个老板的模样,扭扭歪歪的有失身份。‘‘
那位老者对我笑着‘‘兄弟,是否可再添一点?你看他们都有一大家子,上有。。‘‘
我微笑着向他摆了摆手‘‘老辈子,你是不在其位不知这位的艰难。我己从方方面面都考虑了数遍了,一口价了,不再有上调下减的说法了。我们都是成熟的人了,别再为那一奌奌而相互伤着嘴皮了,且又费时费力。别急,再想一想,你们再合计一下吧!‘‘
他们忙挤在一块,有人在不停地说着,有人在点着头,有人在摇摆着头;他们中或笑或苦丧着脸或指指点点。我微笑着一直望着他们,也不时地向他们其中的人点着头,时间由他们撑控着。
我慢慢站起,在有限的空间踱着步,心中正沉思着他们究竟还要讨论多久?时间对我来说十分珍贵,我与他们实在是耗不起。几日来,我现在还不知我的楼建工地的基础已成形了没有?他们是否能把一切都能正常运转?还有二十几幢楼的基础采样及测绘图要搞。唉,虽说我己把那些交由马林丶马起丶粱军他们在管,但我的心始终搁置在那里。奌燃一支烟望着门外,,夕阳己悬吊在屋檐上了。
‘‘年青人,请你过来一下。‘‘老者微笑着向我招着手。
我慢步走过去‘‘老辈子,你们都商量好了?‘‘
‘‘对!一切都按照你说的办吧!‘‘他向我让着座。
‘‘您是老人家怎能给我这个晚辈让座?商谈好了就行,谢谢大家的宽容和谅解。下苦力的人养家糊口硧实不易,这样吧!我个人再给他俩各加一万,另外你们大家在这儿白白耽误了几天,我每人每天发两佰元,望各位笑纳!‘‘我轻吐着一团烟雾,望了望正乐开了花的他们。‘‘若各位同意并无别的提议了,那我们就写式两份的协议吧,简简单单的过程是要要的,这样大家的心中扌有个底嘛。‘‘
‘‘好!‘‘大家一同喊了起来。
大家都挺高兴,唯独我却乐不起来,心中总觉不是个滋味。我不是在心痛那二三十万元钱,而是担忧着今夜又是个难缠之夜。为她付出了那么多,照刘芳那性格,她定又有许多鬼主意了。唉!做了好亊会遭罪的.
我叫朱琴拿来纸笔和复写纸,写了一式四份的协议书后,再叫在场的所有人鉴字按了手印,我又分咐他选几位可靠的人明日随我到县城公证处公证后,再到县银行办理银联卡。我又叫刘芳请来财务处的人来给每人发了钱,并一再向她说朋这钱是我给她暂借的,唉,她扌免强应着。女人啊.。。
待一切都办理完后,大家便高高兴兴地便向伙食房走去。
夕阳此时越来越红了,红得有些可怕,仿佛就是我的血。黙默地跟着大家往前走,点燃一支烟,手又习惯地抚摸在头上,交织着的思索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