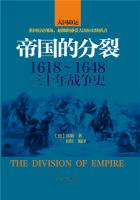第二天,素宁终于抵达了自己十个月来念兹在兹的朔方城。
跟大多数边城的形制一样,朔方城的形状有点像个“回”字,即城中还有一座小城。这座内城是用来设置郡治官署和官员住所的,周长不到二里,警戒严密,出来之后北面是成片的军营,南面则是鳞次栉比的民居和熙熙攘攘的市场。霍去病本来是住在军营之中的,但是军中不能有女人,于是他在内城的中心选择了一处宅子作为自己婚后的住所,并安排素宁直接住在了这里。
看着素宁安顿下来,霍去病说道:“我得回营中处理点事情,你在这里不要动,我一完事就来陪你。”
“嗯,你赶紧去忙吧,我就在近处转转,找一下市集和商铺,买点日用的东西。”
听了这句话霍去病却没有动身,而是很郑重地看着她,说道:“不行,你哪里都不要去,最好不离开这座宅子。实在想转转的话,必须有我的亲兵跟着,而且不能离开内城。市集都在外城,买东西这种事情以后就交给别人吧。”
素宁一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外出吗?”
霍去病叹了口气,面色严肃地拉着她坐了下来,“这是有原因的,我们得好好地谈一谈。唉,本来我是想明天再说的……”然后他尽量和缓地把自己面临的安全形势说了一下。
尽管他讲得已经很和缓了,素宁还是感到一阵阵眩晕,她这才知道,原来漠北的匈奴人早已千方百计地想要行刺大汉的骠骑将军!而只要出了这个内城,街上就会有许多说匈奴话的人,刺客若是混杂其中是很难防范的,而且这里已经不止一次地闹过刺客了!
霍去病关注地看着她的脸色,“你没事吧?我不想吓到你,其实只要做好防范,也不必过多担心。但是我要确保你是安全的,总之你不能有任何闪失。”
想象着匈奴人的毒箭飞过来的那一幕,素宁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问道:“万一箭矢是向着我飞过来……那又该当如何呢?”
霍去病把她搂住,“你别胡思乱想……正常情况下,他们不会那么傻的!你若有什么闪失,我会灭了他们全族的!”
素宁勉力定了定神,说道:“是的,杀了我只会增加你的战力,他们不会那么傻的!那么,怕的就是……”
怕的就是他们不杀、而是擒住之后作为要挟了……两个人默默对视了片刻,似乎都能听到对方沉重的心跳,考虑这种可能性确实是格外残酷,连霍去病的脸色都有点发白了,终于他还是口气冷静地说道:“我们来分析一下,一般来说也不会的,因为他们只知道你是我的妻子,但并不真正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素宁心里想道:“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哪还能让他们要挟到你?真要到了那种时候,我会立刻死的!尽管我没有勇敢到不怕死的程度,但是为你而死,我是不会犹豫的!匈奴人,你们就稳稳妥妥地等着灭族吧!”
然而看着对方的眼睛,她并没有把这番话真的说出来,只是说道:“对啊,他们并不知道我对你有多重要。”
霍去病点了点头,继续道:“所以呢,我们俩不要人前人后地显得很恩爱,最好是让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并没有多少感情。我们需要演戏,特别是我,得表现得把你不当回事才好。”
明明知道这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听到这里素宁还是忍不住泫然欲涕。唉,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美人吗?多么绝艳的词藻,多么沉重的实际!有多少甜蜜又有多少酸楚啊。
霍去病也默然了良久,最终说道:“委屈你了,朔方城的治安,我会想办法改善的。”
“有办法吗?”
“办法不是没有,只是比较麻烦而已,我一直抽不出工夫去管,现在搞得你也不能出门,我必须管一下了。”
素宁赶紧道:“我可以待在家里的,千万别为了我一个人而兴师动众。”
“也不仅仅是为了你。这一年眼看着这里的各色人等越聚越多,秩序越来越乱,但是别忘了朔方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池,它是北击匈奴的军事重镇!而且距离五属国又如此之近!地方上的事情我一向不爱管,但是现在必须给这些官员施加点压力了,这么乱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治理!”
“好吧,看来这里的地方官员要比从前难做了。”
“当然。也是我一向太省事了,其实应该让他们比我还着急才是!大司马就在他们这里遇到危险,他们这官还想不想做下去了!”
霍去病说要演戏,他也尽量去演了,可是他这段时间的幸福,无论如何是掩饰不住的。不但当前觉得自己很幸福、而且知道不久之后的自己将更加幸福,这应该是人生最幸福的感觉了吧,他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
在一般人的眼里,他很少跟人说话,形象一直是相当高冷的。他话少是有原因的:首先他是寂寞高手出身,从未像其他人那样有过与知己朋友倾心交谈的经历;其次他年少位高,又是军人,必须时刻保持严肃和严谨的形象,只说必须要说的话,措辞必须简洁、明确、规范;再者他自幼就是一个外戚,像他们这种人,既比一般人多知道很多宫闱秘事,也比一般人更清楚祸从口出、臣不密则失其身的道理。
所以他在外面只可能话少、不可能话多,像是赵破奴、路博德这些下属,都知道他从来不谈女人,其实他不谈的何止女人,聊天时除了军事话题之外,只有两个话题他会发言,一个是蹴鞠,另一个是大将军。而到了母亲、舅父、弟弟这些家人的身边时,虽然他会放松下来,话也会说得多些,但是话题范围总是不会太宽,而且在家人面前他也是有形象的,至少要满足他们对他的期待,因此他很难跟他们谈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更不可能无所顾忌地指点江山、臧否人物。
他平生最喜欢的谈话对象当然是素宁,可是在过去几年里,他们见面的次数非常有限,每次相别时都是意犹未尽,后来又只能写信,更是书不尽言。如今他的知己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每晚都能陪着他天南海北地聊天,这在他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他终于知道了痛痛快快地说话是个什么感觉。
如果周围的人留心的话,就能看出这些天里他的脾气和神情都是有所改变的,他变得特别温和善感,不拒绝任何人的要求,说话也多了,而且总是情不自禁地挂着笑容。只是周围的人都在为了即将到来的婚礼而忙碌不停,也没人顾得上留心他有什么不一样。
无论在哪里,筹备婚礼都是非常忙乱的,何况现在时间紧、事情多,朔方这种地方又采买不到高规格的东西……总算幕府中不缺办事高手,这些困难都被一样一样地克服了。习惯于号令三军的霍去病,在这种事情上也只能被动地盲从了,就跟每个晕晕乎乎的新郎一样,别人让他去做什么,他就赶紧去做什么,无条件地服从每个人的指派,而完全不理解每一步程序到底是在做什么……但是这时候又的确会感到很幸福,仿佛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围绕着自己的幸福而忙碌,而自己只要负责享受这份幸福就好了。
一切程序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霍仲孺的回信也已经带回了朔方,让霍去病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在信中告诉他,自己决定亲自来一趟。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来得居然很快。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霍仲孺为了快一点赶路,执意骑马而没有坐车。他并不是骑惯了马的人,年纪也不轻了,两腿内侧很快便被磨得血痕累累,全身更是酸痛难当,以至于都无法自己下马,就这样硬是坚持了十多天。
霍去病还记得第一次与父亲见面时,自己是差点笑了出来,可是这一次,当他看到父亲是被人抱下马来、下了地东倒西歪、被人搀扶着才能勉强站住时,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
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用几乎是埋怨的口气说道:“看你们怎么搞成这样了!这么远,又没有让您来……”
霍仲孺则连连摇头:“不是的,不是的,我来了才能心安……”
霍仲孺安置下来不久,吕老先生便前来探视了,陪着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将为何在朔方成婚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霍仲孺则告诉吕老先生,自己早就知道长子被流放到朔方了,但是并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只知道那是高层的机密的事情,平民百姓是一句也不敢乱问的,不过从幼子霍光的家信中,他知道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长子自己订下的婚事圣上并不同意。
吕老先生道:“所以,您当时是知道去病的这个决定是有违圣意的?”
霍仲孺点了点头,“我是知道的。说实在的,那天我接到他的信时,也是捧着信思量了很久。我想得出他这个决定一定是有难处的,这个时候我若是不能支持他,还对得起抬头‘父亲大人’这四个字吗?”
吕老先生既感动又欣慰地说道:“连我都不曾奢望你能亲自来到这里,如今真是太好了,你这个父亲到场,‘礼’字上面就没有一丝毛病了!去病的这个身世,让他从小因为这个‘礼’字而难堪过很多次,今天他的人生大事能够不再难堪,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霍仲孺低下头来,良久才叹息道:“唉,我也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的这份惭愧……他小的时候我不曾尽过任何责任,也从来没有为他担当过什么,这份愧意一直压在我心里,或许能借此消除一二吧?”
吕老先生忙道:“那是自然。”
霍仲孺思量了一会儿,又道:“去病非常尊敬您,我也不想把心里的话瞒着您。实际上,他的这个决定,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年,说实话我是惭愧得掉了眼泪的……不负鸳盟,这样的才是男人啊!相比之下,我当年算是什么东西啊!他的母亲让他随了我姓霍,人家一个女人也比我有担当啊……”
他说不下去了,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抬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当年在平阳府里,他遇到了那个身段窈窕、四肢修长的美丽舞女,两个人海誓山盟,可是有一天,当他知道了这个已经失身于自己的美丽舞女,竟然是长公主准备进献给天子的人选时,吓得连夜落荒而逃,什么海誓山盟都统统抛到了脑后……多少年过去了,说愧悔什么的也没有用了,也早就没脸再见一面了,他知道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只能被儿子们当作反面教材,他也只能自嘲地想道,幸好他们只是随了自己的长相,可是,天底下毕竟没有哪一个父亲,愿意一辈子只能作为儿子们的反面教材。
吕老先生见他情绪激动,默默地给他递过巾帕,再徐徐以温言开解道:“人这一辈子,只能说凡事都看两面吧!你看,就连流放也并非全无好处!去病如果不是被流放到朔方,婚礼上就见不到自己的父亲,长安那边不论排场再怎么盛大,他也一定是会有些难堪的。”
霍仲孺拭着眼泪道:“是,幸好是在朔方,若不是在这里,我都没敢奢望过还能尽上这点儿心意,也没敢想象过还能亲眼见到他的婚礼……”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春分时节,简朴安静的婚礼终于在朔方城中举行了。没有奢侈的聘礼,没有喧闹的宴席,“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喻含的是同甘共苦的结发之恩、恒久不已的夫妇之义。
两位长辈都没有在朔方这里多做停留,婚礼之后的第五天,他们就谢绝这对新婚夫妇的一再挽留,执意冒着风寒天气南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