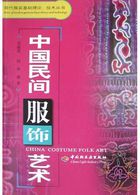午间休息时,霍光跑过来找他的兄长,“兄长,下午的射猎,我可以跟着你吗?”
他的兄长身前摆着那把太子的硬弓,正在默默地沉思着,听了他的话,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我不参加。”
“你不参加?”霍光露出了极为失望的神色,“我听他们说,往年只要有你在,别人绝对得不了第一,我本来还想好好看看呢!你若不参加,今天肯定是郎中令得第一了!”
霍去病仍然是面无表情,淡淡地说道:“我还有点事情,再说我也不想跟人比了,你去看看太子跟着谁,这几天你就跟着谁吧。”
“太子肯定想跟着你啊!”
霍去病脸色一沉,声音不大但却十分严厉地训斥道:“陛下愿意太子跟着我吗?我都说了我不参加,你还没有听懂吗?”
霍光完全没想到兄长今天的火气这么大,竟然一句话就变了脸色,吓得赶紧跑开了。
这天下午的射猎,当然是李敢夺得了头名,刘旦和刘胥都跟他一队,兴奋得上蹿下跳。
第二天上午的射猎,霍去病仍然没去参加,只是陪侍在圣驾的左右。
然而射猎的众人出发没有多久,就有个侍从火急火燎地跑来报告,“太子坠马了!”
一言未毕,刘彻已是一惊而起,连连问道:“伤着哪儿了?要不要紧?”
侍从赶紧回说并无大碍,刘彻这才松弛了一些,吩咐御医快去瞧瞧,看过之后赶紧过来禀报。
目送着御医走后,他在原地踱了几个圈子,心情逐渐由焦虑转为不满,终于忍不住对左右抱怨道:“你们说说,这么大的人了,怎么骑个马都能掉下来!”
这句话自然没有人敢接,霍去病也保持着缄默,过了一会儿,他眼看着圣上的心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便一言不发地转身出来,招手叫过自己的一个亲兵,吩咐道:“去把霍光给我叫来。”
未等亲兵离去,霍光已经远远地过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就是有话要说。霍去病把弟弟招到身前,沉声问道:“你都看到了什么?说详细点。”
霍光详细地向兄长报告了他的所见所闻。原来他奉兄长之命跟着太子,今天早上听到侍从说,昨天太子骑的那匹小马踏到了尖石,伤着了马蹄,所以今天给太子牵来的是另外一匹小马。刚开始一切都挺正常的,但是经过一个山坡时,太子的马突然往坡下一个猛冲,太子一下子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好在太子并没有受什么伤,情绪也没有受什么影响,爬起身时还笑着说了一句:“幸好我天天练铁牛耕地,坠马时还真管用!”
霍光继续说了下去:“太子一起身就换马了,那匹失控的马就有人给牵走了。但是我悄悄地跟着过去,趁人不备时看了一下那匹马的牙口,应该是五岁左右了,它只是长得矮小,也没有骟过。”
霍去病一直凝神听着,至此赞赏地点了点头,霍光继续说道:“当时大家都看到那个山坡下的树林里隐约是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一匹马,而且我怀疑那是一匹发情的母马,所以这匹成年公马才忽然冲下去的。可是好几个人都说那是一头老虎,太子的马是见着老虎才受惊的。”
“你看得真吗?有没有跟他们争辩?”
“我觉得自己看得挺清楚的,不过我没有争辩,立刻就上这儿来了。”
霍去病再次赞赏地看了弟弟一眼,“走,带我到那里去看看。”
霍光领着兄长来到刚刚发生过坠马的那片山坡,霍去病打量着现场的地形,“老虎就在这片树林里吗?太子的马一上来是往后跳还是往前冲?”
“直接就往前冲。”
霍去病冷笑了一下,“断无老虎。”
说完他就钻进树林,低头仔细搜索了一会儿,找到了几个新鲜的马蹄印,认真观察了一下,说道:“没钉马掌,应该是母马。”
霍光点点头,因为当时一般只给用作使役的公马钉掌,而母马,特别是处于生育期的年轻母马,一般都是不给钉掌的。
霍去病盯着这几个蹄印,眼神如同寒冰,按照规矩,无论大臣还是禁军,所有的车驾里根本就不可能有母马!是谁把发情的母马带进这皇家禁苑的?还正好布置在太子要走的路边上?
不管是谁干的,主管禁卫和侍从的郎中令,都不可能不知情。
霍光看到自己兄长的眼神冰冷、脸色发青,知道他这次是动了真怒。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兄长如此的怒容,他知道兵家的讲究是“善战者不怒”,人人都说大将军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动声色,而兄长呢,至少外表上也一向都是相当平静的,他一直觉得这就是卫霍两位名将的兵家风范,却没想到兄长不怒则已,一旦怒起来气势当真逼人!
他被这怒气吓住,不敢再待在兄长旁边,赶紧远远地躲开了,心中却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来:“你们这些人疯了吗?你们惹急了的可是霍去病啊!别忘了他下手是很重的啊……”
不错,霍去病此刻是真的怒了。
“你们对大将军动手,我还可以强忍,对年仅十岁的太子下手,那就忍无可忍了!在弓上做做手脚,让太子出出丑,这还可以慢慢处理,可是竟然已经在马匹上做起手脚来,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胆大妄为了,弄不好随时会伤了太子的性命!”
他本以为自己昨天在圣驾前放的那一箭,对任何阴谋者来说,都既是一个很明确的揭露、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了,没有想到居然还是震慑不住他们,他们居然还敢更进一步!
如此说来,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难道非要逼着我出重手吗?难道非得亲自尝到霍氏打法的凌厉狠绝,你们才肯罢休吗?”
更何况,他们掌握着侍从和宿卫,下起手来防不胜防,再拖下去,谁知道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他们随时可能再次动手,太子就随时处于危险之中!
在盛怒和焦虑之中,他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一刻都不能再拖了,必须现在就出手了!
“而且今天就得解决掉,别忘了,票姚的意思就是快!”
对方的要害在哪里,他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然而如何出手,却已经权衡了很久、犹豫了很久,没想到此刻一旦决定动手,所有考虑过的做法,却是一样都用不上!
因为所有考虑过的做法,都在想怎样最圆转、怎样最稳妥,而今日之情势,却是只能尽快、只能行险了!因为所有考虑过的做法,都不愿让圣上觉得自己是太子的人,而今日之情势,却是只能自己来当这个刀尖了!因为所有考虑过的做法,都想的是怎样尽量保全李敢,而今日之情势,却是只能直接取其性命了!
他犹疑了那么久,一直觉得心里很乱,然而此刻决心一定,一切却忽然在脑海中变得无比的清晰,就好像每一次作战的进攻发起之前一样!他清楚地看到,此役共有三个目标:第一,拔掉对方的要害!第二,不留退路,向圣上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三,也不给圣上留退路,逼着他也表明态度!
他的嘴角边,慢慢地浮起了一丝冷笑:“你们算计舅父、算计太子、算计储君之位,玩的不就是算计吗?真玩算计的话,你们能玩得过一个兵家吗?好,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兵家的算计!”
中午时分,霍光被兄长叫了过来,他看到兄长的神色已经恢复了,整个人看上去平静无波,正在向两个亲兵交待着任务:“你们两个到太子那里去,就说我的要求,他不得离开营帐一步,对外就说坠马了养几天伤。你们两个不要回来,必须寸步不离地守着太子,再从队里挑十个人,在太子帐外随时候命,懂了吗?”
两个亲兵领命而去。霍光看着兄长如此安排,心中蓦然明白过来:“恐怕此时已是非常之时!”
这时兄长转向他,语气仍然是平静无波:“你的任务是,下午去大将军那里,把你早上看到的事情告诉他。如果到了晚上没有什么异常,你就照常回来。如果听到什么异常,你就跟大将军说我已经算过了,风险不大,单于仍在,圣上不会动我,请他放心。”
“什么算是异常?”霍光没有听懂兄长在说什么,着急地问道。
“到时候你自己能判断。”
霍光还是没有听懂,但是他看得懂兄长的神色非常坚决,于是把兄长的命令重复了一遍,确认无误后,转身离去。
他的兄长目送他走远,回身取过太子那把硬弓,平静地瞧了瞧,微微冷笑了一下,背在了自己的身后。然后他平静地整理了一下随身的箭袋,从中取出了一支箭,在手里掂了掂,放进了帐内的箭箱中,然后把少了一支箭的箭袋背在了身上。
最后他平静地上了马,看上去一切如常,唯独此刻,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决绝之色,他端坐在马上直视着前方,就像是在战场上一样。
他的眼前,似乎再次出现了战场上刀尖对冲时的情景,只不过这次对面冲过来的,不是匈奴人,而是李敢!
谁又能想象得到人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可悲的一幕,曾经并肩作战的两把旋刀,在经历了共同的出生入死之后,他们的两支刀尖,有一天却不得不针锋相对!李敢啊李敢,在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难道就不曾想到过这种可能吗?
没人能知道事情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是谁把李敢那样一个人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员能征惯战的骁将,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即将倒在同袍的马前!没有战死在疆场,却终于毁在了权力斗争的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