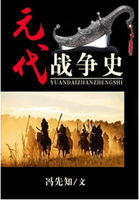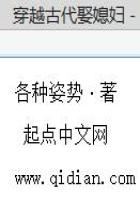那荀融面容冷肃,也不留客,待得杨忠三人出了酒楼,眼神一转,低声朝身后称心嘱咐了几句,称心得令,转身离去。
这时荀融转头看向场内,目中神色顿时变得复杂,只见他缓缓走到离韩长恭三步之处,语声有些痛惋,嘴角微颤,对着韩长恭轻声唤道:“凤凰儿,你怎会落得如此?”语音之中颇是心痛,说着便不由自主,伸手向韩长恭额角拂去。
那韩长恭方才目不斜视,依旧执着长槊在与风十里较劲,两人魂力相当,互不相让,竟然相持不下,那十方紫金槊在两股巨力拉锯之下,震的呜呜作响,竟似要折断一般。而正在此时,韩长恭忽然听闻那句“凤凰儿”,似乎顿时听闻天崩山裂之音一般,顿时气机一涣,转过头来。
却说风十里方才为了相救忽赤尔丹这个投缘的酒友,挺身当下韩长恭这一槊,但由于韩长恭魂力实在太强,两方相持之下,却如同骑虎难下一般,既占不到对方便宜,又不能松劲变招,否则便如同有性命之危,因此风十里不得不振起全身魂力,心境冥定,全力与韩长恭对峙,便连荀融一行人进入堂中也不知。
正在运劲之间,风十里却忽然觉得对方劲力瞬间涣散,他不由得大惊收劲,但却已然救之不及,只见槊尾一挑,长槊挟着风十里魂力,荡开韩长恭执槊右臂,瞬间将韩长恭震得脸色煞白,接着便刺向呆呆看向荀融的韩长恭胸口。
却见这时,方才一直跟在荀融身后的枯朽老仆忽然两步踏上,挡在韩长恭身前,双指点出,瞬间捻上槊尾,接着肘随肩动,带着槊尾凭空绕起了大圈,途中肩膀撞顶在韩长恭腰间,将韩长恭挤开。那老仆便这般牵引着槊尾绕了三个大圈,已然将长槊上风十里来不及收回的劲道解了,只听得“咣当”一声,长槊落在地上。
这边韩长恭被那老仆棉柔之极的劲力一撞,拿桩不住,便随着那股劲力,扑通一声跪倒在荀融身前。这时风十里收了劲,也转目看向荀融这边。却见荀融将手伸出,按在韩长恭太阳穴上,轻轻揉按,道:“凤凰儿,回来吧,到家了!”
却见这话方才说完,韩长恭俊秀的脸庞忽然扬起,怔怔地看向荀融,口中呜呜有声,竟似是低声哭泣,半晌,呜咽稍停,韩长恭似乎大梦初醒一般,四周看看,又复看向荀融,似是心有喜意,开口道:“永固,你来了?我……我这是在哪?”说着茫然站起,四下环顾。荀融这时向那老仆打了个眼色,那老仆会意,双指一骈,点中韩长恭巨骨穴。那老仆劲力透入,加之韩长恭此时已然是强弩之末,便即软倒。那老仆拦腰将韩长恭扛起,拾起韩长恭的十方资金槊,侯在一旁,等待荀融指示。
却见荀融这时似乎略为颓丧,自顾自走到盘膝而坐的风十里身旁,在方才风十里坐的长椅之上。将那胡没碎的刀如烧提了起来,对着坛口,便大口喝了起来,许多酒浆洒在他的狐裘围领上,他却全然不觉,只是默然喝罢,嘴角露出狠色,恨恨道:“何人伤我凤凰儿如此,我若得知,必万剐之!”说罢,忽然将那酒坛摔在地上,酒浆飞溅之下,风十里面上、衣襟上也沾了些许。
荀融这时转头看向风十里,惨然一笑道:“叔父勿怪,小侄方才是一时失态。”
风十里抬袖子擦了擦面上的酒浆,笑道:“无妨,多年未见,却不料凤凰儿此时已然如此骁勇了!”言语之间,颇有暖意。
荀融正待回话,却忽然听得脚步声响起,却是称心慌慌张张跑回,边跑边叫道:“公……公子,不好了,白狼寨的土匪又下山来围猎了,现在难民无处可去,都朝这边围过来了!”他说得惶急,加之他是少年嗓音,在此时听来异常尖锐。
荀融闻听这话,问刚跑进酒楼,仍在气喘吁吁的称心道:“你没听错?确实是白狼寨?怎么会这时候来?”
称心喘了一大口气,道:“没,没错的,虽然天色暗,但我也远远看见了,那领头的,确,确实是披着白狼皮披风的匪徒。这次来得似乎比前几次要迅猛得多了,我本来想要回府调人,但听说那帮贼人一上来就硬闯荀府,攻不下来便转来西面,据说还抬了口棺材,放在了咱们的府门之前,可嚣张了!称心想到公子安危,于是便回来报讯了。公子你听,那些匪徒正朝这边来哪!”
众人这时凝神听去,却是听见四周有类似狼嚎一般的声响正在快速靠近。那狼嚎夹杂着马蹄之声,和难民奔走的呼叫声,一时如同潮水一般围近,但到得将近一里开外,似乎遇上了什么阻碍,声响稍降,但仍有数骑奔驰而入,向酒楼围来。
这时边地战乱,乱民纷起,这山贼若是在寻常年月里本不足为患,但如今百业萧条,难民如潮,连山贼也抢不到粮食,自然是较以往更为凶残狠辣,加之难民若是害怕逃窜,便又会形成难以抵抗的人潮。而这些难民本就是食不果腹之人,若是裹挟在山贼之中,难免也会成为浑水摸鱼的盗匪,而且这些难民往往对有余粮的富户心有仇怨,因而往往会害的富户家中不只财粮一空,往往人也无端丧命。因此这月余来但凡遇到白狼寨下山,建昌城内有点资产的家户都会认为是大难临头,要不便是深墙高院,闭门死扛,要不便是匀了家财,给地方大户纳了孝敬钱,让大户集结乡勇,对抗山寨。
而这地方大户本来一直是黄家大院的黄鹤黄四郎扮演,但谁料几个月前却被一股无名的流寇张麻子攻破防卫,闹得倾家荡产。好在荀家也是富户,这黄四郎虽然走了,荀家便当起了这护卫地方的重责。这荀融却也是颇有将才,带着家将围剿了两次白狼寨,那个曾经危害一方的白狼寨竟然就此一蹶不振。但这番白狼寨能卷土重来,却不知道又是何来的实力。
只听得这时柜台前忽然“哐啷”一声响,原来是齐夫子这时吓得心惊胆颤,蹑手蹑脚遥朝后堂缩去,不料途中却由于太过紧张将柜上的泡酒坛子打翻了。
风十里缓缓站起,拍了拍齐夫子的肩膀,道:“这里人多,便算是盗匪来了也可保无妨。”
这时二楼客房的门忽然“咿呀”一声开了,织田高虎拄着手杖,道:“荀公子,可需要织田相助?”
荀融却不看向织田,兀自凝神细听,半晌,长舒了口气道:“织田长官不必操心了,那匪徒今次的呼喊声调有异,似乎并不是志在此处,且他们此时已然力竭,应会退却。小侄的家将此刻应该已然赶到了,此地应当无虞。”说着长身而起,让那老仆背上韩长恭,带着称心,也不管堂中之人,便自出楼而去。
织田皱眉细听,果然听得那呼喝之声至楼外半里之处,便似是遇上了阻碍,不得不折返而去,而那撤退的号令似乎并不是狼嚎,而是某种奇异的鸟鸣。织田不由得觉着好生无趣,打了个呵欠,便入房而去。
堂中的风十里看着荀融离去的背影,不由得摇了摇头,自语道:“断事果绝,临阵不惊,敢怒敢爱。阿岘,你的孩儿果然大有你的风范啊!”说着轻轻踢了一下醉卧在自己脚旁的忽赤尔丹,有些恍然若失地自语道:“兄台胸襟宽宏,定非常人,但风某觉得有幸之处,便在于能与兄台纯以酒量相交,不涉名份。愿他日相会之时,你我还能是这般不明身份的酒友!”说着也不看忽赤尔丹,不顾褴褛衣裳,行出殿外。
待得风十里走后,齐夫子见忽赤尔丹醉成了一滩烂泥,正待上前将忽赤尔丹轰走,却见忽赤尔丹这时终于悠悠醒转,坐起身来,转头四下里看了看,咒骂道:“妈的,才睡了一觉,人却都走了,好生无趣!”说罢又抱起酒坛喝了半口,接着从腰间中翻出些碎银子,朝着一旁的齐夫子打了个酒嗝,道:“给我开间上房,我也要住店!”
那齐夫子经历了今日这许多周折,眼见这忽赤尔丹深浅不明,正不知如何是好,却见忽赤尔丹从怀中捞出一份镶金边的考究拜帖,递给了齐夫子,接着头一歪,竟然又昏睡了过去。
齐夫子摇头叹气,接过了那拜帖,却见帖子上写着“诚邀荒古使者”的字样,不觉一惊,当下将那拜帖揣入怀中,俯身将忽赤尔丹架起,扶上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