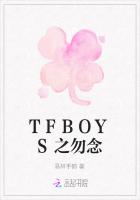朱武乐呵呵的走回自己的房间,才走到门角,“哗”的一声从门壁里扑出一个人来,娇脆的声音:“惊不惊,喜不喜?”
空气中发散着诱人的香气,彭品娟在他的面前笑得灿若花开:“我来了,你欢喜得说不出话?”
他可以说话吗?的确是又惊又喜。
门卡被她抢了过去,“叮”的一声她进了门,再伸手把他一拽便扯进了房里。
朱武无助的望着因她的到来而明媚了的壁灯:这千山万里,她竟然追了过来?
林和言一脚便牛气的把聂皓天的手下给赶了出去。仗着身上还剩余的一分酒劲,向着坐在床边的聂皓天懒散的敬了个礼:“首长好!”
自他突然闯进,聂皓天便一副冷酷神色。林和言给他敬礼,他眼睛也没抬,冷漠的道:“我是司令,你是团长。我大你多少级?”
“司令,大我……”
“陈军长就是这样教导你的吗?半夜三更,一身酒气,冲进首长的睡房?”聂皓天突然站起,眼睛瞟一下他的腰际:“还带枪?”
“聂司令恕罪。”林和言的酒气“嗖”的飞走了,额间开始冒冷汗。
聂皓天虽比他年轻了近10岁,从前还在他的手下短暂的谋过事,但现在却已官至司令,领上将军衔,军队中,职级职务之间的分别最是严明。
他这一闯,便是犯上作乱,真是鲁莽了。
聂皓天靠在床沿,冷漠的表情,阴鸷的笑意:“林团长因为个人私仇,今晚携枪闯入,意图行刺首长,这罪名,你领得起?”
行刺首长?这罪名安得有点大了。林和言急急的反驳:“聂司令,你不能含血……”
“绑了!”
“是!”不知何时,门口暗角处竟站着一个便装的战士,只一招便把他整个人控制得严严实实。
被突然袭击控制的林和言顿时慌了心神,哑声哀求道:“司令,是属下的错,你大人有大量。”
“我从来都很小气。”聂皓天懒懒的,手掌在被窝里伸出来,抚上某女人的额头。女人“嘤”了一声,很娇很软的声儿。
林和言这才发现,床上竟躺着个女人。他半夜撞破了聂皓天的情事,怪不得会惹他发怒,要绑自己。
林和言被自己蠢哭了:“司令,前晚军营失火被烧,档案资料大部分消失不明。属下一直求见司令,却不得接见,因此才情急之下闯了进来。实是希望求见司令,指点明路,以取回兵团里的重要资料。”
“林团长言下之意,是怀疑那些资料都在我这儿?”
“不,不敢,绝对不敢。”林和言平日的霸气威风,现时被折得一分都无:“聂司令,当年我们也曾经共过生死,这,这……”
“这全军上下,有哪个没有历过生死?”聂皓天更冷了:“历过生死就能对首长不敬?历过生死就敢携枪闯我私人住处?林和言,这些年,你的兵白当了?”
“是,聂司令教训得是。”
“既然你也觉得有道理,那就进局子里,好好反省反省。”
“啊,司令,司令……”林和言求放过的声音在走廊外越来越远。聂皓天无言摇头:徐展权,扶的都是这些脓包。
脓包就脓包吧,居然还弱智,弱智也算了,居然还鲁莽……
他在沉思,大手却被一双热乎乎的小手握紧。不得不说,在这冰冷天气里,被这么一双温热的手握着,软绵绵热乎乎,还真是让人的心情瞬间转了个调。
刚才这一场大戏,林微虽在病中,却也瞧出了些端倪。她身子发软,全身骨头酸痛,可见这回是真的生病了。
但她此时只注意到一个问题:“绑那个人的兵,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瞪她一眼:“军事机密。”
她急了,坐了起来,眼里的急切之色,让他意外得很:“怎么了?”
“难道,平时,你身边总有人的?”
“像我这种级别的,难道不应该有一两个隐形保护者?”
“隐者?”她尖叫了,摇着他的胳膊:“你是说,这些人平时藏着,时时刻刻监察着你的动静?”
隐者?亏她想得出来,又不是拍武侠剧。
“烧糊涂了?”他抬手抚一下她的额,她却更焦虑了,简直急得全身都是抖的,因发烧而通红的脸颊,抿得紧紧的唇:“死了,那我们以前,那个那个的时候,全被看到了?”
“什么那个那个?”
“你和我做坏事的时候,他们也都在,对吗?”
他无语的侧过脸,差点便忍不住笑。
以他的职级,平时当然会有卫兵保护在侧。但都是暗中保护,不招人耳目,也不会惊扰他的日常。林和言自走进酒店大堂起,便在兵将的监控范围之内。他上来进房,卫兵当然便紧跟着,以防首长受伤害。
虽然也是布防严密秘密,但说到会看他和她“那个那个”,那真是天方夜谭了。
那些时刻,他怎么会留几个“隐者”潜伏?即使她不害臊,他还要面子哪。
他认真的回答她:“是的,看见了,也听见了。”
“噢呜……”她趴在床上,这回是再也起不来了。
“唉。”他轻叹气,瞄了一眼大被蒙头羞愧难当的她:“烧退了?”
“那么大的打击,能不退吗?”她慢吞吞的坐起来,人还在晕,嘴边被塞了个大水杯。他一边给她灌水,一边说:“给我全喝光,然后上医院。”
“我烧退了,我不上医院。”她很可怜地:“我都躺多少次医院了?”
“怕躺医院就不要总抽风。”
“我是伤风,又不抽风。”她大眼睛眨了眨,又欢快地:“你陪我去?好咧……”
看她跳起来穿衣的动作兴奋,他本来还想陪她上医院的心情登时便往下沉。现在,看她欢脱,他的心里反而极不舒服。
为什么她能这么欢快欢乐,而微微却要永远的离开了他?
“你自己去。”
“喂,我生病了。”她一枕头扔向他,他接住软绵绵的枕头,脸上冷漠冷冰:“郝清沐,别再装,我不受这一套。”
“不准再叫郝清沐,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她对着他吼,他极鄙视地:“这是你本来的名字。”
“什么叫我本来的名字?”她讶然,纳闷为什么最近他的态度如此反常:“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