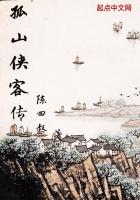眼前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眼睛有棱般锐利,两道横眉此刻成了倒八字—“丷”皱着,鼻端如胆,脸色横峻有怒。
头裹一块红布,脑后两鬓长发散开,身穿一件黄色丝绸云纹短袄,内服红衣长袖,手腕紧绑,手心下压着腰刀刀把。下穿红绸长裤,腰悬黄绫装饰腰刀。
其身后不远处有奔来的旗手打着杆长旗,借助火光的照亮、可以看清打着一杆“韦”字淡黄底色蓝边旗。
夏诚急忙抖手的将刀侧旁松手一丢,自身却急向后退了两步,让自己身后陆续涌来的士兵护住自己后,这才提手喝指道:“什么人?怎么混在清妖的队伍里?”
夏诚倒打一耙,倒先撇清了自己劈砍之责!
那人不说话,反而看着山岭上涌下的太平军士,凌厉眼神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一旁亲军指骂道:“大胆,此乃右军主将之弟—太平天国国宗、韦俊韦国宗!你怎敢意图伤害在前,无礼放浪在后!不惧太平天条吗?”
夏诚一时忍住没说话,夏诚自己任命的假书办吴公九却见自己的“小老板”吃憋,急忙跳出来分担火力。
“谁知你们是真是假?又是不是冒充的?”
吴公九前半额头发还不长,后半脑辫子解开后头发则相当长,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1)般,整个人涌出人前、指责发问道。
夏诚心里十分高兴,心道:“好一条忠犬!不枉我救你,说的好!就该这么说。”
也抬眼看着眼前的韦俊一行人做何回答。
“大胆!你…”
韦俊挥手止住了亲军的叫喊,平声道:“我就是韦俊,你们不要害怕,快去找来你们的旅帅,我有话要问他!”
夏诚的士卒们皆望向夏诚,夏诚见躲不过去了,也光棍的偏头一抱拳:“在下就是,不知道韦国宗有何见教?”
韦俊倒有些惊奇于夏诚的年纪,上下打量了两眼,责道:“你倒是胆识过人,人小好胆!”
“国宗客气!”夏诚却毫不掩饰。
“我倒要问问,谁给你的胆量扣押同级旅帅,无上司任命,就携卷全军,来此要地,又不发行文,就开仗以报私仇?”
韦俊的右手捏紧了手里的腰刀把手。其亲兵们也都捏紧了手里兵器。
夏诚知道这话里带着坑,不能贸然回答,如果细谈这件事,肯定得背好上几个罪名。
夏诚干脆道:“国宗没听说过“初生牛犊不怕虎”吗?”
这句话看似像是为自己鲁莽行事的辩解,又像是对自己敢独自带领一群不服之众来夺清军炮岭的行为与勇气的赞扬。
韦俊“呵”笑了一声,他却不管,扬手道:“前营旅帅朱灿在哪里?请叫他出来答话。”
韦俊夜出水窦要塞,出来后带着人到达高坡边口土垒处,由留守前营士卒向其讲明情况,韦俊还是判断不了夏诚究竟是真打石燕岭去了、还是借此卷席全军去裹降清军。
随即调集其余三垒士兵,一路准备好火把,但不打出,暗地行军尾随,以好不使别人发现,来以此击溃不曾提防的敌人!
未料夏诚的一枪一弹未放,就夺了石燕岭,接着清军近半数出动,他明显发觉到这是个机会。
于是下令,禁止燃起火把,直往清军山岭下靠近,清军一个个直在意山岭,对周围疏于防范,等韦俊的部队经过八旗兵逃跑的小道,大部靠近到近前,猛然间纷纷燃起火把杀来时,猝不及防下的清军顿时被太平军冲杀的大乱。
山岭上夏诚部见状又复杀下,两部太平军相向杀进,夹在其间的不少清军立时成了刀下之鬼,好在夜晚,清军丢下火把乘黑四下躲草一逃,太平军也看不见。
此一战杀死杀伤九百余清军,清军因慌乱四下又散去四五百,逃回营清军不足三千之数,虽然散去的四五百第二天又陆陆续续回来了。
现在韦俊要见朱灿,他内心其实对夏诚这样的刺头也不知道怎么处置,用两句话可以形容:“爱其才能,恨其无上。”
故而欲借朱灿之口对其处置一番,磨磨夏诚傲性。
等朱灿被眼睛有些发红的崔拔由山岭上带下,再次带到众人之前时,之前绑的绳子早已经解了。夏诚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即将到来的处罚,心里恶气气道:
“打骂什么的不怕,贬官也接受,要是让老子受刑让老子受死,老子当即就打死面前你们这群鸟人、扯旗拉杆子单干!”
“拜见韦国宗!”朱灿单膝跪地拜见。
“朱灿,夏旅帅是否胁迫威胁与你?实话说来,我自为你做主。”
韦俊目光炯炯望着他。
“没有,是我自己想来的,与夏旅帅无关!”
谁知朱灿下跪半腿,抱拳行礼道。
此语一出,两面众人皆惊,内心皆道:“什么鬼?”
夏诚更是想到,难不成这人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
“你不要怕,我现在此,无人敢胁迫于你!”韦俊皱着的眉头更深了。
“在下人头可去,胆色尚在,若我不从,谁人可以言语威逼胁迫于我!”
朱灿毫不给韦俊面子,直冲冲回答道。
韦俊知道这里边肯定有相当多的弯弯绕,但他已经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不好再随意无理由的去处置隶属杨秀清的中军部属。
最后反复看了看夏诚的队伍,一挥手,带着自己召来的人返身走了,同时拿着马鞭对着夏诚留下一句话,“好好守住山岭与土垒,磨磨性子,不要太自傲了,夏旅帅,这话对你是有好处的。”
夏诚抱拳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的回答道:“紧遵韦国宗教诲!”
待到韦俊一伙走了后,夏诚等一众人回过头来都好奇的看着朱灿,夏诚稍昂首笑道:“朱旅帅,怎么这么好说话啊?你不是不服我吗!”
朱灿瓮声翁气的道:“休谢我,去谢你的崔“铁脸”好了!”
夏诚闻言看向崔拔,这才发现崔拔脸上及右眼发红,像是被人狠狠扇了几个耳光,复又在右眼上打了一拳。
原来刚刚崔拔跑回山岭顶上去带朱灿,去解朱灿绳子的同时,崔拔希望他能够顾全同属中军一师的大局,不要将夏诚向隶属右军的韦俊恶语供出。
由其他各军的人来处置中军部属,这样他朱灿在杨秀清面前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朱灿嘴上被勒的像牲口的草绳一被其解下,当即恨恨的对着当初拿草绳子勒他嘴的崔拔道:
“如果你也让我脸上狠狠揍一顿出出气,只要这气一顺,我就不告了!”
崔拔果真解了绳子站着不还手的让他打,朱灿也果真不客气,对着其脸就是一巴掌,崔拔不还手道:“顺了吗?”
“还没有!”“那继续”
“啪”朱灿反手又是一掌。
“顺了吗?”
“还没有!”“继续”
一连扇了七八掌,扇的崔拔腿不由自主的后退,但崔拔一遍遍的尤站直让他打,问道:“顺了吗?”
问恼怒的朱灿对着右眼就捣一拳。当即将已经站立不稳的崔拔猛打倒在地,但崔拔又复爬站起来,道:“顺了吗?”
朱灿甩了甩手,心里对这家伙算服了气,道:“顺了!”
“走吧!”说着一脸伤的崔拔面色平静的带他下了岭来。
夏诚眼神复杂的看着朱灿与崔拔,崔拔自从被自己提拔以来,可谓一直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和与不同常人的果敢。
远的像火器营处成,新圩战场与乌兰泰重纶等人交兵时,新训练成的火枪士卒一个个惶恐不安,是崔拔虽无命令、就首先拿长矛戳死了想要逃跑的左茂之弟,夏诚上去才复给一刀,这才震慑住了奔溃的队伍。
近的像刚刚朱灿不服,抓他的瞬间,崔拔就自己急用绳子勒住了其欲叫喊部属的口,使其无所发声,保障了夏诚接管部队的成功。
诸如此类,一直总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默默地以更好去做事,夏诚对其没有说什么,直接将刚回到自己手里的马刀丢给了崔拔,以为对他的奖励。
又类似记住此次崔拔折辱付出的信物。
夏诚又对朱灿眯眼发问道:“我该给你说些什么呢?”
朱灿却单膝跪下偏头抱拳道:“现在我却服你做师帅了!”
夏诚人小斜眼藐道:“为何?”
“我以为你十几岁、又属刘师帅亲戚,前不久还在古苏冲被一群鸦片兵打败了,是个浮浪子弟!
我不想受饭桶指挥,故不奉命,但今夜一战,我才发现胆气豪情不及你,你若不死,必成大器,在你手下不算埋没我,我故此愿服之。”
夏诚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将其放了,让他去守高坡土垒去了。
石燕岭顶上根本扎不下这许多人日常的休整与吃饭。
夏诚干脆留了焦宏的队伍在山岭上,他领两旅之兵扎在土垒与山岭之间。
一连十几日,清军大营炮弹集中开始猛烈轰打石燕岭,尤其是第三日,清军调来桂林城头的三千多斤的大铜炮。
山岭上焦宏的队伍被炮轰死许多人,几天后焦宏就“受不了”,罗三炮带着他的口信急忙下来求援,再等到夏诚带着人跑上山岭时,焦宏就在这一晃而过的功夫里,因在山顶的帐篷里他的过于显眼,直接被一发炮连人带帐蓬轰了个稀巴烂。
罗三炮直抱着一堆碎肉大哭,道着焦宏以前的自封、威德王什么的,想来这焦宏的野心还未施展,自己的野心与身体就被轰了个稀巴烂。
估计这焦宏有些死的不心甘情愿!
夏诚见这山岭根本没法儿守,又见清军因为大败缘故不派人上来攻打,只是一昧的对准山岭顶上营寨旗子放炮,夏诚干脆派人扎了些草人,干打了些旗帜。
将后营其余人交由罗三炮代领,都撤下石燕岭来,清军派人的斥候根本无胆跑近山岭上近前看看清楚,误见山上影影绰绰,把草人当成了真人,一个个跑回去禀报,大炮又一连轰了好些日子的草人。
在来援水窦十五日后,太平天国“兵部”下令撤回夏诚所属一师回永安休整,由他部前来轮替。
夏诚于是下令收拾东西,七门缴获的虎墩炮也被他抬走了。只留下两只缴获来的八百斤的大将军炮送给了水窦要塞,这东西太重,又费火药,日后永安突围,这东西可不好带,夏诚干脆做了顺水人情。
千余队伍进入要塞防线、一路朝着永安方向行进。
夏诚看着自己队伍由十五天前来的一千八百多人现如今只余一千三百余人回去,还有不少伤病员,来时两马并行,归时两马并行,只不过另一匹马上坐的是于贵了,心里叹了口气。
而城里的洪秀全,此时正躲在“太平宫”里与自己的娘娘们打量着自己身上几天后要举行封国大典的锦绣黄绸衣服是否威严合身。
能否符合天王的气派。
作者的话:历史上任何开国帝王将相都是踩着一路的尸骨走来的,他们场面多华丽,地位多高贵,其下则不知道充填这多少的血与肉,一将成名万骨枯,人们永远只记得成名的将,无人会在意枯的万骨,仿佛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马上要写到永安建制,夏诚能否正式继承刘老二的位置,永安建制对于太平军及清军有何影响,赛尚阿一直以来藏着掖着的“鬼胎”听闻永安建制后放出,即将在永安城里嫌弃何等风浪,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节——永安建制!
文中释义:
(1)刘海仙:指五代时的刘海蟾。相传他在终南山修道成仙。流行于民间的他的画像,一般都是披着长发,前额覆有短发。
(2)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