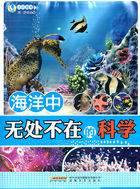这天是腊月二十七号,已经快要接近春节的日子。一大早的时候,天才蒙蒙亮,一声声凄厉的尖叫伴随着匆忙的脚步声吆喝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这声音直钻入内房里,沉睡在梦乡中王续缱很快就被这声音惊醒,她赶紧把被子用头紧紧的捂住,想是那杀猪的屠户又过来了。
在小时候母亲刚过世的那一年里,好奇心驱使着她和弟弟王续征两人,缩在厨房那扇油得亮汪汪的大木门的后面,捂着嘴巴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群大人挥着他们粗壮有力的胳膊,前面两个人摁着猪头,扯着猪耳朵往前进,后面的人只管推着猪屁股往前拱,但是那猪却不肯妥协一样,它似乎也能预感到生命走到尽头的讯息,却还是要做着并不管用的垂死挣扎,它被强迫性的推着往前赶,四只蹄子硬生生的往前拖,在地上撂下一道道很深的印迹。他爹爹王文以前也是其中拉猪的一员,后来家境好了些,家中米铺里请了一些壮实的伙计,逢年过节的杀猪这重任就交给他们来干了。
两个人掩藏在木门后的的身影显然不够隐蔽,看到那猪被拖到院子了以后两人就被乳娘满云发现了,她絮絮叨叨的对着两姐弟又是一顿说,哎哟喂我的两个小祖宗,这污秽的东西小孩子可不得看见,当心着阎王爷来挖眼珠子,快走快走快走。
她听到要被挖眼珠就冷汗直冒,王绪征更是夸张,哇的一下就嚎啕起来了,我不要挖眼珠子,我不要我不要!乳娘没办法只好把他抱起来,一边拍着他的背轻声哄着一边往厢房那边赶过去,走去厢房的路还是要经过院子的,那时候他们已经合伙把那猪放在院子里的案板上给开膛破肚了,被开水烫过的猪身热气蒸腾的冒着白色的烟雾,肠子和各类器官外露,血淋淋的看上去很渗人,空气中还有一股子令人作呕的味,王续缱紧紧拉着乳娘满云的衣角胆战心惊的绕过两桶冒着热气的猪血,听着乳娘在前面不住的咂嘴道罪过罪过,她心里却只是惧的慌,联想到人体的处境,步子也不由的颤颤的发抖起来。
她自小就不像弟弟一样爱哭,遇到恐怖的事情只是觉得心里充满了无望的畏惧,像深陷一个暗黑色的泥沼里,别人进不来,她也出不去,也不知道怎么去拯救自己。她有什么事情大部分都是在心里吓自己,不能哭出来释放情绪,这多难受呀!那么血粼粼的场面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特别还是挖眼珠子的传闻,脑海中都能自动构思出来那一幕,锋利的刀边儿上还滴着热血。所以当她数年后回想起来那些情境,还是清清明明的历历在目。
从此以后的每一年,一到杀猪的这天,为了逃避这血腥的一幕,她总是会故意起得晚一些,听到这凄厉的猪叫声就会条件反射性的吓得在被窝里面裹紧了自己不敢动弹,心里也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着。弟弟却不是,他早已挣脱了那种恐怖的吓小孩子胡塞的鬼话,约着邻居的一群孩子在门口放鞭炮正开心。
说起来她今年也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
她家出落在一座小城里,今年夏天的时候她就自学堂里申请退了学,学校里天天之乎者也的有什么意思呀,这个年代,家里也不是特别注重女孩子文化培养,就随了她了。
她生性散漫,爹爹千辛万苦安排她进这边唯一的一家纺织厂当女工,那可是不得多的一个香饽饽位置,活计轻松,时间也自由,适合女孩子,却没想到一个月都没待满呢她就撂担子不干了,由此便被爹爹好一顿骂,说她也太不争气,要知道,为了安排她进工厂,可是费了她爹好几罐好茶叶和好酒呢。
无奈之下,他爹就只好让她就在家看着自家的米铺,仓库没库存了就开始订货安排着伙计去桥头把米运过来,自己也跟着过去点点数。整个县城里就两家米铺,一家是她家,还有一家人信徐。
只听说那徐姓人家的婆娘泼辣霸道的很,自家管事的却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相必是在家被他娘子的怒骂熏陶的久了,养出这幅性格,没有一点男子气概,是附近出了名的妻管严呀。
相比之下,王续缱爹爹为人虽圆滑,却也厚道,跟左邻右舍的关系也相处的很好,细说来,两家相比却还是她家的米铺在县城里名头好些。
在米铺里熬着熬着,半年时间晃悠悠的也就这么过去了,眼看正接近年尾,前段时间两家人碰巧同时去桥头运米,却不想为了一袋米而争执起来,争着嚷着,双方就打起来了,她哪里见过这种情景,顿时便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好了,心中只是不知如何是好,眼瞧着对方把米袋撕烂,米洒了整整一个码头,惹的旁边看热闹的人群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
果不然的回家了又是被爹爹说教了一顿,这会她的气可还没消呢,她已经好几天没去米铺了,铺子都是家里的大小子放假了得闲在看着。
这会儿,她正捂着耳朵烦躁着,只希望院子里那堆屠杀的场景越快结束的好。
到了中午,留下那屠户在家里吃饭,刚刚宰好的猪被拿来做现成的肉菜了,桌面上一眼望过去几乎都是肉,中间还盛着一大碗肉汤,浮在表层的是一层厚厚的油花和肥肉,瘦的都沉在碗底了,她看了看就顿时没胃口了,乳娘还专门每人盛了一碗汤放在跟前,叮嘱着要他们一定喝光,她看着弟弟王续政美滋滋的小口啄着上面的油花,大口咬着五花肉,心里头更腻的不是滋味,吃了一小碗饭就回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