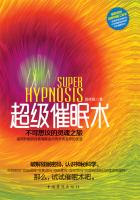东天熹微。
武林无神的看着破了个大洞的屋顶,雨水从那里落下,风也从那里灌进来,本来还点着两根蜡烛来着,倒是没有被风吹灭,可是已经烧完了,蜡油流淌的满地都是。他已经很久都没有移动一下了。
他是被痛醒的。背后被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前后透亮,血都要流干了。白玄找到他的时候连生命气息都要没了,可随着白玄施展手段为他吊命,他竟然挺过来了,却没有再苏醒,一直昏睡着。
直到将近黎明,他才被自己的伤口痛醒。
他的手里还攥着一块破布,醒来时第一眼就看见了。是白玄临走前留给他的,上面满是潦草的字迹,看得出来很急。那块破布上说:
武小子,现在我要叫你乖孙了。
乖孙啊,我要走了,还会回来,也许不回来了,你不用来找我。你总说我装高人装的很累,连说话都拐弯抹角,今天我就不跟你矫情了。
你是我看中的孩子。
定当光芒万丈。
乖孙,好好活下去,要成为让自己自豪的人,我老了,没有做完的事情就要你接着去做。赞了些银子,还等着你长大些,就给你说门亲事的,也没法子了。还有我种的那些花,你要是能照看一下就看看,我可不想就剩下些花枝,还有那壶醉国春,我连尝都没尝,还有,狮子心保管好了,还有,那株一直没开花的树下,还有……
还有还有……
絮絮叨叨的,真不是他的风格。
武林低垂着眼帘,枯黄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留下一只无神的眼睛。只是有风从残破的门前吹来,拂动碎布,他才会下意识的把拳头攥的更紧了。
还紧紧抱着王友媛的脑袋。
他轻微动了一下,把王友媛在怀中挪了一下位置,好让自己能直面的看着她。她不再漂亮了,她原本是那么漂亮,光可动人。现在她苍白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了,都顺着脖子流到武林的衣服上,她还睁着的眼睛是那么浑浊,武林却依旧能从其中看见自己鬼一样的脸。她原本抹了蜜糖一般的嘴唇也不复红润了,干瘪下去,他伸手在上面摸了一下,含进嘴中,身体颤抖了一下。
良久。
他把脑袋垂得更低了,肩膀不住的抖动。隐隐的,有声音顺着风离去。
“不甜了……”
这是一处破损的香火庙,建立于百余年前,坐落在云城靠北百余里,积攒香火。平时人烟稀少,再加上地方偏僻,香火少得可怜,这里原本有一座村庄,后来也都迁走了,更是没有香火气,久而久之也就破损了。
那尊受人供奉的菩萨金身也破损了。似乎是年久失修,下半截碎了,从腰部断裂,或许是天意,上半身整齐的落在高台上,竟还能保持着完整。头顶那破了个大洞的地方正好就处在菩萨金身的上方。
有一柄红纸伞遮在菩萨的头顶。
为她遮风挡雨。
随着时间流逝,有更多的香火庙建立,也没人还记得这里还有这么一座供奉庙。能陪伴她的竟只有一柄纸伞和夜寻的老鼠,何其可笑。
武林拖着身子靠到了菩萨身边,和她背靠背,把头后仰担在菩萨的肩膀上,感受风拂动王友媛头发时的温柔触感,在她脑袋上轻轻地拍。
他忽然想起他们相遇的那一天,天上飘着大雪,她一袭红裙在雪白的天地间就像是一朵独放的花,红裙起落间,沾染了雪尘和人气,于是他觉得这寒冷的天都变得美好了。他们相知相遇四五年,他怎么也看不腻她的好。
那么好……
怎么能死?
他忽然伸腿,把杀生踹出去。这杆枪一直倒插在一边,此刻被武林一脚踹开,盘旋着在地上绕了很多圈,撞在墙壁上才停下,那圈铁环晃荡两下,便没了动静。
一切都悄寂起来。
武林醒了睡,睡了醒,再睁眼时竟已月上中天。清寂的月光照在这片残破的土地上,照亮了不眠的天地;照在沉了一般的运城上,照亮了血流十万里;照在这座香火庙上,顺着那个破洞,正好全都映在了武林的眼中。
一切如此静谧。
他看着拇指上的狮子心。那个白发老头原来这么厉害,原来有那么多的故事,原来有这么沧桑的眼睛,他会讲故事给他听,他会教他什么是武士的荣辱信誉,他会和他一起插科打诨,就像是亲兄弟。
亲兄弟……
也只剩他一个了。
怎么能死?!怎么能死?!那可是他唯一的了,唯一的家人了,唯一的憧憬了。现在他没了,她也没了,从此就又沦为孤家寡人一个,一切都晕自己无关,沉默的吃着碗中的残羹剩饭,活的像只野狗。
野狗?
野狗……
武林忽然跌跌撞撞的跑出去,在墙角捡起杀生,回到菩萨的身后,和她靠在一起。他抱紧王友媛和那块碎布,把杀生举过头顶。他在忍不住颤抖,举枪的手一直晃动,锋利的枪刺就悬在他的头顶,在月光下映射冷厉的光。
他要自杀,他不想活的像只野狗。白玄没了,王友媛没了,家没了,连偶尔安身的窝棚也没了,自己还活着干什么?
死了算了。
赌一把,在黄泉路上跑得快一些,说不定还能追上他们俩。
他手臂晃动了很久,最终无力的垂在一边,杀生落下的声音清脆如同鸟鸣。武林颤抖着抹去眼泪。他最终没有那个胆量把杀生刺进自己的胸膛。真是废物,怪不得一辈子也只能活的像狗一样,没本事活着,连去死都做不到。
他忽然放下王友媛,捂着脸痛哭。
他痛恨自己不能跟他们一起活着,连跟他们一起死都不敢。
时间还在流逝,头顶的那轮月亮就要看不见了。
哭够了,武林又怔怔的躺回菩萨身后,抱着王友媛跟死了一样,他的手中,依然攥着那块碎布。
“菩萨,”武林举起手,看着狮子心在月光下荡漾着水波般的清光。他拍了拍菩萨,问她。菩萨没有回答,那柄红伞静悄悄的在风下轻微颤抖。
“为什么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