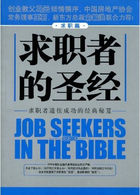到夜深时,皇宫中依然彻夜通明,云鸢背着手站在苍穹殿,面无表情地听着一个接一个的汇报。
云源派的人、皇后,他们勾结的宫中人、朝中权臣,都获罪下狱,听候发落。东宫卫、御林军的首领被抓,但云鸢放过了其他人。
他没有在应天殿处理事务,因为云顺帝安息在那里。
当被问起如何处理云鹤时,大臣们都以为他会将这个叛逆的太子弃之荒野,但他听了只是冷冷地一笑,说:“把他安葬在皇陵,既然这么想当皇帝,那就不要离开皇家,让史书,去评判他吧。”
似乎在一瞬之间,云鸢就变了一个人,没有以前的无赖活泼,他变得沉默,带着冰冷的威严让每一个见到他的臣子唯唯诺诺,不敢抬头直视。
或许云顺帝没有看错,他知道自己的孩子,骨子里是怎样一种气质。
鸡鸣三声,夜已将尽,天边出现第一缕曙光,人差不多已经走完,还剩云鸢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半晨半昏中,像是被所有人遗弃的人。
至少在沈辞临走进来,心里是这样认为的。
一夜未眠,处理各种大小事务,也不见云鸢有什么疲倦。他回过头,看着沈辞临淡淡地点头。
沈辞临突然发现只是一夜的时间,他便看不太懂这个他一直教着的孩子。
或许他从未看懂过?
“有什么消息?”云鸢的语气并不急切,但眼底却有着关心。
“殿下。”沈辞临发现这样的称呼好像有些不妥,于是改口,“新帝,除了芒种,什么都找到了。”
云鸢凝眉,冷冷地盯着沈辞临:“什么意思?”
沈辞临并不答话,只是招手让一个跟着他进来的侍卫下去。不一会儿,那个侍卫又带着一队侍卫走了上来。
他们手中都捧着东西,有人在地上铺了白布,依次将东西放上去。
先是两个人抬上一具白骨,从骨架和身上的衣服辨认得出这是一个女子,接下来,是一块通体透明,中间带着红色血丝的翡翠,然后是从云鹤的尸体上抽离的刀“青灼”。
云鸢双手环在胸前,看到一件件东西被摆放出来,然后想了想,把他手中的乌斐也放了上去。
所有人都低着头看这几件东西,敛声屏气,等待云鸢的旨意。
“所以你想告诉我,你们把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找了回来,但找不回一个人?”
云鸢的语气中隐约有些怒气,眼神也逐渐变冷,让众人一阵胆怯。
那些低着头的侍卫不敢看云鸢,昔日云鸢与他们这些侍卫混在一起,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事没少做。如今他一朝为帝,令人心生敬畏,不敢有一点嬉笑的心思。
“恕臣无能,臣带领下属从皇宫内一直搜到敬城,也只找到了这些。”沈辞临拱手道,“燕家主有要事,便先行离开,未能前来与新帝道别。”
云鸢默默的没有说话,敬城已经接近云朔国下游,而奂城处于云朔国上游,如果从上游一直找到下游都找不到,那么人活着的几率就很小了。毕竟,越向下水势越急,河底还有泥沙滚石,人被冲走就算不被淹死,也会被石头撞上。
“多带一点人,去综城。”云鸢低声说,“不管怎样……找到他!”
他的声音虽然很低,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所有人齐齐跪下,高声答道:“是!”
待沈辞临带领侍卫退下后,他走到白布前蹲下,伸出的指尖在尸骨上方颤了颤。
“小野,谢谢你,为了完成你的心愿,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他把指尖放在尸骨的眼眶处,却再也摸不到那当中会流出的清泪。
《》
清风拂柳,窈窕的影子落入水面,草香在空气中淡淡浮动,一点一点涌入树下的绿荫。
清澈的小溪汩汩流淌,穿过茂密的树林,几只松鼠和鸟儿在水边蹦跳着,溅起两三朵小小的水花。
这个地方很安静,寂寥无人烟,头顶的树叶茂盛,几乎掩盖了阳光。
小溪的源头在一个水塘,水潭上是一道瀑布。突然间,有什么东西被冲进水潭,打破了森林的平静,将安静戏水的小动物吓得四处逃窜。
他醒了过来,呛出一口水,浑身都很痛,尤其是头,像是被活生生撕裂了一般。
他睁眼打量四周,然后慢慢地从水里爬出来,爬到草地上躺着,任阳光炙烤湿漉漉的身体。
脑中一片空白,他努力地回想,却什么都想不起。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受伤?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抬了抬手,忽然有一种错觉,怀中空荡荡的,似乎失去了什么东西。
树林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许多人从树林外走过,他起身,强忍着浑身的疼痛,跌跌撞撞地向林外走去。
每走一步,力气就在流失一分,还没有走几步,他便支撑不住沉重的身体,向前栽倒。
光影斑驳的视野中,女子的身影款款走来,像是一个人,又像是两个人,不知道是个人,但最后所有的影子合在一起,伸手抚上了他的脸庞。
午后,天气有些闷,让人昏昏欲睡,知了在横栏外的草丛中鸣叫,鸟雀躲在窗外高大的树上,只露出尖尖的喙。
软木制的地板被踏响,来人“嗒嗒”地跑着,一边喊道:“副教主,那人醒了!”
女子面向着栏外,让人只看得到一个清丽的背影。
“茗因,你又这样冒冒失失的。”女子清冷的声音响起,在炎炎烈日里,像是一股甘冽的泉水流过人心头,“不都说了让你平时还是叫我师姐。”
叫茗因的少年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着:“副教主,不,师姐,我这不是急着来告诉你嘛。”
“走吧,去看看。”女子点点头,转身离去,茗因连忙跟在她的身后。
他们走进一个不起眼的房间,推开门,一股沉闷苦涩的药味迎面扑来,与外面清新的空气完全不同,房间里昏暗暗的,只燃了一盏光线微弱的油灯。
女子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茗因也不再笑闹,小心翼翼地从外面关上门。
床头靠着一个男人,头发披散着,随意穿着一件外袍,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缠满了纱布。听见有人来,他依然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什么,一动不动。
女子坐在他身旁,犹豫一下,伸手摸着他的头发。
“你是谁?我是谁?”男人用沙哑的声音问。
女子愣了一下,指尖微微一颤,随即眼中涌现少许悲伤:“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她的手撩起男人的头发,露出那张清俊的脸,然后纤长的手指移动到他额头处被包扎好的伤口处。
“我叫毕乙……你是……芒种。”
男人终于抬起头看着她,布满阴霾和茫然的眼睛里,终于渐渐地有了些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