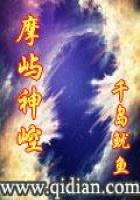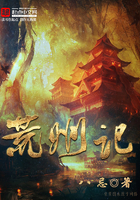原来是一个人上半身扎在一个土洞里,干爹握住双脚使劲一拨,把那人从土里拔出,却是一个早己死透的人,只见他直勾勾地瞪着惊恐的双眼,半个脸皮己经脱落,弄得半张脸血肉模糊,脖颈上一条血淋淋的划痕,嘴角淌着黑黑的血迹显是死了有几个时辰了。
干爹向那土洞内看了一眼,嘴里嘟囔道,“盗墓贼“我听到盗墓贼三个字禁不住心底直冒凉气,因为从小就听过不少关于盗墓人惨死的灵异故事,我展眼四周张望,忽见一旁的草从内还躺着一个,就对干爹说,“那儿还有”。
干爹过去把那人拖出草丛,不想那人死状更惨,脖颈间整个一个大血窟隆,弄得满脸都是血迹,就象是用血在脸上糊过一般。
这是怎么回亊呢,大清早在这儿遇到两个暴死之人。我心里十分晦气,不禁喑自埋怨干爹,不好好走咱的路下下来干啥。“呸,,呸呸。“太不吉利了。
干爹沉思片刻,对我说,“旁边的那一个是噬血候咬断脖颈吸血而死,土洞内这一个是被洞内惊恐的异象吓死的,“。我想土洞内有啥异象?难不成有,,,,,,。
我赶忙左顾右看半天,不见任何东西,到觉这儿挺眼熟,对,那次和张小看电影就是在这儿碰到鬼打墙的。至今想起心里还惊恐不已。荒滩前的那条山路就是前言村通到我们村子的山路。
我怕恶鬼缠身,赶忙崔着干爹走路,他却说,“马二,咱得报案,两条人命哪,大事。“我心里想,要报你报,我管它那闲事干吗,别把自个儿扯进去。
我说,“管它干啥呢,大老远的去公社,还得问这问那。“
干爹似乎对报案更忌惮,正想走,我发现草从里还有一只敞口的破麻袋,正想走过去看看,干爹却说,不想报案,那东西别动。
正好我一眼望到前言村方向慢慢的过来一个人影,象是在山路上拾粪,我悄悄说,“有人喽。“
干爹拉着我飞快的向村路走去。
那次回来以后,没过两天消息传来,说架梁东有个大古墓,死了两个盗墓贼,公安局都出现场调查了,是前言村一个早起的老头报的案,这件事传来,父亲很怀疑的问过我多次,我说那天是在道观里和干爹一块睡的,后来就没在问,我想大概干爹也是这么说的。
这件事过去以后,有一天我在道观里听干爹讲述了古庙里那个女人的故事。
原来棺材里的女子是他的师妹,是1866年同治六年南方闹捻军时他师父天一道长抱养回来的。
刚进入秋,天一道长站在坡顶凉一下脖颈间湿漉漉的黏汉,到是心头清凉了不少,他在前面其兰镇有一位至友李岸,今天准备就在这位至友家歇脚了,看看天色,到也不急,饭前准还能赶上一杯香茶,因为至友好茶道。猝然一阵马蹄急奔的声音,眨眼之间,一马如飞的跑近,只见马上一位中年战将并不下马,满脸血污,己看不清脸面底色。将一包裹物拋向天一道长,恳求道,“俺叫郝通,是张帅部将,今已走到绝路,九死一生,将小女托付道长养大做个闺女吧,拜托,我拦住他们,道长块走“战将说完将马拨回对着身后绝尘追来的二十几个清兵冲去。
道长解开包裹看,是一个不满一周的小女孩,红扑扑的小脸上长着一对灵气的大眼晴,情状甚是喜人。再将目光抬起时,那位战将早被割了首级挂在了马头鞍上。另有两名清兵正在打马上坡,到了坡顶时,再看刚才的道长那有踪影,只得驮着四,五具尸体打马回营。
从此以后天一道长多了一个儿子,取名郝明叶,只为她从小就是着男装,在她十五岁时那年,天一道长让她改着女装,是为了让她嫁人,早点了却了那位将军之托。
她笑着说不急,不急,你急着把我嫁出去,谁给你和师兄做饭,再说,我生长在道家,你不教我点道法,我还不嫁呢。
“傻孩子,学道法,就得入道门,修道的苦痛常人是难以承受的,再说你是女子,入道就得去尼姑庵。这是道门祖师爷的规距,那样岂不违了你父亲所托。“
“我不管,你得先教点,“。
看着撒娇的养女明叶,天一到没了办法。
也罢,就教你一个戏法,我也就这一个道法“
天一让明叶找来两只蚂蚱,从嘴里蘸了点口水抺在两只蚂蚱身上。片刻,两只蚂蚱长大了两,三倍,并且直立如人形,互相拳击角力。两个小东西神态昂然甚是滑稽可爱。
明叶拍手笑说,我要学,就要学。
“那就和你师兄学道家拳吧,在这乱世之中,能健体防身对以后的生存是很有用的。“
我听得有点不对,就问干爹,为什么她童年,少年是男装,还不愿换回女装,那为啥她在棺材里打扮的那明艳呢?
干爹抬起迷茫的眼晴,我看清,今天眼角确实有泪光。
他缓缓的说,那是她后来遇到的一个人使她改变了以前的心性。
明叶二十岁的那一年去山中采药,不到中午就回来了,背上还背着一个人,明叶将那人放在炕上时,干爹看清了他的模样。
“这是杏南沟祁秀才家的儿子吧,你背他回来做啥。这咋地啦“。
“快,师兄先救人吧。”
等把祁公子的伤包扎好,把昏迷着的他安放平妥。干爹才知道。
这位祁公子的父亲祁秀才年节前己经死了。现在只剩他的老母亲和他相依为命,本来家境就不好,在父亲生前还能教私书挣些家用,父亲一亡,将家底变卖换作了出葬费用。可是现在母亲又病重,无钱抓药,好在祖传会些医术,他自己只得进山采药为老母治病。不成想一个从小读书的瘦弱书生,那里爬得了那悬崖陡壁,一个不小心就摔了下来,好在摔在灌木丛里,也道没有性命危险。
三,五天之后,祁公子己能下地行走,师妹将那祁公子送回家去。岂知从这一天之后,师妹完全换了女儿心性,再不是那种傻来疯去的野小子行为了,她每天总要有事无事的找个借口,跑一趟杏南沟,捎带看看祁大妈。一来二去我看出了她的行径,告诉了师父天一道长。
师父问她时,她躲躲闪闪的不肯说。可是都二年了,这是为什么?师父到那祁公子家里却发现,那祁公子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去京城登科考试去了,他的母亲也已病亡,家中只乘两间凄风漏雨的破房而孤零零的座落在那里。这一去两年多杳无音讯,而师妹早在他走以前就怀上了他的骨血。
看看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我只得按师父的意思,给她把祁公子那两间破屋收拾好,从观里将那月供的米背了些将她扶下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