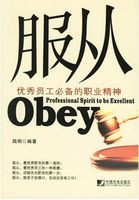王老头用眼翻一翻赵蓝眼,没有答理他,他知道象赵蓝眼这种人不识答理,总归是有缺陷的人,何况智商又不高,如果答理他,他会和你纠缠不清。
王老头问我齐老道在观里不在,这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昨天我刚从张小的三姨家回来,道观还没去。提起道观我想起那位姓候的少年,不知道这件事情,该不该告诉干爹。
就在这时,突然街角拐弯处,转出了两个女人,对着我们大声的喊道:“赵蓝眼,你还在这里磨蹭啥了,你嫂子撞邪了,还不快去看看。”如果在往天,他听到有人喊他赵蓝眼,非跟你急。今天他不再理会,嗖的一下就蹿了出去,古语说:老嫂如母。一点错也没有,今天听到嫂子有事,他急得头上冒了火,因为他童年丧母,是嫂子把他呵护长大。我听说撞邪,也急忙跟着去了。
赵蓝眼急急火火的跑进哥哥家,只见披头散发的嫂子坐在炕上,正在呲牙咧嘴的啃自己的手臂,她的那只手臂早已被她啃得血肉模糊,地上站着的侄女哭着叫着妈妈。赵蓝眼二话不说上去把嫂子的头从手臂上狠劲的搬开,背起就走,将要出门之际,闻讯赶来的六婶叫住他,:“咋了咋了,你还不快把你嫂子放下,快去叫齐老道。”他一时没了主意,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嫂子放下,正想出门一眼撇见了我,“马二,快去叫你干爹。”我一看屋里急成那样,一路小跑着就到了道观,进门时,干爹正在打坐,我急忙喊:“快去快去,赵蓝眼的嫂子跳鬼了。”他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到我一下子就露出了笑容,“昨天回来的,咋的了,大惊小怪的。”我急忙将刚才看到的景象向他简述了一遍,他把破布包一夹,二话没说扭头就出门而去。我喘嘘嘘的连歇也没歇的就跟着回到了赵蓝眼他哥哥家,一进屋,屋子里的人像看到救星一样,急忙给干爹腾出地方来,赵蓝眼看到干爹,哭声哭泣的说:“你可来了。”干爹上前接过她的手臂,右掌一下子按到了她嫂子的后勃颈间,看到一条血淋淋的手臂说,:“没事,这是外伤需要消毒。”此时他嫂子已不再面目狰狞,刚才凄厉的眼睛这会到变得和善一点,透着迷茫的神色,身子仿佛虚脱了一般。赵蓝眼急忙给找了个枕头放在炕上,扶嫂子躺下。
就见干爹向屋内的天棚上望去,左手一挥袖中射出两颗红火珠,直奔屋角的天棚而去,只听见惨厉的尖叫一声,一团灰扑扑的影子从屋角天棚上蹦了出来,一路翻滚着蹿向门口,就听见门口一声猫叫,展眼一看门口不知何时早已蹲着一个栗色大猫,两只猫眼绿幽幽的泛着精光,看到灰色的影子纵身一扑,那团影子似乎恐惧到了极点,一路尖叫着从人们的脚下又返了回来。干爹张手一指,那两个红火珠紧追着那团灰扑扑的影子在地下来回绕转。
来回跑了两圈,那灰影直向北角的一个柜下钻去,这时干爹把众人都撵出外屋。我们从门口看去,只见他双手抱于怀中,那两颗红火珠返回跃入他的袖中,他双手缓缓推出,突然手中射出一道蓝光,蓝光射入柜底。此时,柜下的尖叫声又已响起。过得一刻,柜下慢慢地走出一只大老鼠。门口的大猫一闪就扑了过去,此时,老鼠已是半死不活,大猫一扑就将它叼了起来,闪电般的跑出门去。
这时,干爹对着赵蓝眼说:“快去找医生,把手臂包扎一下。”这时,他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他六婶烧出一锅热水来,满屋子地下泼了一遍,其时,村里的医生也已到了。将赵蓝眼嫂子臂上的伤口包扎了起来。干爹拉着我向门口走去,身后传来赵蓝眼的挽留声,干爹只是哼了一声,并不停留,我两一起回道观中。
在观中我将这几天的遭遇向干爹说了一遍,他埋怨说,早己跟你说过张家的那个孩子是个惹祸精,你不听,偏要和他玩,看这回闯出祸来了吧。好在后来二老粗和他家里人不再追究你俩,公社里又因为你们是孩子,才把此事放下,如果是大人的话,恐怕得去坐牢。我估计你父亲和老张去家里求过人家。
“二老粗他恶人先告状吗?
“人家是有证据的,把猪尿泡都放在公社了。“
怨不得母亲唠叨,父亲却一声也没有骂我呢。
“干爹,今天怎么是只老鼠呢,“。我好奇的问。
干爹此时变得一脸严肃。“他们家祖上就供俸的是灰仙。只因祖上供了灰仙,灰仙长期得把别人家的粮食倒腾到他们家里,那些年他的祖辈到也富足受用了半辈子,岂不知因果循环,报应到了孙子辈,儿子早早死去。赵蓝眼哥俩小时候好一阵子遭罪。“
“那他祖上供的是灰仙,为何现在却要害他。“我不解的问。
“早已从赵蓝眼的父辈就断了,香火一断,恩断义绝。现在还在他家住着,估计那女人八成是惹着它了,否则也不会这样决绝。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早几年就除掉它了。今天它也是为了保全子孙才自已出来的。否则他也不会甘心自己出来化骨消魄。
“那猫是那里来的呢?”我接着提出疑问。
“那是道家的灵符幻化,”
干爹沉思一会又说,“听你今天说起沟里山林少年,我想多半必是那只噬血候无疑,我这几天老在坝上一带找他,因为它酷爱古尸恶魂,那些地方古墓多一些,原来它到藏在眼皮底下,真是没想到它还玩了个灯下黑。
“那为什么又用开水泼地呢?“
干爹意味深长的瞧了我一眼,才说,“这个有讲究,是咱们道家的不传之秘。你想那老鼠乃阴寒之物,附体上身且不说,就是那间屋子被它光顾了,其内阴气大盛,开水乃化汽蒸腾为纯阳,用浇热水法化治寒阴屋子才能住人,否则一年内必会重病一人,三年就会死人,因为那是个灰妖啊。“
说到此时,他沉默一会儿,接着两眼放出精光,开言说道,“那只噬血候得马上找回来,否则它会闯出大祸,到时惹得天怒人怨无法收场。“
“干爹,它又是一只什么动物。“
“它是终南山长期陪伴知不知道长炼丹的一只灵猴,知不知道长羽化之后,由于在长期的练丹中受了些仙气,又懂修道,所以它迀居泰山。因为在泰山多年的修炼中偶得太清君官的仙丹,又经几百年的日月精华之炼,所以有了近千年的仙根,只是妖气未除,迟迟不能过妖仙之关。“
“那它又为何在太行山被你捉住。”
“人修道尚有一百零八难需要闯过,从练气到还虚为八十一难,从还虚到入境又是二十七难,层层难以闯过,更何况它是只猴子了,这其间之劫难真的是难以言述,你现在难以理解,只有等你层层深入了才能自己体会。那猴子难以过了心关,以致失了先天阳血,所以现在为魔了。“
他的话确实说得高深莫测,我觉得再听下去,反而无趣了,也就不在追问。
“它不得不离开泰山,当初洪武帝在泰山祭天之时,册封了一条专看供品的青蛇,青蛇看到它每天都去偷吃供品,两物发生了一场大战,灵蛇当然是胜了,它有正封的册印,灵猴自然败走它乡,到了太行山修练,可是在修练中它为了尽快复功,却坠入了魔道,当然天意要禁固它,这是定数,更是劫难,谁都无法改变。“
干爹的眼里透出一种迷茫,有一种暗然神伤的神情,我心里想,难道修道到了这般天地,心底也有许多的无奈。
我正在暇想之际,门口传来一阵哭声,哭声由远及近并且是重喉音,是个老女人的声音,听着就哭进道观院内,我和干爹惊诧的迎出屋外,只见村南的张大妈站在院中跳着脚的嚎啕大哭。张大妈还是个旧时代过来的小脚女人,这一跳好似老母鸡跳舞,显得那么滑稽。
这时张大妈的丈夫张老敢也苦着脸跟进来,他来到干爹的跟前嘴唇颤动了好久才把事情说清。
张老敢的二儿子叫张三,自小家里人贯养形成恶习,都二十七,八岁了,还不务劳动,张老敢一说让他去生产队上班,他就变脸,“生产队辛辛苦苦上一天,才八分钱,还不如我背个袋子去坝上转两家就两碗攸麦,值多少钱。“你还别说他有时还真得去干过,一次他在坝头一个村里真在实施计划,走到一家张开口袋等你家给舍粮时,忽听那女人叫出了他的名字,“三儿“,他抬眼一看,顿时羞愧的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原来女人是他姑舅姐姐。在姐家吃过饭,姐姐给他灌满粮袋,他才回来。过后姐姐捎回信来,让他姑管着点,太丢人。
别说父母管不了,就是生产队长都管不了,队长有一次和他说,“你是队上的劳力,不上工,年底不给分囗粮。“当天夜里,队长的院墙就被人推倒了。虽然心里明知道是他干的,可是没有证据,他大哥又是解放战争的烈士,调查他不承认也是白搭。
他长年不在家,出门在外不是乞讨就是赌博,偶尔也骗人,曾经公安局也骗人处押回过一次,写完保证书,第二天又就没影了。
今天张老敢说张三死了,死在三十里外的一个破庙里,当地人今天早晨发现以后就给公安打电话,因为张三在三里五乡有点名气所以一眼就认出他了,张老敢用一个小驴车将他拉了回来,现在还停在村口的门板上,因为暴死在村外的人不充许进村,赶着来想让齐老道给择个入土为安的日子,看一看埋尸时下得什么镇物,别弄得儿子暴死,老俩口再不得安宁。
干爹听罢拿着布包就跟张老敢出门。张大妈一看丈夫将她甩下,也急忙停止了哭泣,紧着小脚捣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