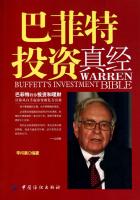踏上几步石阶,丛林掩映处有一扇棕木楼门,片片的青苔覆满了墙角门落。
如言敲门欲进入,我赶紧将她拦住:“你想好了没?”去到里面,一切都将是未知之数。
她向我微微一笑:“想好了,或许很早以前就想好了。”
我牵住她的手,敲了两下门,木门无人自开,恍若隔世的门声沉沉哀嘶,溅起茫茫烟尘,似有什么已在久久恭候。
深吸一口气,正要一脚踏进去,手忽然被握住,耳畔想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臭丫头。”
我愣了愣,及其习惯的甩开了握住我的那只手,道:“死小子,我不是说了很多遍吗?我叫萦云不叫臭丫头。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
离夜微微皱眉,目光扫向四周,林间雾色清冷,草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华,偌大的楼门前孤单的立着我们三,他收回目光:“方才瞧着缺儿一人回来才知你们来了这处。”
我长话短说对离夜道了下事情经过,在如言的执意下我们三入了晚晴楼。
离夜说这个晚晴楼在魔界是个低调的存在,知者甚少。
当我们进了这楼后才知这是座荒废己久的空楼,里处的所有房屋已无什么魔迹,我努力告诉自己楼有相似而已。
只是楼中阁内,无端飘着漫漫酒香,弥而不散,欲饮还休。
大厅中央摆着一张寒床,袅袅的寒气似亿万年都不曾消去,我触手摸了摸,一冲冷意便直窜四肢百骸。
当如言立于榻前时,冰面上忽然浮现出一行字:
命放寒榻,忆从中来。
当初跟着风信子来的时候,晓陌带我移动的太快,不曾看清楚这里。这楼,还有寒床,不会错了,是飘摇于尘世的记忆古楼。
那么如言失去的记忆,已有了执念,牵引她来到这。原来,该来的,时缘一到,始终会来,怎么也逃不掉。
我走到她面前,管不得离夜诧异探究的眼神,将我所知道的说了出来:“确然,躺在寒床上,便可梦入回忆里,也许是自己的回忆,也许有你不知道的别人的回忆。只是你会一直沉浸在回忆里,很难抽离出来,当你的执念选择永远的留在回忆里时,寒床就会夺去你的生魂,那样你会死的。”
如言喃喃着:“心字成灰,命,还道有无?”顿了顿,转身对我和离夜道:“请你们代为转告我夫君一声:两百年了,他待我勿爱勿休,如今我亦成全他……算了,还是什么也不要说了。”
她决然转身,欲上寒床,离夜瞬时上前将她拦住,我也死死的捞着她的胳膊。
勿爱勿休,两百年来离溟不爱如言却又不能休了她。
如言了解,所以如此;我也了解,所以无从劝慰。
心系一个不在乎自己的人,该怎样在乎他?是在远方肆无忌惮的念着他?还是在他身边默默看着他和别的女人欢好?
我看着决心匆匆的如言,道:“即便是如此,可终归你是他的妻,你们今后还有千千万万年可以生活在一起,总有一日,他会把你这个妻子放在心上的。”
如言的眼中看不见一丝伤心的泪光,是呀,两百年了,任是再沉重的泪水也早已干尽。
她轻抚我的右臂,清兰一般的脸上竟似有种赖皮儿的味道,眼边唇角的笑意格外的恬淡无谓,这样子的如言是我未曾见过的。
如果离溟能够看到此刻的如言,看到这样的笑颜,会不会就对她心动了呢?会不会就爱上她了呢?
那****说“你也别再把我当成谁了”,他分明是看了她一眼的,若眼里不是她,他为何有时又体贴的待她呢?
如言望向空无的长门口,轻轻道:“萦云,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喜欢画心阁,自从成亲后,离溟便再也不回寝宫了,画心阁是他常去的地方,听说阁的名字也是他取的。所以这几天,我能够暂往在画心阁里,已经很满足了。阁中的桌椅,花草,一瓶一器,都有他的气息。小萱炉里燃着的是白檀的香线,我猜他喜淡不喜浓。还有,昨晚,我悄悄的翻了一下他的衣柜,原来他喜欢玄紫的衣色,而且他不喜欢白色,柜子里面没有一件白色的衣服。两百年了,这是第一次我觉得离他很近很近,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及到他。”
我接道:“正因如此,万万不可放弃自己的生命。那记忆失去了便失去了,既是你父魔告诉你那是因为天劫失的,要询个究竟,你可以去问他不必以生命相弃。”
她缓退一步:“父魔一百年前就已逝离人世了。记得父魔还在世时,他告诉我,我历天劫失去了少许的记忆,没过多少日子父魔把我许给了七殿下,离溟,即使我从未见过他。那时我没有想别的,只觉着心好像浴在火里,朦朦胧胧地失了方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嫁给他……”
我截住她的话:“对你来说失掉的记忆固然重要,可是,远不如他,你知道他不能休了你,所以你想找个理由离开他,成全他。以这样的方式离开,阴后和木渎世家知道了也不会怪罪于他,所有的一切你都为他想好了!”
想想也是,她的身份不仅仅是上弦朝七殿下的正宫娘娘,这凤冠上还承着木渎世家的荣耀和地位,却长年不受夫君的待见,木渎那边迟早得弃车。她是个知进退的女子,早些了断,让本家送上值当的顶上,以此保全木渎,也顾全了离溟和上弦朝的脸面。
这等的女子,即便想为爱要死要活,也会顾全大局,为身后的整个家族生死一掷。
我不知自己是在劝慰如言,还是在一步一句的剥析她那颗千创百孔的心。
我收拾了下心情,正欲再劝却被离夜拦下了,他松开了抓住如言的手:“七弟给不了的归宿或许那张寒床能给。”
如言对我俩宛尔一笑:“你们说,怎样的女子才入得了他的眼呢?”
她从容的躺上寒床,平静的闭上双眼,流瀑一样漆黑的发默默凝住,刺骨的冰冷不消一刻便能将她的身体侵蚀。
的确,这是她最想要的归宿。
离夜一直握着我的手没有放开,良久,他伸手往我前面一指,在距寒床一尺高的半空中,出现一团晶莹的粉光,粉色光影中一朵朵鲜艳的樱花瓣缓缓展开,离夜拦腰带我飞入这片光影之中。
我静静瞧着漫天飘飞的樱花瓣子,身旁离夜熟悉雅朗的声音悠悠响起:“这么些年,她多少是觉到了些,他夫君眼里见不得她。不是说可以梦入执意想知道的回忆里吗,甚至是别人的回忆,她是想知道,可以放在他眼里的姑娘是怎样的。”
他偏头对我道:“你既放心不下如言,那我们便去瞧瞧那段失去的记忆。”
下一刻,脚落地立定之处,已在如言失落的记忆虚境中。
乍时一片偌大樱林闯入眼帘,在我们周遭铺尘开来,粉白尽处,瓣舞纷飞,遍地香查。
离夜说这里是魔域的木渎镇,一年四季樱若飘雪的木渎镇,如言的家乡。
一片随风吹散的粉瓣落在离夜的肩上,有如一只倦了的肩上蝶,真实可触,即使再清楚不过这里只是如言两百年前失去的记忆,一个虚幻的曾经。而我们只能隐在其中,可感可及,却是不扰丝毫。
不远处一个伊人翩然起舞,芳姿窈窕,步伐婉转,衣袂绽开,流风回雪,云端漫步。
不觉看得出神,牵着的手却突然被猛捏了一下,我一把甩开:“喂,疼!”
离夜冷道:“至于吗?瞧个男的把魂都丢了。”他表情阴霾地看了我一眼,调开了头。
“啊,她是男的?”我惊到不行。不过再细量,伊人冰清肌肤上所着的确实是一身米色男装。
离夜转头瞧我,神情微征,半晌,淡淡道:“他叫桑昕,估着辈分,算是如言的师兄。”
桑听,听着水榭中的侍女八卦过,他乃是,上弦朝内四族的木渎家御执事,传闻亦道,木渎第一美男子。
有关他的事迹轶闻很少,因着他时常隐居在深林,采药闲作,较少露面。
天下竟有如此像女子的美男子,我侧身准备对离夜小讽一下:“怪不得今次瞧到这等的‘美女’,某位世子的魂还在。”
却在我转头的那一刹,无意瞥见了几步开外正停下脚步的另一个魔,离溟。
两百年前的他,彼时是个少年,玄紫衣袂,俊涩翩翩。
他身旁的樱树开得很盛,一片一片的粉瓣子吹落到他身上。
起初不经意的他,此刻眼里,寂寥无它,惟有不远处漫舞的纤柔‘女子’。不刻,凉薄的唇角轻轻勾起,温柔的笑意无声漾开。
这样的一抹笑,随风而沐,全无心思,或许连离溟自个都不曾意识到此刻他笑了.
直至后来当我看完了这整段记忆,才发觉原来这段故事笼统不过有两次错过,在初次的错过中开始,在第二次错过后结束。
最后错过的剩下时光,他执意固守,另一方则在拾忆后殒去。
良久的驻足之后,离溟悄无声息的离开了这里,连一点上前去和‘伊人’搭个讪的念头都没有,大抵是因为跳舞的那厮是个男的。
这是第一次错过,他的有意错过。
随着他的离开我们身处的这片灼灼樱花林也层层化开,一路流光飞舞。没一会子,景致换然。
雨若丝,纷纷扰扰,闪电破空,风卷雷鸣。
林间,潮湿扬起的尘土味混着一股淡淡的血腥。
离溟受伤了,右肩伤口溢出的紫血混着雨水漫延。他勉力拖着一柄银寒长剑,一步一顿地走着,落地的剑尖在泥泞路上划过一道长长的痕迹。
我单手拂了拂身侧离夜的肩,以示不要担心。
但是很快我就后悔这多余的举动了,离夜纤长的指沾了沾溅在草叶上的紫血,放在鼻间嗅了下,随后回我一笑:“那是我伤的。”
“你伤的?”兄第不和,骨肉相残?
“嗯,我记着当时他非要和我比划,硬是不躲受了那一剑,之后就一溜烟没影了。”离夜随意变了把油纸伞,撑开在我俩上空,处在与离溟不远不近的地。
我见自己的裙摆被雨水打湿了一块,随意里往伞中央挪了下。
“喂!”离夜突的扯了一声。
“怎么了?”我莫名。
“这几年你还蹭了多少个?”他语调厉然,将伞往自个那边挪了挪。
蹭了,多少个?这什么跟什么呀?
等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握住伞柄使力往这边移。
他却一把抢走伞,迎面扑来的雨湿了我一脸。
“小时候你就往我身上蹭,你……”
“没有!”我慌不择言的喊了一声,截住他的冷语。“一个也没有。”除了这两年和晟非有些许的小意外,就再也没和谁亲近过。
离夜说的“小时候你就往我身上蹭”,是指初遇的时候吧,那不是蹭,是扑,是小孩打架的手段。
“你、哭了?是……”他走近我,满目柔光熠熠,将伞撑在我的上空。
我抹了把脸,“哦,是雨水。”
离夜回我一个大白眼:“骗我一下你是会死吗?”
“好吧,我哭了。”或许我是真的哭了,却是雨水的关系离夜瞧不出来。
有种伤心是要隐藏起来的,因着不知它从何而来,不明所以的就有了。
我侧开脸,再将目光转向不远处的离溟。
“你受伤了?”一声泠泠的男音响起,是从林子另一边疾步而来的桑昕,背上负着一筐药篓。
当离溟回首抬眸时,桑昕已经站在他身畔,立时,一阵狂风卷起两人的衣袂飘扬,没待离溟晕厥,桑昕就扶住欲倒下的他。
渐渐袭来的暮色隐去了淡青的烟雨,桑昕让半睡半醒的离溟靠在他的肩头,一路上参扶着他,将他带去了自己的林陌别苑。
一场雨,一肩伤,一次搭救,一段相识。
月上帘钩,离溟身负剑伤,很老实的在床上晕了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