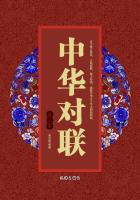二姨是几个姐妹中长得最漂亮、也最辛苦劳作、最心灵手巧又识字最少的一个。为了供大舅念书,她起早贪黑编席子,手指不知勒出多少道血印子,姥爷硬要她嫁给曾是地主的富户,瓦房四间,又有体面的彩礼。二姨不乐意只是哭,成串的泪珠浸透了手中正纳着的鞋底儿。这次,姥姥照旧没说什么,只是边干活边撩起罩衣大襟擦眼泪,家中死静死静的,没人说也没人笑。姥爷叹了口气,一声“穷命”,二姨嫁了她看好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常年在建筑队打工的二姨夫。
有了哥哥、姐姐抗婚成功的先例,三姨、小姨、小舅自然顺顺当当结婚生子了。
我和哥哥、小妹都是姥姥一手带大的。腊月二十三“小年”是姥姥的生日,可一进腊月门,是她最忙最不得闲的时候,浆洗缝补扫灰糊墙上上下下忙个不停,还得点灯熬油给我们做新鞋,唤小姨、小舅挂灯笼贴对子,淘米做粘饽饽,冻上干、白豆腐非她亲自操持不可。全家最盼望的事就是杀年猪,姥姥一边张罗着把杀猪的张师傅请来,再烧上一锅滚开的水,找人抓猪,再手忙脚乱地上案,一阵猪嚎人叫,猎杀好了,先给张师傅砍上两斤好肉作为酬劳,接下来再大卸八块亲戚朋友分了。没分上的邻居,姥姥不忘叫小姨端过一碗炖肉。
现在的女人就一个孩子还整天喊累,我真不知道,姥姥带这么多的孩子,日子该有多劳顿。一天,小舅逗小妹:“快收拾东西,你爸妈在火车上等你,一起上你爷家过年。”小妹禁不住“哇”地大哭起来。姥爷刚吃了一半儿饭,气得“啪”地把筷子一摔:“大过年的,找不痛快啊?”小舅连忙陪笑:“我在逗她玩儿呢!”我接过话茬:“姥姥,为啥我们总在你家?”姥姥笑了:“傻孩子,你爸从小没妈,他跟你妈管我都叫妈,你说你们家不在姥姥家过年那上哪儿过呀?”
在姥姥家过过多少次年,我数不过来,可在我的记忆中,姥姥从来没过过生日,不知道她是忙忘了还是压根儿就没想起来,当我们笑嘻嘻地捂着小脸大叫灶王糖粘牙时,她总是笑。我从来没听过姥姥抱怨过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直直腰”,顺势在煮小豆锅的热炕头上躺躺,烙几下,没几分钟,一咬牙又下地了。
日子不禁过,一晃儿,大舅、二姨、三姨也有了孩子。邻里大妈常笑着逗姥姥偏心,只给大女儿(我妈,排行在大聋舅后,大舅前)看孩子。说来也是我们哥仨不争气,至今我妈都觉得欠姥姥的。当时家里只爸一个人挣钱,每月还得给爷爷和后奶寄钱寄物,日子过得太紧,没办法,生下哥哥不久,她就出去做临时工,把哥哥送到爸爸上班的县医院托儿所,可哥哥偏偏瞪眼不吃不喝干嚎了三天,嗓子也哑了,眼睛也肿了,姥姥来了,二话没说,把哥哥带走了。我自幼体弱,伤风感冒不断,老是打针吃药,家里那张浅黄色的八仙桌的第二个抽屉装了针药,日久条件反射,谁一拉开我就大哭。姥姥来了,不高兴了:“小孩能有多大的病?头疼脑热的,吃一碗热面条,炕头热被窝一捂,睡一觉就好了,还吃啥药?”两岁的我也去了姥姥家。
妈妈后来又到县铸造厂去做临时工,平日不敢总请假,怕人家不给转正。几十斤重的暖气片坯子一扛就走,一天下来,人累成了一摊泥,可是星期天还得起大早坐火车走旱路到姥姥家看我们。每次姥姥总对妈妈说:“你就放心忙你的吧,有我呢。”孩子大了,也恋妈,每次姥姥总是哄哥哥啃骨头,对我则是让小姨领着到处看扭秧歌,妈妈偷偷地走。
到有了小妹的时候,妈发狠了,决心不再拖累姥姥,雇老伏太太看她,每天水果、好吃的拿着,可小妹就是不吃,回家饿得找咸菜喝凉水。有一次自己竟偷偷跑出来,顺着洗澡堂门前那条石头小路,哭喊着找妈,小黄头发在冷风中吹得一撩一撩的。姥姥偷偷让三姨来,把小妹接走了。一个秋天地煮青苞米,小妹长胖了。
多少次,姥姥边给我编小辫儿边跟我说话:“你妈苦是苦了点儿,累是累了点儿,可自己挣钱花,不用看男的脸色活。”姥姥让我长大了好好念书,“上学认字,东西学到肚子里了,谁也抢不走,自己上哪儿去心里也不憋屈。”每次外人说姥姥偏心向着妈妈,姥姥总是啥也不说。
姥姥一天最闲的时候是梳头,早饭后洗罢脸,就着洗脸的温水,先是用那只木梳子从头发中间分个缝儿,再沾上水,左抿一下右抿一下(至今一闭眼,这个动作都难以忘怀),两手一起一拢,在脑后挽个髻,再拉上网套。这是姥姥最美的时候。从没见她擦过雪花膏,可她总是那么俊。
最不敢看的是姥姥洗脚。一天累下来,姥姥最大的享受就是用那个被孩子玩闹摔得皱皱巴巴的小铝盆,盛上热水,“啊”地往里一烫。姥姥的两只脚都是二脚趾摞到三脚趾上面,像是硬掰过去的,磨合处的茧子厚厚一层,我每次见了,总是问:“姥姥疼吗?”姥姥说傻孩子,小时候疼,长大就不疼了。我问那我的脚趾怎么跟你的不一样呢?姥姥说:“我小时候,我妈说女孩子大脚没人娶,我的脚这样才能小啊。等你长大了,还这么听话,肯定能嫁个好人家。”我说我不嫁,永远跟着姥姥。姥姥感动了,用右边脸贴着我的小脸儿,边摇晃着身子,像是自言自语:“女孩子,比男孩活得苦呀!得长本事才行,别像姥姥一个大字不识。将来有文化了,跟你妈现在似的,坐办公室,就不会像姥姥这样靠体力吃饭了。”
许是自己没文化,姥姥硬是起早贪黑让大舅读了中专,三姨、小姨、小舅念完了九年。只有二姨只念两年书,当时家里实在没条件,姥姥总觉得对不起她,也格外挂念着她。
哥哥、我、小妹相继到了上学的年龄,要离开姥姥了,哥一路哭喊,回家不到一星期,哥哥想姥姥,病倒了,姥姥也不像从前整天有说有笑了。姥爷试探着问姥姥,要把哥哥再接过来在村上念书,姥姥说啥也没依。我和小妹离开姥姥家也是一番撕心裂肺地哭,可姥姥就是没心软,坚持让我们回县城念小学。
在照看过我们哥儿仨后,姥姥管的最后一个小孩子就是小孙子。小舅和舅妈结婚生下大崇后,舅妈就一直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要想转正就得考上县的教师进修学校念两年才有资格。姥姥给舅妈打气:“考考试试,别人行咱也能行。”天天三顿饭姥姥做,就连碗也不让舅妈洗,怕她分心。舅妈到县城上学,姥姥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和小孙子滚在一起。小孙子慢慢长大了,姥姥的背也越来越弯了。
姥姥明理、刚强,再加上处事公道,在亲友邻里中间留下了好威望。但在家,她总是听姥爷的,从不跟姥爷计较。可有一次,来人借麻袋,在大门外,姥爷说家里没有了,来人说“我进屋问问大姑(指姥姥)”,姥姥说还有两条,顺手就给拿了。姥爷不容分说,顺手给姥姥一个大嘴巴,还直唠叨:“不听话,还反了天了!”这一巴掌,打在姥姥脸上,更打在姥姥心上。头一次见姥姥掉眼泪,我吓得大哭。眼看快过年了,姥姥不说不笑,但给姥爷做饭却一顿也没耽误。一天姥姥独自闷在东屋里大半天没出来,隔着门缝,见姥姥在收拾那个蓝皮小包袱,“姥姥要走”,我大哭大叫。大舅连忙把东屋门弄开,姥姥边系鞋带边说:“女人没本事,一辈子遭人欺负。”姥爷搬过一条板凳横在门口,右手颤抖着夹着烟,火柴还没点着,眼泪先下来了:“你往哪儿走?”(跟姥爷这么多年,再苦再难姥姥从没说过要走)“离开谁都能活!”“你也没钱呀?”姥姥听罢更伤心了(平时姥姥花一分钱也得跟姥爷要),铁了心要走,孩子们谁劝也不行,最后姥爷赔礼道歉答应再也不那样对待姥姥了,姥姥的脸才肯放晴。
奔波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姥姥倒下了,严重的风湿、骨刺痛整日整夜地折磨着她。先是腿脚不好使,再后来下地都困难了。妈把姥姥接到县城住在我家,姥姥总觉得住在闺女家心里不安,每次上厕所,都急着拄棍儿往外走,生怕弄脏了屋子,给爸妈添麻烦。
姥姥的病加重了,脑压过高,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亲友们急得有病乱投医。姥姥年轻时曾经打死过一条蛇,众人回想起来了,说是得罪了蛇仙,要请跳大神的。姥姥从来不信这个,连连摇头说不要不要。哥哥回来看姥姥了,当时姥姥说话已有些不大清楚,可她特别高兴,和哥说了很长很长时间。
姥姥不让妈告诉我和小妹,怕误了功课。姥姥一生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可临死,她却没让我兑现一次我许给她的诺言,就连一包最普通的点心盒果子,最舍不得吃的香蕉,她也没来得及尝上一口……
姥姥最惦念二姨,当初她随夫去吉林谋生,几个子女数她离家最远,连封信也不会写,虽然姥姥不识字,可她总问有信来没有,最终快咽气了,也没见到二姨,姥姥连眼都没闭上……
姥姥是在她最喜欢的季节——秋天走的,就连选择离开,也想着要儿孙们在黄灿灿的收获中健康快乐地活着。
姥姥生前常说她是树根,妈是树干,我们是树叶,只要有树根在,就不怕树叶找不着家。如今我们这些树叶都有家了,姥姥,你总该放心了吧。
生命的根
杨妤
在北方,冬天的草木是没有语言的,沉默是它们的一切。临近世纪末的一个冬季,纷扬的大雪不期而至,早早地覆盖、积压,草木始终不出声息。这一大段的生命仿佛空白掉了,删节掉了,追忆的只有草木将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那泛绿、开花、结果的一阕章节。
雪后初霁的天是最冷的,慌乱翻找御寒的冬衣,却发现一条崭新而厚重的红毛裤,霎时幡然醒悟,无语哽咽,泪雨滂沱。时间回到了去年的那个冬日。
母亲在窗前阳光的荫翳下,穿着父亲特意为她买的紫红色棉袄,倚在床边静静地用布满沟痕的双手为我和弟弟织着下一年的毛衣毛裤。那时,她已身染沉疴,糖尿病合并肾病,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眼角满是眼屎,只是微微地翕张,肚里的腹水涨得肚子像个皮球。母亲凭感觉、凭记忆编织着浓浓爱心、殷殷希望,是希望的曙光照亮了一切,而她自身的悲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然而,那一个充满阳光的冬天却没有再来,母亲也没再迎来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如冬天的草木无言地逝去了,没留下一丝云彩。天地间,孤零零地立着二十六岁的我和二十岁的弟弟,心冷如冰,心僵如铁。亲历了病魔一点点地侵蚀,母亲一点点地忍痛煎熬;亲见了透析室如钉子般粗的针头从母亲的血管上出出进进,母亲的肌肤、躯壳一天天地松懈、衰竭;亲听了将逝者的默默的抽泣和无言的悲哀,我们只能深刻地咀嚼悲伤,透彻地感悟黑夜。如果母亲逝在我的童年,那时不太懂人世间的挚爱与真情,会将她渐渐地淡却。如果母亲逝在七老八十,让我已尽责尽孝,尽展儿女的成就与辉煌,那么临行前母亲会微笑着随烟云飘走。而母亲偏偏中途撒手西归,割舍不下又惦念不已即将成家立业的儿女,那是怎样的伤悲,怎样的从容?于我们则是刻骨铭心地疼,剜骨割髓地痛。
顾诚说:“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而黑色给予我的却是无边的伤痛,无言的泪水,勾起了我对生命的枉叹与无奈,体味着生命的苍白,命若游丝,奄忽浮尘,面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莫里老人告诉了我一个故事:在南美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名叫迪萨那的部落,他们认为世界是个恒定的能量体,它在万物中流动。因此,一个生命的诞生就招致了另一个生命的终结。同样,每一个死亡带来了另一个生命,世界的能量就这样保持着平衡。当他们外出狩猎时,迪萨那人知道他们杀死的动物会在灵魂井里留下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将由死去的迪萨那猎手的灵魂去填补。如果没有人死去,就不会有鸟和鱼的诞生。
冬天的草木“冬眠”过后必将迎来新的一春,重吐枝芽,母亲的逝去也会带来另一个生命的春天吗?那个生灵又在何处?但无论如何,我才是母亲的根啊,母亲赋予我生命,是让我吐露芬芳,花开花茂,洗却沧桑,揩干眼泪,在充满泥泞的人生之路上拾级而上,紧紧抓住生命的根,捍卫生命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