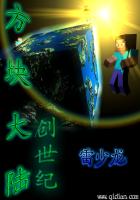我和胡子都很纳闷的看着平底锅,我心说他接个羊血而已,又怎么不对劲?
胡子顺着他的话还反问,“咋了哥们?在血里发现金粒子了?”
平底锅知道胡子是在调侃他,他也没太在意,反倒依旧拿出严肃的样子,把椰子壳捧起来,给我俩递过来。
平底锅让我俩问一问羊血的味道。
其实让我吃羊肉还行,但生羊血嘛?我总觉得膻呼呼的,打心里我也真不想闻。
我本来摇头示意,不过平底锅拿出坚持的样子。
当我看着椰子壳都递到我和胡子面前时,我知道躲不过去了。
胡子还示意,让我先来。我耍了个小算盘,估计屏住呼吸,凑到椰子壳前,特意“闻了闻”。
我没闻到什么,但随后我又把头缩回去,跟平底锅说,没什么异常嘛。
平底锅很诧异。胡子则像我那样,也凑了过去。只是这哥们很实在,狠狠的吸了一大口。
胡子突然嗝了一声,还翻着白眼,这就仰面就倒。
我看在眼里,也立刻施加援手。
胡子被我拖着,并没真的摔到地上。而且借着这么一会的缓冲,胡子回过劲儿来。
他又咳嗽上了,还跟我说,“他娘的,你是不是鼻子锈住了,我怎么闻的时候,觉得那么苦呢?”
我嘿嘿笑了笑。胡子彻底反应过来了,说我竟敢耍滑。
我跟他斗了几句嘴。但接下来,我也把精力也放在羊血上,这次我为了验证胡子的说法,稍微对着羊血闻了闻。
不得不承认,不是一般的苦。
我和胡子都犯迷糊,胡子念叨说,“奇怪了,这只羊怎么搞得,难道是胆有问题,胆汁啥的,都渗透到血里来了?”
我觉得胡子这说法不太靠谱。而我能想到的是,这只羊平时被喂了药,往深了说,或许不仅是它,整个养殖场里的牲口,都被喂过药。
我把这分析说出来,平底锅依旧拿出懵逼的样子,胡子却觉得我说的有点意思,他接话说,“难道丑娘那些娘们很讲究,把这里的某些猪、羊都弄成‘药膳’了?”
我们没法再往下求证。平底锅趁空又问,“这只羔羊还要不要吃了?”
要在平时,我肯定不会再打这只小羊的主意,但在这小岛上,随意丢弃肉类食品,这让我觉得简直跟暴殄天物没什么区别。
我最后有了计较,让平底锅去捉个鸭子回来,我们把羊血喂给鸭子喝,要是鸭子喝完了没啥事。我们也别太较真了,把这只羔羊烤着吃了吧。
平底锅绝对是被羊血的问题闹得,他脑筋现在都有些转不过来。他又问我,“鸭子能喝血么?那玩意平时也不吃荤啊?”
我提醒他,“鸭子最爱吃的就是鱼!你说它吃不吃荤?”
平底锅拿出顿悟的架势,立刻屁颠屁颠跑着离开了。
他很快拎回来两只鸭子。这俩鸭子或许是被惊吓到了,哇、哇的一直叫唤着。
我对鸭子这状态比较满意,毕竟它们越活分,就说明它们越健康。
我又找了两个一等奴,让他俩配合平底锅,强行给鸭子灌血。反正折腾一番,这俩鸭子都被喂饱了,尤其嘴巴全红呼呼一片。
我们把鸭子放在草屋内,一边观察着,一边这就点火,把刚死的羔羊扒了皮,架在火堆上了。
一直等了半个钟头,这俩鸭子还没啥事,外加那个羔羊都烤的差不多熟了。
我们这些人问着烤肉味,早就馋了。我们不再等了,一起开吃。
这一次是我们所有人,包括大毛,都聚在一起。我们围着烤羊,坐了好大一圈。
平底锅这些一等奴,冷不丁跟两个随从聚餐,有些不习惯。想想也是,平时他们吃饭时,都是被等级制度限制着。
我索性有话当面说了,让他们放开身份,也别想那些用不着的,我们现在就是一群好哥们,聚在一起搓一顿。
胡子为了调节尴尬的气氛,还主动胡扯起来。
他先讲了一些小故事,但气氛还没被他调动起来,有些死性。胡子看着默默吃饭的这些人,哼了一声,说真是要逼老子使出杀手锏。
他又一转话题,聊起女人。我打心里不得不感叹,心说不管什么样的男人聚在一块,似乎一谈到女人,大家就全真都有共同话题了。
很快的,两个随从和平底锅他们都彻底放开了,偶尔胡子讲完一个荤段子,这些人还嘻嘻哈哈的坏笑起来,包括那大毛,他不会像正常人那般笑,却会哇哇的叫几声,表示兴奋。
一晃又过了一个多钟头,这只烤羊几乎被我们吃完了。我、胡子和平底锅这些人,都只是腆着肚子,随意的坐在地上,而那俩随从和大毛稍有异常。
他们一脸通红,时不时傻笑着。就说那俩随从,他们还非要跟我们说一说狐姐的秘密。
按他们的意思,狐姐一直是梨王的女人,但梨王太胖了,走路都快成问题了,更别说做那事了。所以狐姐偶尔被梨王摸几下之外,他俩根本不发生关系。
另外狐姐正是好年纪,她总不能一直被梨王挑起欲望,却无处发泄吧?最后狐姐就偷偷跟黑鸡好上了。黑鸡那是啥人?听外号就知道,他那方面很威武雄壮的。就凭他这优势,也绝对能把狐姐弄得舒舒服服。
我听这俩随从说这些的时候,也偷偷观察平底锅这些人。他们都挺诧异,也绝对被这种爆炸性新闻震慑住了。
我一直觉得这俩随从是挺有尺度的,但为何这次这么失态,非要当着这些一等奴的面,说狐姐这些原本不能公开的秘密呢?
胡子跟我有类似想法,他还盯着这俩随从,喂了一声,多问说,“两位,喝大了吧?”
这俩随从摆摆手,说哪有?但我被胡子这话一提醒,再这么一观察,反正也觉得,这俩随从跟醉酒了一样。
而且没多久,这俩随从互相肩靠肩的依偎在一起,呼呼睡了起来。而大毛呢,耷拉个脑袋,也拿出昏睡的架势。
平底锅先有疑问,说我们刚刚吃的是烤羊,并没喝酒啊?
我凑到两个随从和大毛身旁,试探下他们的鼻息。他们呼吸有力,不像是中毒。而且我冷不丁又想到白天打斗时的经历了。
黑鸡也好,大毛和这些随从也罢,他们都在大中午时,像得了流感一样,时不时往下流鼻涕。
只是后来他们的症状都轻了,我就把这事忽略了,现在一看,我觉得这些随从和大毛的身体有古怪。
我一时间没法把这事想的太明白,外加这俩随从和大毛没啥性命之忧,我就招呼这些一等奴,先把这三人抬到草屋里,让他们睡醒了再说吧。
随后我们又收拾一番,至少把吃剩下的羊骨头,外加扒下来的羊皮和下水啥的,都弄到一块去。
平底锅还主动要把这些“垃圾”扔了去。我把他拦住了。
我想的比较深,明天狐姐她们肯定回来养殖场,到时她们真要发现这一大堆垃圾,我和胡子作为随从头领,不好解释这事。
我就让平底锅把垃圾给我,我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把垃圾处理了。
现在大半夜的,外加胡子吃撑了,他说陪陪我,也借机溜达溜达。我说行。
我俩把羊骨头和下水都裹在羊皮里,我拎着一把简易的铁锹,胡子拎着羊皮,我们随意的走起来。
我本意是找个什么小沟,挖个洞,把羊皮丢进去。而胡子说他想到个更好的地方,还张罗着带我去。
我一时间挺纳闷,等跟他走了一会,我发现,他带我来到猪圈附近了。
这里有一个恶臭凹地,借着月色一看,这里全是屎,有人的,也有猪的和羊的。
胡子说,“怎么样?咱们把垃圾埋到这,是不是更保险一些。”
我点点头,问题是,这里太脏了。但胡子不在乎,他拎着铁锹,当先小心翼翼,踩着相对干净的地方,一步步走到里面。
他还立刻戳起土来。
我俩就带了一把铁锹。我一时间帮不上忙,外加我也不想往里走,就蹲在外围,默默等起来。
没多久胡子咦了一声,还加大了戳土的力道。我隔远看的纳闷,心说他咋跟挖坑较上劲了。
我喊了他几声。胡子最后因为力道大,还差点把这简易的铁锹弄断了。
他招呼过去看看。我不得已,压着嫌脏的心情,也走了进去。
胡子挖的坑并没多深,尤其坑底的地方还直反光。
我看到这场景后,眉头一皱。胡子蹲下身,摸了摸反光的地方,跟我说,“娘的,这里有铁板,还不小呢。”
我在这岛上,能见到的铁器很少,毕竟物质匮乏,这块铁板能被埋在这里,想必是丑娘那些人做的。但这么一来,我也想不明白了,为何这么好的东西,用来做什么不好?非被埋在这儿呢。
我接过胡子手里的铁锹,又挖了一番。
我主要是把铁板上的土全都清空。我估计少说费了一刻钟的时间,整个铁板暴漏在我们面前了。
这铁板长宽都有一米吧。它并不算太大。我和胡子还各自搬着一个角,使劲抬了抬。
而在这铁板被抬起的一刹那,我能感觉到,它底下呼呼往外冒风。合着这铁板只是个“门”,这底下竟然还有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