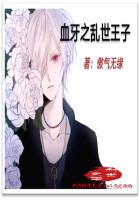醒来时已是早上,却不知是第几日。沈夕睁眼坐起,仍是那片圆地,自己正靠在那颗断桩上。男子已经不在,蟒蛇也不见踪影,仿佛一切都是梦中所遇。摆动臂膀,仍有些酸麻,暗想来事,微微记得轮廓,却也忆不出其中详细之形。
日光从叶隙中渗下来,有几道洒在他脸上脖间,沈夕顿发懒意,盘臂倚后,心想:“那人说这里叫失落林,没了蟒蛇,倒比大长老的乡园还安逸。”
想起大长老,猛然坐起,低叫道:“坏了,我离开几日了,小园子他们会不会在找我?”起身就要离开,不妨脚下一绊,带动地上树藤,树藤牵动林外花从,沈夕立时被猛拉过去,在地上拖曳疾滑。
拖动他的是条巨蟒,沈夕弯起身子要解脚踝树藤,可那蟒蛇甚是机警,不等他动,一尾巴径直拍来。沈夕心想:“原先我中了毒,尚且敌不过,现在轮到你尝尝苦头了。”抓住它尾尖翻身上攀。
蟒蛇左右乱晃,沈夕死死抱住蛇尾,将树藤缠上,只听哧啦一声响,树藤被蛇力扯断,沈夕也随之坠落下去。快落地之时,右掌劲推,借力弹上,跳到蟒蛇头顶。蟒蛇摆动更甚,头部猛受一拳,痛的它上下翻腾,却始终无法将沈夕甩落。打了几拳,蟒蛇渐渐消停下来,似乎气力已尽,沈夕笑道:“早这样不就好啦。”轻拍了下它脑袋。
驯服了巨蟒,骑着它行了许里,竟而出了失落林。眼见水潭临近,木桥依旧,对面草丛一浮一荡,沈夕不禁大声欢呼。刚跳跃下来,一望水潭边,不由得又一声怪叫,水潭边站着一人,正是那苗族男子。
男子微笑道:“你睡了三日,我还以为你再醒不来了呢。”说着走上木桥。沈夕点点头,暗道:“我竟睡了三日,那毒好厉害!”一望男子行动,不禁惊诧万分,只见他走到谭对岸,对草丛一招手,立刻涌跳出无数九夔。沈夕刚要叫他小心,可接下来的事更让他感到骇然。
男子从容步入九夔群中,银袖拂过,抓来五条九夔。他徒手抓这些毒物也就罢了,却见他刨开九夔肚腹,掏出胆囊,仔细在水潭洗过,往前抛起。水潭一下跃出四条巨蟒,分衔胆囊,重跃回谭中。沈夕身边的巨蟒一吐长信,倏然窜跃过去,衔下最后一个胆囊,对男子探了探身。
男子对沈夕道:“你吃不吃?”
沈夕干呕难当,连连摇手作拒。男子道:“这里的蟒虽然体大,吃食却挑剔得很,九夔之毒美味无比,是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偏偏只吃胆囊,不吃皮肉,如果我不在,它们定会饥饿而死的。”
沈夕道:“你到底是人还是怪物?”男子道:“你看我像人还是像怪,你觉得是什么,那就是什么了。”
眼前之人既很怪异又很神秘,却又有种说不出的气魄,他分尸了五只九夔,竟无一只敢向他示威攻击,全瑟瑟缩在草丛之中。男子伸手一挥,众九夔才鸟雀般散去。
男子道:“它们吃过了,我们也找些东西吃。”沈夕忙道:“吃…吃什么?”男子笑道:“你认为我们该吃什么?”探手入谭,哗啦一阵响动,从水中抓起一根合抱粗的滚木。
男子走上滚木,叫沈夕走上来。沈夕咽了咽口水,飘身跃上,岂知那滚木被河水冲刷的极其光滑,脚下生不住力,立时偏歪下去。男子一按他肩头,沈夕便即站稳,宛如站在平地上一般。沈夕朝男子投去惊佩的目光,心想:“这人好强,单这份助他人定身的功力,自己就万难做到!”
脚踩滚木,顺河而下,绕出两座山谷,潭水陡然变宽。男子说道:“我们走。”衣袖飘然,跃到岸上。沈夕也要跃过去,脚下一轻,滚木霎时间沉入谭底。沈夕月步连施,踏水急行,一声呼啸,落到男子身边。男子面容带笑,赞道:“好轻功!”沈夕也是一笑,却笑得极为勉强,刚才哪是男子定住自己,是他定住了滚木,让滚木浮在水面上,天下有这等控制他物的神功吗?
越想越觉奇怪,大长老小园子他们不让自己踏过木桥,莫非是防范此人?此人修为极高,性格倒平顺得很,不似为非作歹之辈,又防范他做什么?
随了男子一阵,水潭也渐渐汇成了大河,河水清清,亮可见底。河面靠岸边处停了艘竹船,船上坐了个长须艄公。男子走过去,艄公立马起身,绕过男子来到岸上,头一抬未抬,口中也不说一句话。
沈夕跟着上船,趁机打量起那艄公,却见艄公额头冷汗直流,握着木桨的手背瑟瑟颤抖,暗暗称奇:“这人怎么了?生病了?”
进了船舱,男子不施礼让,坐于当中端茶自饮。沈夕不住朝外张望,脚下猛地一晃,船竟离岸驶动起来。沈夕指着岸上的艄公道:“他…他不是…”男子道:“那只是看船的,不是开船的。”
沈夕大感惊异,他不开船拿着船桨做什么,这船还能自己动?
男子抬头看他一眼,说道:“此处河谭名叫死水波,水底有暗潮,若无人掌舵,船便自行随潮飘流。看船之时,既要拨动木浆稳住船身,又要用真气抵御水中瘴气,那人能支持一天时间,很不错了。”
沈夕惊道:“原来他是修真之人!”
男子道:“疯人院的五卅你都见过了吧,听说谢少殇还和你结成了泯恨之交,可喜可贺。”沈夕奇道:“你认识谢公子?”男子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他进疯人院便是我荐来的。谢少殇脾气古怪,和我倒合得来,你是他朋友,自然而然也是我朋友了。实不相瞒,把你叫进失落林,其实也是受谢少殇所托。”
沈夕啊了一声道:“他现在在哪里?”
男子道:“怎么,你没寻到他?”沈夕道:“疯人院找了几次,没找到。”男子笑道:“他哪是呆得住的人,大长老的话,他是不会入心的。只怕他早出了疯人院,去西山了。”
沈夕点了点头,望向船外,不知不觉间,河岸已消失在视野外。忽地想起一事,问道:“相识几日,我们都还不知对方是谁,在下…”男子放下茶水道:“你的名字我已知晓,不必说了。”沈夕又道:“那你是…”
男子缓缓的道:“疯人院从首代长老起,共传七代,大长老是第七代,我是第六代。”沈夕指着他,大叫道:“原来你就是上任长老!”男子道:“做了两年,做不习惯,便辞让了。”沈夕忙道:“你有这等修为,称号该是万卅以上吧?”男子笑道:“我没有称号,长老是不封称号的。”沈夕道:“咦?如今的大长老不是排行第一么?”
男子哈哈一笑,道:“这是大长老他亲口说的?在谢少殇之上,疯人院排行第一的万卅,朋友不是刚刚见了,看船的艄公,他就是疯人院唯一的万卅。”
沈夕瞪大眼珠,喃喃道:“那老伯…那老伯…为你看船,还是万卅,前辈究竟是…”男子道:“我姓秦,名叫秦无极。”
沈夕只觉头晕目眩,浑身瘫软,秦无极的名字自己怎会没听过,王道长赞不绝口的五位天下奇人,秦无极最为神秘,道长都没见过,自己竟无意间幸见,原来就是疯人院的前任长老!
秦无极道:“你很惊讶,听过我名字?”
沈夕一想道长和他齐名,自己晚了一辈,当以长辈相见,俯身就要拜倒。秦无极道:“谢少殇和我举杯对坐,你又拜什么,朋友之间,没有辈分一说的。”沈夕愕然一阵,收拳呆立。
及到午时,船行到河道下游,晃动微缓,沈夕凑出头去看,只见两岸高山耸立,木楼悬崖而设,大大小小竟有十几排,宛如一方水上城镇。任由竹船靠岸,两人并身而出,登上云梯,绕山行了半晌,前方半山腰处赫然立着一家露天酒栈。青旗呼哧飞展,“避风舍”三字遥遥可见。走进酒栈,一个苗家姑娘笑颜迎上,把两人领进靠崖的雅座。
苗家姑娘似乎和秦无极相识,不等他吩咐,便招呼跑堂的去准备肉菜。苗家姑娘细细看了沈夕几眼,笑问道:“这位阿哥是谁啊?”
沈夕正要答话,秦无极道:“朋友。”苗家姑娘笑道:“原来是贵客,万不能怠慢,阿妹叫后厨多加几个菜,秦先生,这账可记在我头上喽!”
秦无极道:“不知我这朋友饮不饮酒,把米酒换成枣子烈,或符他口味。”
苗家姑娘点点头,靠近沈夕,轻轻搂住他肩膀,低声道:“秦先生经常到这里来,阿哥就别见外,你年龄比我小,有吩咐叫声阿姐啊!”在他脖间一吻,笑嘻嘻离去。
沈夕从前只接触过两个女子,桓若卿是自己的师姐,云笙如同自己的妹妹,被这样一个陌生苗家女子亲吻,登时面红耳赤,血液澎湃。他正值青春年华,岂能经受这样的刺激,阿姐阿姐的声音不住在耳边回荡,尴尬难堪,忙侧开头去。
酒菜呈上,秦无极倒上烈酒,向沈夕一端,一口饮尽。沈夕也倒了一碗,喝下半盏,偷偷斜睨上酒台。只听秦无极道:“那姑娘,你喜欢吗?”
沈夕哎呦一声,剩下的半盏酒倾洒出来。秦无极道:“喜欢的话,叫声阿姐,她便会来。”
沈夕连连摇头道:“我们素不相识,怎谈得上喜欢二字,只是…只是…咦,她的话你都听到了?”脸上微露惊讶之色。秦无极笑了笑,指指耳朵道:“有些话,你听不去也难,别人说,你就得听,只因这东西就长在我们嘴巴旁边。”饮下两碗酒,手指在碗边轻轻敲击,说道:“就如人的一生,冥冥中都已安排好了。”
沈夕道:“冥冥中安排好的?先生话意,晚辈可听不明白。”秦无极道:“在这个世界里,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让你对这个世界感到空虚,绝望,甚至有些恐惧?”沈夕道:“先生酒量如何,不如都别喝了,我们…”秦无极一摇头,道:“酒我醉过,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只是想问你,你觉得这世界真实吗?有没有一种特殊时候,仿佛天下间只有自己一人,孤单无助,其余都是冥冥中安设好的?”
沈夕想了想,答道:“在我小时候,有个道长为了救我跌落山崖,那时我茫然无助,也很寂寞。”秦无极道:“他是你感激的人,你有恨过的人吗?”沈夕想起迟远心,此人逼使自己和桓若卿离开圣火宫,四处漂泊,最后两人异地相隔,一拍桌子道:“恨过!时间一久,倒不像从前那么恨他了…”
秦无极道:“说是恨,倒不如说是厌恶。我也有厌恶之人,不过不是一个人,是很多。”沈夕好奇道:“都是哪些人?”秦无极道:“不是哪些人,是哪一类人。”话音一停,续道:“这些人,你恨也罢,不恨也罢,相遇也罢,不遇也罢,想法早已根深蒂固地植入我们心中,就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外力,它让你喜欢谁,你就会喜欢谁,让你恨谁,你就记恨一辈子,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人类的命运冥冥中似已注定,你明日该做什么,那力量便指引你前进,指引你去做,即便那力量微不可察,潜默所思,总能感觉得到。命运是双无形的大手,而我们只是木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逃脱,终究离不开那双大手的掌控,就是死,有时候也由不得自己作决。”
沈夕手抚烈酒,默默喝下剩余的半盏。秦无极道:“你我相识,是巧合吗?第一,你修真聚气,在修真路上,你我已是同类。其二,你遇到了很多高手,有这些高人指点,实力逐渐提升,和谢少殇这样的年轻一辈过招,自然解释得过。其三,谢少殇认识我,有他在中间做介,咱们不就相识了。”也饮下一碗,冲沈夕一笑。
沈夕心中琢磨:“秦先生也会有恨忌的人,他这般厉害,谁敢惹他呢?那双无形大手被他说得如此玄妙,究竟又是什么力量?”见秦无极不再叙说,倚着崖楼自斟自饮,蓦地里一股悲怆之意袭上心头,忍不住大饮几盏。
过不多时,只听踢踏踢踏上楼之声,赶上来两个脏兮兮的乞丐。这两个乞丐衣衫褴褛,乌发蓬头,栈中客人全移去目光。其中一个微胖的乞丐呸地吐了口痰,大摇大摆走向最近的酒桌,一敲桌子,吆喝道:“富家子弟富家相,施舍穷人几银两。不嫌少,不嫌多,剩菜剩酒也凑合。大爷们,慷慨点吧!”
那酒桌上的客人脸现鄙夷之色,哗啦抖出一把碎银,挥手道:“快走,快走,别扰了我们兴致。”
胖乞丐颔首微笑,包起银子走向第二桌,仍是先唱再乞,也捞了不少钱物。
沈夕看得连连称奇,南疆人有这么富裕吗,施舍乞丐的银子竟比自己腰包里的还多。眼见两名乞丐向自己桌子走来,摸向腰间,只有不到十两银子,难道也要舍给他们?
这时那苗家姑娘叫了声:“站住!”两名乞丐登时停步回望过去,胖乞丐笑道:“老板娘肯出血了?我们讨的是客人的礼,你的可不要。”
苗家姑娘哼了一声,指着沈夕那桌说道:“店里的客人你随便乞讨便是,这桌碰不得!”胖乞丐道:“为何?是你的老相好吗?我怎么一次面都没见过,刚认识的吧?”另一个乞丐立时捧腹大笑。
苗家姑娘冷冷道:“是不是相好,关你屁事,我店里有牛肉有羊肉,偏偏缺了人肉,你胆子大,尽管向这桌讨就是,只怕银子没讨到,人肉先捞着几十斤。”胖乞丐笑道:“此话怎讲?”苗家姑娘道:“乞丐虽然肮脏了些,死了不一样是人肉一堆么?”
咔嚓一声,廋的乞丐拔刀出鞘,把沈夕的桌子削下一大块,高声道:“你想要我们的肉,先看看这把刀再说!”
那刀上擦满了黑乎乎的油渍,桌子被斩处也腐烂了一片,刀上竟似涂满了剧毒。
苗家姑娘道:“我说怎么这般蛮横,原来两位练成了‘卯时命’。”廋乞丐道:“有眼光,这卯时命一旦沾上,绝活不到第二日卯时,知道此毒还给爷们道歉?”
苗家姑娘道:“我话没说完,瞎嚷嚷什么,卯时命啊,人家未必怕呢!”
两个乞丐相视一眼,哈哈大笑。廋乞丐举刀朝沈夕一横,道:“喂,她说你不怕,你到底怕不怕?”
沈夕心想:“这俩人哪是乞讨的,原来是打劫的,若在这里起了冲突,这家店可就毁了。”当即拿出银子甩在桌上。胖乞丐一声不响兜起。廋乞丐轻蔑一笑道:“怂包一个,谅你也不敢和我们作对。”收刀挥向秦无极,喝道:“轮到你了!”
沈夕忿忿不已,忍不住想要发作,忽地一想:“秦无极是五尊之一,他该怎么应对眼前情形?”
秦无极酒盏停在嘴边,问道:“两位从何处来?以前谋过面么?”
廋乞丐道:“你也配打听我们来路,你又从何处来?”秦无极道:“顺水南下,来自死水波。”当的一声,砍刀落地,廋乞丐慌忙捡起,死死捏在手中道:“死…死水波?你们果真从那死亡之地渡来?”
胖乞丐打量秦无极半晌,拉过廋乞丐道:“这人很古怪,先别讨了。”廋乞丐呸了一声,叫道:“他要来自死水波,老子就是疯人院的,死水波怎么了,不就是毒瘴之谭吗,他有办法抵御瘴气,未必就能挡住咱们的卯时命!”银光一闪,径直砍向秦无极。
刀到中途,吱吱声响,廋乞丐竟拿不住刀身,撒手放开。但见那砍刀吱吱响个不停,上面的黑油剧毒如纸片般卷起,顷刻间化为黑雾,罩向廋乞丐。廋乞丐大惊,想去抽刀,冷不丁腰间中了一脚,扑通滚将开去。
踢他的是胖乞丐,踢了他一脚,慌不择路往后便逃,绕店兜了一圈,躲过黑雾,冷冷打量起秦无极。
廋乞丐骂道:“你踢老子干甚么!”胖乞丐道:“不踢你,咱们的命早没了,快看前面。”廋乞丐骂骂咧咧起身,却见那砍刀仍悬在半空,刀边腐朽,滴下铁水,最后只剩一把刀柄。秦无极从容走向那黑雾,伸手轻撩,黑雾渐渐转淡,竟而消失。廋乞丐大声惊呼:“这厮竟能化去卯时命!”
胖乞丐也震惊不已,正想喝问,抖觉脖间一凉,被秦无极抓个正着。廋乞丐哇哇大叫,张臂扑上,身子刚离地而起,行动就此顿停,也和那刀一般,悬停在半空中。
秦无极道:“刀有刀的使法,毒有毒的妙用,以毒喂刀,焉成正统。”松开胖乞丐,翻掌覆下,那毒雾重新聚拢,竟而化成一张椅子。秦无极放下黑椅,道:“请坐。”说罢回到酒桌,继续饮酒。
胖乞丐从未见过这等控毒神功,以为是妖法,哪敢推拒,恭恭敬敬端坐其上。廋乞丐摆脱禁锢,瞧瞧秦无极,又瞧瞧胖乞丐,快步抢到胖乞丐身边,和他同挤那张黑椅。
众宾客看傻了眼,都停筷不吃。苗家姑娘摆手道:“没事,没事,两只莽撞的小家伙而已,现在老实了。”
黑椅矮窄,胖廋乞丐挤不开,大腿摞在一起,乖乖地看着秦无极,眼珠丝毫不敢乱错。沈夕暗觉好笑,低头扒饭。廋乞丐道:“大…大爷,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敢问你刚才化毒的功夫是什么名堂?”
秦无极微微一笑,端酒递过去道:“喝点吗?”廋乞丐道:“不…不敢喝,大爷真有诚意,喝点倒也不错…”胖乞丐低声道:“住口!”廋乞丐哦了一声,便不再说。
秦无极道:“两位是风族的人物,风族没有祖传的卯时命练方,你们是怎么练成的?”
胖乞丐脸现惊色,随机转常,如实答道:“七蛇,五花,三斑虫,投入九目丹王鼎,武火而出。”秦无极道:“练给我看看。”胖乞丐道:“现在吗?可是没有毒方,也没有鼎,该如何…”秦无极道:“九目丹王鼎,盖子上是不是有九只孔?”胖乞丐道:“是。”秦无极单手支颐,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不时说道:“嗯,这里的鼎只有五目,不在这里…”
廋乞丐朝胖乞丐看了一眼,胖乞丐点头会意,两人便要离椅站起,刚要行动,那黑椅顿时分出四扇栅栏,将两人牢牢困住。便在此刻,店中有人喊道:“我的七蛇毒!”“我的五花”“谁在施法,老子怀里的三斑虫呢?”
沈夕不禁转头看向东首,上空飘了一堆毒虫草药,底下人张手伸够,毒草陡然移向,飞向胖廋乞丐。又听哗啦响动,一方四角齐人高的铜鼎撞窗而入,哐当一声,落在胖廋乞丐跟前。
秦无极睁开眼睛,笑道:“毒方丹鼎已齐,现在可以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