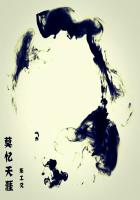桓若卿自小呆在圣火宫,从未下过山,外面的世界怎样,民俗民风如何,鲜有耳闻。这日来到一处村镇,桓若卿问沈夕道:“你饿不饿?”沈夕摇了摇头。桓若卿道:“走了两天,咱们东西没吃,觉也没睡,得先找个地方歇歇,是先吃饭还是先睡觉?”沈夕又摇了摇头。桓若卿道:“想什么呐,怎么问什么都摇头?”不等沈夕回答,见旁边有个摊子,摊子上热气蒸腾,抢先挤了过去。
那摊子是卖贴饼的。卖家一瞧来了生意,手上面粉搓了搓,凑过头来微笑道:“姑娘要饼?”
桓若卿道:“这东西好吃吗?”卖家道:“好吃,好吃,不好吃不收你钱。”桓若卿饥肠辘辘,拿起摊子上一张饼递给沈夕,自个又拿一张大嚼起来,见沈夕端着饼出神,叫道:“吃啊!”
沈夕道:“爹爹不知道我们出来,我…我想回去…”桓若卿道:“回去干什么….你打得过人家吗…过几天咱再回山上瞧瞧…”她说一句啃一口,眨眼间三张饼入肚,胡乱抹抹嘴道:“走,找睡的地方去。”
卖家见他俩作势离开,浑然没有给钱的意思,叫道:“姑娘,姑娘!”
桓若卿回头道:“干什么?”卖家道:“你的钱呢?”桓若卿道:“什么钱?银子?”
卖家见她衣冠楚楚,不像穷苦人家,说道:“买东西要给钱,姑娘不会连这道理都不懂吧?”
桓若卿道:“你东西摆大街上不就是让人吃的,怎么还要钱…”她虽不明世事,此刻也知道不付银子决计走不了,眼睛骨碌乱转,突然呸了几口,大声道:“难吃,难吃死啦,大家快来看,他的饼有毒。”卖家道:“姑娘,话可不能乱说…”桓若卿:“哎呦,哎呦,我快疼死了…”面色由红转白,捂着肚子缓缓倒下。
眼见路人围观过来,卖家一时慌了手脚,对桓若卿道:“姑娘,钱可不给,也别诬赖我啊,姑娘,你快起起!”伸手去扶她。一个行人道:“怪不得你生意不好,到底在面里和了什么?”卖家辩解道:“我没有…“那人又道:“人都这样了,还说没有,走,咱们去见官!”一把拉过卖家。
卖家有苦说不出,只得去求桓若卿,低头一看,地上空空如也,哪还有人在。
桓若卿带着沈夕挤出人群,长吐一口气,心想:“怎么这人和灭凡一个德行,动不动就要银子。”想起鬼刹教众人仍在和敌人拼斗,不由得一阵神伤。这时只听听沈夕问道:“公主,你肚子还疼吗?”桓若卿拍了他脑袋一下,道:“笨蛋,我那是装的。还有,这‘公主’二字其他人可以叫,你不能再叫了,叫我若卿好了。”回头一顾,见那卖家没有追来,这才宽下心,找了个安静地方美美睡了一觉,及到傍晚时分方动身北上。
一路行来,桓若卿渐渐知道了银两的作用,她身无寸文,坑蒙拐骗生抢硬夺倒挺拿手,自是冻饿不着。行到第十五日,距离圣火宫已有千里之遥,眼见房屋渐少,积雪渐厚,终于起了归意,可她身处极北,早已丢了方向,又怎识来路在哪。
转过几处土丘,遥遥看到一群中年人在驱赶雪鹿,甚感欢喜,大喊大叫一阵,向沈夕道:“走,咱们看看去。”沈夕不为所动,眼睛勉力张合,呼呼喘着粗气。
桓若卿道:“你怎么啦?”一摸他脸颊,吓了一跳,道:“怎么这么烫,你生病啦,姑姑说男孩子身体强壮,我没事,你倒弱得紧。”背起沈夕,朝那些驱鹿人追上去,边追边喊:“喂喂,有人会治病吗?”
那些人一瞧是两个小孩,以为谁家孩子出来胡闹,全不理会,继续驱赶。桓若卿道:“你们耳朵聋啦?”
驱鹿人终于停下来,见桓若卿奔近,打量她一番,道:“你们去哪?”
桓若卿道:“我问你们会不会治病,问我去哪干嘛,沈夕病了,你们谁会瞧病?”
最前方穿黄皮衣的驱鹿人见她说话举止飞扬跋扈,全无礼数可言,眉头大皱。其后走上来一人,向黄衣男子道:“齐风兄,这孩子好像真的病了。”黄衣男子冷哼一声道:“病就病了,人家有爹有娘,用得着咱们管?”那人又道:“可他得的是极地热,若是本地人,万不会染上这种病,齐风兄,要不…”
那叫齐风的男子一听‘极地热’,脸色微变,大步走上前,拿住沈夕脉搏摸来,喃喃道:“两日了,两日了,还剩半日…齐云,你身上可带了山耳?”后一句是向一穿厚袄的青年所问。
那青年自见到桓若卿就一直呆望着她,听齐风相问,摇了摇头,道:“都放庄里了。”又看向桓若卿。
齐风道:“那就回庄里,事不宜迟,救人要紧!”大手一摆,驱赶鹿群先行。
桓若卿道:“什么极地热,很严重吗?”齐风冷眼瞧向她,道:“要不是徐生兄出言相劝,没有人会搭理你们。快上鹿!”说着牵过一头壮鹿来,示意桓若卿沈夕骑上去。
桓若卿见他脸色不善,心想:“这人好生可恶,我哪里惹到他了,算了,等沈夕病好,再取他项上狗头不迟。”狠计已定,把沈夕放在鹿背上,自个也骑上去,跟着鹿群前行起来。
行了数里,到了一处庄院。桓若卿见庄门大开,两旁挂满了灯笼,与圣火宫自难相比,却也甚是端整好看。下得鹿来,进了庄子,当院竖了根大旗,旗帜随风飘展,上面写有“吕家庄”三个大字,暗暗寻思:“看这字面,庄家主人应该姓吕了。”
院内迎出一老者,约五六十岁,穿着甚是奢华,向齐风道:“今个怎么这么早回来?”齐风道:“路上有事,不敢耽搁。”那人道:“什么事比赶鹿还急,庄主要知道,齐风,你可要小心大麻烦啊。”齐风淡淡道:“不用陆总管提醒,齐风也甘愿受罚。”呼哨一声,引着鹿群往西面草棚去了。
这陆总管是吕家庄的大管家,掌管庄内仆厮诸事,职权甚大,齐风等人为吕家庄放鹿,虽不是吕家庄人,论尊位却属最下等。陆总管见齐风爱理不理的样子,颇为恼怒,不敢向他发火,指着徐生道:“看你们这些穷落魄,若不是庄主怜悯,早不知饿死在哪里了,还跟我摆架子,我明日就告知庄主,把你们全撵出去!”
几个驱鹿人气血上涌,正要拥上前,徐生伸手拦下,微笑道:“陆总管息怒,今日早归实是事出有因,等晚些时候,我送些鹿皮鹿角过去,天气冷了,你也添些厚衣,补补身子。”
陆总管道:“还是你明事理,不像那姓齐的…罢了罢了,今日之事就当没发生,可不能有下次。”徐生道:“那是当然。”陆总管得了好处岂不满意,点了点头,转身就要回屋。这时只听一个声音道:“喂,老混蛋,你刚才大骂一番,里面也包括本姑娘吗?”
那陆总管咦了一声,回过身来,向话音瞧去,见是一少年和少女,跳将起来,大叫道:“你…你们是什么人…你刚才骂我什么?来人啊,把他俩抓起来!”
他一声令下,庄里呼啦出来一大票人,手中各持银枪,在日光的照耀下,好不映眼。
陆总管手指桓若卿道:“这女娃子敢骂老夫,给我杀了他!”
众庄卫正要上前,徐生拉过桓若卿,赔笑道:“她是我远房的一个表妹,脾气有点古怪,刚才话语得罪了陆总管,我徐生先陪个不是。表妹,还不向总管认错!”
桓若卿呸了一声道:“谁是你表妹。”转头向陆总管道:“老混蛋,我就骂你了,你能把我怎样,你要气不过,咱俩比划比划。”
陆总管面色铁青,嘿了一声道:“看齐风干的好事,鹿没放成,领了个女贼头回来!”举手作势,众庄卫哄然围上。只听屋内一个威严的声音道:“住手!”众庄卫当即止步,垂首散开,空出中间一条道。
屋内缓缓走出一人,青冠缎袍,相貌堂堂,是个中年男子。他一转目,众庄卫当即会意,再不理会桓若卿,纷纷退出了庄院。
桓若卿见此人举止不凡,那些庄卫又极听他话,笑问道:“你就是吕庄主吧?”
那人道:“不错,姑娘又是何人?”
桓若卿晃了晃脑袋,道:“我是谁你不必知道,刚才这糟老头无缘无故骂我,实在没有礼貌,你是一庄之首,要容许这等荒唐事发生,岂不失了威信,为了吕家庄,我劝你还是把这老头撵出去为妙!”
陆总管气的浑身哆嗦,骂道:“臭丫头,到底是谁没有礼貌,老夫责怪徐生,碍着你什么事…”
那缎袍人微微摇手,道:“陆伯,你先下去吧,这里有我。”
陆总管又怒又气,可庄主在场,不能再说什么,朝桓若卿狠狠瞪了一眼,忿忿离去。
缎袍人拱手道:“在下吕青鹏,既然姑娘不肯告知姓名,可否问问从哪里来?”桓若卿道:“西域。”缎袍人嗯了一声,道:“西域,西域…”沉思半晌,又道:“姑娘来所为何事?”
桓若卿把沈夕往前一推,道:“齐风那恶…齐风他说我师弟得了极地热,也不知是什么病,想来非常严重,他说要回庄里拿山耳来治,我们便跟了来,只可惜遇上你们庄的破管家,耽误了些时候,你还是把那管家…”
吕青鹏哈哈笑道:“原来是水土不服之症,也没什么大不了,区区山耳杏菇这些药材,放在市面那是稀物,本庄应有尽有,快快扶你师弟进屋,我来救他。”
桓若卿见这人语气和缓,气概豪爽,竖起拇指道:“你这庄主好,有大家之风。”吕青鹏获赞,抚掌哈哈大笑。桓若卿刚要随他进屋,忽觉背后有人拉了下自己,回头一看,是那叫齐云的青年。
齐云摇了摇手,示意他不要进去。桓若卿眉头一皱,刚要相问,吕青鹏道:“姑娘迟疑什么,是怕我加害于你么,再等些时候,你那师弟性命可真的难保了。”桓若卿道:“来啦!”拉起沈夕,快步跟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