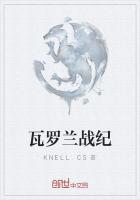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况且还有母亲,众人根本拦不住邬启迪。爱小轩很是着急,就问王从容该怎么办。王从容让木迎春先陪毕生和傅小珍去城里,待处理完毕家的事情后,就去茅屋村与他会合。
待三人应命而去,元哲皓说:“下官得去请示一下伍大人。”
王从容只说回头他会跟伍元子说的,便与元哲皓、爱小轩、黄小燕和马五一起追赶邬启迪,可是哪里赶得上他呢。过了好一会儿,邬启迪已追上了吕有为等人,大怒,指着湛愤,厉声说:“是不是你杀害了我父亲母亲?”
在路过茅屋村的时候,见邬老伯门前挂着丧榜等物什,已经知道了大概,此时湛愤才知死了的正是邬启迪的父母,便说:“真是晦气!原来那俩老东西还有个小东西!”
邬启迪的愤怒已经到了极限,没有二话,一拔出剑来就刺向湛愤的咽喉。湛愤看得明白,本来他的话就是为了激怒邬启迪,遂即刻接招。
邬启迪虽有为父母报仇的心,也有出剑之力,却是一直处于激愤的状态,剑招和步法的配合有些乱。同时,他每日还兼着算卦之事以及嵩山书院的先生身份。而湛愤呢,在登封县里,虽然有崭露头角,但是都被木迎春和王从容给搅和了,而且吕有为和余天希也向着他们二人,所以他心里一直憋着火气,遇到了邬启迪,正是他泄火的时候。嵩山派有刻苦练武的门规,湛愤虽是余天明的管家,不是十分勤苦,但也是多有习剑。
相比之下,自然湛愤的赢面更大。故刚过了三十来回合,邬启迪就败下阵来。因为吕有为昨日刚教训过他,湛愤这次就没下狠手,拿剑指着邬启迪,说:“你刚死了爹娘,要是杀了你,还辱没了我嵩山派的名声。你且回去,等长了本事,湛爷再陪你玩玩。”
邬启迪气愤不过,但也打不过他,却说:“你杀了我父母,还说……哼……我杀了你!”
余天希忙拦住了他,说:“邬老师,您父母是在下亲自送他们到家门口的,虽然有伤,但也不至死。我想其中会不会有误会啊?”
“误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现在我就杀了你!”
“湛爷我说过不杀生就不杀生,你小子别不知好歹。”
“杀了人,你还口出狂言,真不知死字怎么写吗?”
“吕某也可以为湛管家作证,他的那一脚的确不会要人性命的。邬老师,你先冷静冷静。”
“都是蛇鼠一窝,你们的话谁信哪!”
“就算是我杀了你父母,那又怎么样?你那点本事,能为父报仇吗?躲一边去,你湛爷还要回山上复命呢。”
“大家都听到了吧,这位湛管家亲口承认是他杀了我父母。”
“我真不想杀人,你小子别再逼我了。”
邬启迪一心只想着为父母报仇,听了湛愤的话,也拔出剑来。余天希再次拦下了他,轻声的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的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邬老师,你别冲动,先想想爱姑娘,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可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
听了余天希的话,特别是说到爱小轩,邬启迪就停了一下,扔了手中的剑,瘫坐在了地上,愤怒不语,眼睁睁的看着湛愤等人上了嵩山。
过了好一会儿,众人赶来,见了邬启迪这般样子,爱小轩多有安慰,只是他面如死灰,一点反应也没有。无论王从容怎么问,邬启迪就是只字不提。无奈之下,众人只好先回茅屋村,去了邬老伯的家中。此时,木迎春、毕生和傅小珍也赶到了,正见邬启迪两行眼泪,俯倒在邬氏夫妇的尸体旁。哭诉之后,邬启迪才说起追上湛愤后的事情,然后说:“孩儿一定杀了湛愤,为您们报仇!”
王从容让元哲皓检查尸身。一切正如马五所说的一样,邬老伯胸口有一个脚印,伍大娘的后背有一大块淤青。元哲皓说:“二老都是丑时死的。邬老伯只有胸口受伤,伍大娘背上有撞上石头的痕迹。”
木迎春说:“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老弱,还侮辱人,这湛愤真是丧尽天良,简直就不是个东西。邬大哥,我陪你上嵩山,一定为邬老伯和伍大娘讨回公道。”
众人都愿意跟着去。只有王从容阻止了他们,说:“且慢,你们别冲动。湛愤说得对,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背后还有整个嵩山派。”
“余盟主是整个武林的盟主,那是他还不知道他儿子的管家有多么嚣张,多么狂妄,还草菅人命。要是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就是。自古以来,杀人者死。我就不信他余盟主敢包庇自己门下的人。”
“像这种禽兽不如的人,就该偿命,好让邬老伯和伍大娘瞑目。”
众人议论纷纷。
王从容说:“你们说的都对。但是,你们想想湛愤在城里的言行,只有在他惹了众怒,吕前辈和余三公子才稍加制止。可想而知,湛愤根本没有把他们二人放在眼里,更何况是我们呢。再者说,包庇属下的事情,你们也不是没见过。要知道,他可是余大公子的管家。要是余盟主真护短,闭而不见,我们又该如何?”
木迎春很气愤,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公道是要讨回的,只是我们的分量不够。”
“你倒是说呀,我们该怎么办?”
“等,只能等到大哥来了,让他拿主意。”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八月十五就是武林大会的日子,大哥肯定会来的。晚些时候,我去写封信,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先告诉大哥。”
众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王从容的。随后,邬启迪披麻戴孝,在家里设了灵堂,众人吊唁自不必细说。到了申时,元哲皓回了登封县城,马五也回去了,王从容还是不见邬启迪的师父前来,就问他是何缘由。
邬启迪知道王从容的想法,说:“师父他老人家虽然住在茅屋村,却是最里面的房子,也很少与人接触。当然,除了我和马五。”
“那他平时都做些什么?”
“除了读书,就是刻碑文。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碑文也是一碑难求的。”
“此话怎讲?”
“像安晴民、常得善和卞大庄就得到了,而时在壬和齐阳就没有。特别是余盟主,即便他本人来了,也被拒之门外。”
“那茅屋村的人呢?”
“一半一半。”
“那价钱呢?”
“难说。有要几个钱的,也有要几十两的,甚至几百两的。”
王从容叹了口气,说:“唉,真是古怪脾气。那我能见上一见吗?”
“难说。”
王从容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