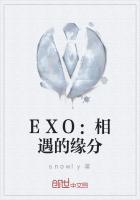文家庄东边的野地里走着一个少年。他十五六岁的年纪,身着淡青色儒衫,前摆上赫然有一道撕裂的大口子,里面的灰色长裤随着他蹒跚的步伐时隐时现;脚上一双黑色的方头布鞋一只沾满了泥土,另一只湿漉漉的,看样子是踩到了水坑里;唯一还算干净的只有他头上的青色儒冠,与其他脏兮兮的衣物形成了较鲜明的对比。
这个人就是文家嫡长孙,文叹。
他背着崭新的紫竹书箱,手里却是握着一柄锄头的长柄。脸上满是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一双本该闪烁的眼睛此时遥遥欲闭,牙齿透过半张的嘴唇,更衬出嘴唇的干裂。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吹过,让文叹不禁打了个寒战。他发现自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他打量着四周。这里不是适合耕种的土地,却是野草的乐园。这一片区域是狗尾草和马唐草的天下。他们两个仿佛是两股军队,无时无刻不在争斗着。
文叹一眼就看到了那座新坟。不过短短半天时间,已经有狗尾草想要占领这座高地了。越来越暗的天色让文叹感觉后背发凉。后背吹来的阴风让他感觉一阵阵发冷。
文叹是来挖坟的!
“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文叹把心一横。他把书箱丢在地上。抡起锄头狠狠地向坟包砸去!
文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挖坟!别说挖坟,他从来就没有碰过锄头之类的农具。而事实上,自文家老太公被赐同进士出身之后,文家往下数三代,再没有一个人碰过农具了。文叹的手握的是关东辽毫,蘸的是清烟松墨。他背的不是“寸麦不怕尺水”的农谚,而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的圣人言语。
文叹轻叹了一口气,心道:“我果然不适合挖坟。”他已经感觉自己的后背和臂膀隐隐作痛了。由于握锄头的姿势不对,他的手腕也十分疲劳。他给自己打气:“我答应了她的!一定要救她的!”文叹甩了甩手,继续挖坟。
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了。坟包终于矮了下去,又继续凹了下去。文叹的儒衫已经湿透了。他已经累得嘴唇直颤,但是还是正了正自己的儒冠。“我应该向老张要一柄锹的!”他终于发现自己的锄头挖坟其实并不顺手。
终于,文叹再一次挥动锄头的时候,发出了“咚”的一声。“挖到了!”文叹喜上眉梢,士气大振,手上不停,浮土刨开,露出一个烂木棺材。
他急急忙忙用锄头撬开棺盖,往里一看,顿时喜极而泣。
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少女。她上身穿着碎花衣衫,下身紧腿赭库配一条碎花短裙。她好像正在熟睡,不过脸上还挂着泪痕。少女手脚都被绳子绑了起来。
文叹纵身跳下棺材,将少女扶了起来。他将少女靠在自己的肩头,轻声而又焦急地呼唤着少女的名字:“白婉云!婉云!我来救你了!”
婉云嘤了一声,努力地睁开双眼。看到文叹的那一刻,婉云觉得受的所有的委屈都值得了!她嘶哑的叫了一声“叹哥”。而这声呼唤让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杂草丛生的荒野中,一座被挖开的新坟旁边,少年和少女放声大哭,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让自己一生都难忘的一夜。
涂阳在独山之南,涂水之北。独山上怪石嶙峋,山下又有美石出世。十年之前,金枪申丰雄独自往独山深处苦修枪术一月有余,出山之时竟然带出一块绝世美玉来。从此独山出美玉的消息也传播开来。
独山中的深潭之下又能凿出寒气逼人的石板来。据说这种石板乃是受了万年寒潭水的浸泡,只要这么巴掌大的一小块,就能让整个屋子凉快下来。在炎热的夏季,独山的石板是大户人家最喜爱的消暑器件。文叹在文家的书房里面也有这么一块。可是夏天的时候,文叹还是觉得热。
涂水自独山而出,往东南流去。顺流而下可经过竹山,转往东去,过空桑,曹夕,直至大都城余俄,转南汇入大河,而入东海。
涂阳山有出产,又有涂水的水运,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十年之前金枪申丰雄一夜暴富的故事,让涂阳人口与日俱增。到了如今,涂阳已经是十分繁荣的大县了。
涂阳城西的一处包子铺,一对少年少女正在吃包子。那个头上扎着麻花辫,拿着包子欢快地啃着的少女正是白婉云。那个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吃包子,口中有东西绝不说话的正是文叹。两个人连夜往东赶路至涂阳,早上城门开的时候,就由西门进入。
文叹把最后一口包子咽下,发愁道:“不出门不知道钱财重要。我的紫竹书箱和笔墨都当了,才得了几块碎银!云妹,没想到一对铁刀就花掉了所有的钱。今天我们在哪里落脚?”
白婉云用力地把第五个包子咽了下去,用手满意地拍了拍用破布包裹起来的铁刀说道:“这可是我吃饭的家伙!叹哥你就瞧好吧。今天的住宿包在我身上了!”
文叹惊道:“云妹你该不会是要……劫道!这怎么成?”
白婉云急道:“别叫别叫!让人误会了怎么办?劫什么道?我这是要去卖艺!”
看着白婉云的自信的样子,文叹不由得想起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三年前,文家老太爷九十大寿,却突发奇想的想看武艺班子耍把式。老太爷说:“我与笔墨纸砚打了一辈子交道,到死了却想见识见识刀光剑影。”于是唱戏的班子被换成了白家班。
白家班的班主正是白婉云的爹,叫做白三水。他自称祖传白家刀法乃是阵前刀法,刀刀力大,刀刀致命的。白三水门下有五个弟子,白婉云是第六个。白三水总说“白家刀要绝了,婉云是个女儿身,使不出白家刀精髓”之类的话云云。但是白婉云在文老太爷九十大寿当晚还是上了台表演。
白三水和弟子们的确很有本事,他们刀法势大力沉。一刀下去,碗口粗的木头一下子就劈断了;顶在仆役头上的沙果,上半部被切掉了,下半部还留在仆役头上。但是就算他们的两人对打也让人提不起兴致。他们在台上打成一团,文家人,包括文叹都在台下打哈欠。这种直来直去的攻守实在没有看头。
直到焦急的白婉云上台,所有人都眼前一亮。一身短打,扎着麻花辫的白婉云十分漂亮可爱。白三水和弟子们都使的单刀,而白婉云却是使双刀。她把两柄刀都磨得锃亮,武动起来犹如两团白光在她手上不断地飞舞。文家观看的人都不禁叫起好来。
就是在这次表演之后,白三水接受了白家班留在文家做护院的聘请。而白婉云自然地也在文家流了下来。
“想什么呢?”白婉云挥手打断了文叹的回忆,她说:“叹哥你赶紧把最后一个包子吃了!西市的人渐渐多了,一会儿我们赶紧去占个好地方。”
看着白婉云盯着包子看,文叹笑了一下说道:“我已经吃饱了。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白婉云内心挣扎了一下,说道:“好吧!可不能浪费了!那我就帮你把它吃掉吧!”
白婉云在文叹惊奇的目光下,快速地吃下了八个包子中的第六个。
担心住宿费的文叹和自信满满的白婉云往西市口走去。文叹十分担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他甚至有点怀疑白婉云是否能赚到钱。除了像文家这样的大户人家请班子,难道还有其他的办法用武艺赚到钱吗?而且文叹感觉自己根本帮不上忙。
忽然文叹看到前面人头聚成一团,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白婉云一下子就来了兴致,她高兴地说道:“叹哥,我们快去看热闹!”
白婉云扒开人群。文叹跟着走上前,却看见了令他难以置信的一幕!原来人们围观的是打人!不是两方斗殴,也不是流氓斗狠,而是几个衣着光鲜的士子在殴打一个老乞丐!
那个老乞丐跌倒在地,用手握住脑袋,不停地呻吟求饶。他满头白发沾染了鲜红的血迹,原本就褴褛的衣衫被打得更加破烂。老乞丐被打的满地打滚,那几个士子却打得愈加欢快!他们衣服也皱了,儒冠也歪了,连手上的折扇都打断了!
文叹生气道:“怎能如此?”说罢就要上前阻止打人的士子。
但白婉云赶紧拉住了他:“文叹哥,这事儿我们不能管!”
文叹正色道:“怎么不能管?朗朗乾坤,殴打孤老,罔顾王法!我不能不管!子曰:‘乡愿,德之贼也。’我不会做乡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