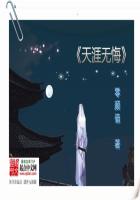胤祯直挺挺的跪在帐内,把匆匆赶回的墨涵唬了一跳,也顾不得细究缘由,急着要入内帐去看胤禩的伤势,却被胤禟拦住:“墨涵,别看!太医正清洗伤口呢!”说实在的,连他都不忍细看,胤锇也只看了两眼就躲到一旁。
“涵儿,把十四弟送回去吧!他听你的!”胤禩的声音传来,温和如常,“没什么大碍,是我自己不小心,十四弟与我同行,见我受伤,惹他内疚自责,你且劝劝他!”
墨涵满心狐疑,却答应着去扶了胤祯起身,他是一脸愧疚,不敢直视,她料定胤禩的伤不像说的那般轻巧,知道他是顾惜她,才咬牙忍住。她大声道:“那我去去就回!”她拉着胤祯出去,见他满脸尘土,还有些划伤的血口,正要细问,胤祯却又反身进帐,径直进了内帐,一下跪倒地上,道:“八哥,求你忘了弟弟的诸般不是。今后,但凡有令,胤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说完,他也不管众人的反应,起身大步流星而去。墨涵忙叫胤锇跟去看着他。
墨涵这才近前去瞧胤禩,虽然心惊心疼,却极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他伤在右臂,整条衣袖已如破絮,露出血肉模糊的处处伤口,又有尘土粘在上面。那伤并非刀剑所致,倒像是中了有回刺的钩、戟,撕拉得皮肉回翻。那伤不止一处两处,绽开的血肉恰如片片鲤鱼红鳞,点点痛在墨涵心口。太医正剪开衣袖,慢慢用盐水清洗伤处。
她上前紧紧握住胤禩的左手,反倒是他着力回握,一边平和的笑着,宽慰着她的心:“这点伤算什么,小时候练骑射早就摔打惯了,不觉着痛。倒是你提心吊胆的样子让我放不下心。”
她勉强挤出笑容,但看那盐水已变得猩红,赶紧吩咐:“水换得勤些!否则伤口间容易交叉感染。”又问胤禩:“可服了白药?”
胤禩还是云淡风轻的笑着:“你再好强,医术可不及杜太医!你能想到的,太医就不知么?别操心了!只可惜今日猎到的狐狸毛色皆非上乘,怕入不了你的眼。抱歉了!”
“是你亲手猎的,我岂有不喜欢的道理?该我说声多谢才是!”她嫣然一笑,心底却是无比酸楚,为着他的伤,更为着他无时无刻的体贴入微。她望着他的眸子,那里只写着深情,写着爱恋。
杜太医仔细瞧着洗去尘土后的伤口,问:“贝勒爷,臣斗胆问一句,是何物致伤?”
墨涵却抢先答道:“杜太医,肯定是利器所伤,创面又众,玉真散是一定得内外兼用的。”
杜太医连连点头,赶紧让跟着的小太监去取,复又取出碘酊处理伤口。
却原来胤禩一直未曾言明因何受伤,胤禟也迫切的想知道,问:“八哥,究竟出了何事?就为了那银狐么?”
“十四弟的马受了惊吓,我赶上去勒他马缰,谁知他被颠下马,我去抓他时,不小心被靴子上的马刺刮伤的。”他轻描淡写的诉说,可想及胤祯低头认错之举,胤禟与墨涵对视一眼,都明白其时情形定是千钧一发、险之又险。
那碘酊清洗伤口的痛楚比盐水更甚,胤禩已在咬牙强撑,墨涵实在不忍再看,只闭上眼将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所谓有难同当,实在需要惊人的勇气与毅力。他却用手指轻轻摩挲她的脸颊,安抚她的情绪。二人再次四目相对,彼此将心看得更加透彻。
“奴才沃和纳给八爷、九爷、格格请安!”沃和纳实在不敢再等,直接寻来,却记着胤礽的嘱咐,一定得避开墨涵,私下与胤禩谈。
墨涵只当他是来找自己的:“沃和纳,有事么?可是表哥有什么事?”
“回格格的话,太子爷大安,只是今日围猎受了寒,太医已请了脉,无碍,略歇歇就没事了。”沃和纳低头说着,手却在地上比着暗号。
胤禩心中正愁如何支开她,却听外面奏报,说是老爷子宣墨涵去龙帐见驾,他连忙叫胤禟陪着墨涵前去。墨涵虽不情愿,也无法,犹豫片刻,只得不舍得去了。沃和纳趁机提议他留下帮帮手,墨涵倒不起疑,只觉得好歹这是放心的人。
来宣旨的太监与胤禟相熟,在途中低声道:“十八阿哥不见了,皇上正着人四处寻找呢!”
胤禟瞪他一眼,所幸墨涵心里只记挂着胤禩的伤势,不曾留意,他自然晓得她一路上关怀胤衸的事。他苦笑一下,墨涵与八哥却是一样的操心命,自己的日子尚朝不保夕,却处处挂念他人。
“墨涵,**家堂叔可与你有来往?”
墨涵一怔,待他又问一遍才回神,道:“你不会毫无缘故说起吧?”
胤禟挥手让太监先行,压低声音道:“原先跟着你叔公的人并未全部落网,格尔芬手里还捏着那些人的把柄,他和阿尔吉善想跟着咱们!”他有些试探的意思,若墨涵首肯,就容易说服八哥,八哥心里好歹存了心思,自认是赫舍里家的女婿。
墨涵狠狠的骂一句:“二五崽!”
“你说什么?”
“别理那两个畜生!今日用别人的把柄来取悦你们,难保他日不落井下石。”墨涵的话从来没这样重过,“别猫三狗四的都笼络到门下,投机取巧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也把眼睛睁大些才是!”
胤禟面色一变,心下不悦,可墨涵却不察觉:“那个伍尔占到底有几成用处,你可掂量清楚了?别使了银子,却招惹祸端!”
她不见他回答,才留意他神色有异,心中也虽抱歉自己话语不留情,还是直言:“胤禟,我是想到什么就说,你别在意,若有冒犯之处,只有你多担待!”
他很快释然:“我还不知你么?走吧,赶紧应对了老爷子,去久了,八哥又该担心了!”
墨涵舒心一笑:“我和胤禩都该好好答谢你的!”
“说这话可就生分了!我想了,你的话有理,我远着这些人就是了!”
正说话间,瞧着胤祥一人从外回营,不见胤禛,墨涵待要上前解释误会,那宣旨的小太监已折返回来,催促道:“格格,劳格格驾,紧走两步,万岁爷在问了!”
墨涵只得朝胤祥挥挥手,示意他在外等她,胤祥点头答应着,她才安心进去。
墨涵听见一个熟悉却又显陌生的声音让她免跪,抬眼去看,老康颓然无神的靠在龙椅上,满面悲切,依稀是才哭过,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忽然担心自己的脑袋起来,窥见人隐私是最被嫉恨的,何况她窥视的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墨涵不自觉的将手捂在腹部,觉得隐隐作痛,她在心底暗道:“宝贝,我们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活得好好的!否则谁来陪伴你阿玛?”
站了良久,老康都没有一句话,墨涵却无法不负劳累的熬着,她自行坐下,也不主动开口,只暗自思量胤禩的伤势,又揣度老爷子何至于如此悲伤。
“胤礽疯了!”冷不防老康冒出这样一句,墨涵心中揣着自己的事,不经大脑就冒出大不敬的话:“也是皇阿玛逼出来的!”
老康震怒中起身,猛捶桌案,他原是希冀墨涵能巧言宽慰,却不料她却豁出胆子顶撞:“你说!朕还要怎样姑息你们?你和胤禩的事,朕已算默认了,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居然说出这样忤逆的话来?胤礽他是咎由自取,你们都是——”话未毕,就咳嗽不停,可依旧不甘,还在唾骂,“朕辛苦创下的基业拿给他们去由着性子争夺才对么?朕是要他们个个都——”话卡在喉咙里,已咳得脸红,竟有些憋气。
左右竟无个伺候的人,墨涵虽有气,到底不忍,上前给他捶着背,道:“天下都是皇阿玛的,皇子们的命原就是皇阿玛给的,何时要取,他们能做什么?无非洗干净脖子,翘首以待,早日有个结果早日投胎,来世再莫落在这帝王家!”
老康方止住喘,无力说话,只挥手让墨涵走到他身前,墨涵倒猜出他的意思,反正话到这份上,有些豁出去的意思:“皇阿玛要打儿臣,也请等将息好了再打,此刻使不出力气,起不到惩戒的效果。皇阿玛存了什么心思料理表哥与胤禩,儿臣猜得出几分,大不了走在前面,省得见他们受辱。”
她心中的怨气何止一点儿,竟觉得这个父亲对个个儿子都是亏欠的。老康冷哼一声,正待要训斥她,却听太监来报,说是太子在营帐中喝酒、摔东西,任谁都劝不住。
“宣太医去诊脉,哪里就那样容易疯了!”老康边说边去瞧墨涵,她咬着唇沉思着,眉头紧皱。他才慢慢将围场的情形说与她听,着力形容胤礽的暴虐,说到末了,竟又老泪纵横,终究不忍:“你代朕去瞧瞧他!”
墨涵犹豫再三,不知仁孝皇后留给她的话几时可说,她原预备到了布尔哈苏台,史书上所说的一废太子处,可此时见老康动了真情,想来父子血缘非一刀可断,正是趁热打铁的良机。她上前一步,跪至龙椅前,正式的三拜九叩,无视老康惊讶的目光,缓缓道:“儿臣于那四年昏睡中,时常听闻有女子声音对儿臣说起宫中旧事,并说是儿臣的长辈。之后儿臣痊愈,亦时常于梦中听闻其声。儿臣心中惶恐不已,那女子却言,只要与皇阿玛说一句话,皇阿玛自然会告诉儿臣她是何人。”她慎重其事,坦诚的看着老康,她的话本来半真半假,又于五月至今反复演练,句句经得起推敲却又不露着意预备的痕迹。
“哪句话?”他倒不信这些事,子不语怪、力、乱、神。
“她请儿臣问皇阿玛是否还记得对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凌波不过横溏路,但目送,芳尘去。’”墨涵盯紧老康,不放过他任何一个神情,一丝细微流逝的痕迹或许都是胤礽生的希望,胤衸不死,其他生的人呢?
老康已踉跄着过来拉墨涵起身,惊恐万分,却又无限期盼,颤声问:“她还说什么,可有什么是托你带给朕的?她、她可好?她为什么不来看朕,为什么不给朕托梦?她是怨朕没管好保成么?”他一连串的问话并不急于要墨涵回答,一旦说完,就好似耗尽他所有的心,他迈着缓缓的步子踱回案前,双手按住书案支撑身体,却忽然发狂般一头嗆木,大声悲号起来。
他这样的反应实在让墨涵大感意外,她原没有十成把握能凭这样简单一句话取信于老康,只是仁孝留函中一再嘱咐,她才冒险以此入题。可如今展现在她眼前的哪里还是那个万能的圣君,只是个痛失爱妻的普通男子,却原来纵有三千粉黛,心中深埋的依旧是结发亡妻。
值守太监在门外不知出了何事,闻得哭声竟擅闯了进来。墨涵立刻察觉老康的怒容,抢先道:“李德全,把这个奴才拉住去赏三十板子!”
老康止住悲声,倒不讶异她的举动,只问:“你当真不知她是谁?”
“儿臣本来只有七成猜想,如今见皇阿玛情真意切,儿臣自然明白了。”墨涵的话有一半是真的,她的确被他的动情吓了一跳。
老康默默的从贴身的衣服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独自沉浸在思绪中,借着那亲手描绘的小像慢慢缅怀逝去的情怀,旁若无人的摩挲着早已失了芳魂的一缕青丝。
他忽然往外急行,却顿住脚步,道:“随朕去瞧瞧胤礽,把弘皙也宣来吧!这些话以后再说,莫对人提起!”
“儿臣明白!”墨涵真希望什么都不知晓,什么都不曾谋划,何不做个笨女人?
天色已黄昏,墨涵总算摆脱老康祖孙与胤礽的团聚,却哪里还见得到胤祥。她急急赶回大帐见胤禩,时间愈久,她对他是愈发难以割舍,哪怕片刻的分离都难抑相思。
“格格!”帐中只有竹心。
“贝勒爷呢?”
“奴才也不知道。爷说请格格早些安置,莫等他。”
墨涵实在疲惫,让他端了热水入内帐,自行梳洗,换下的**却有点点猩红,心中已是一片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