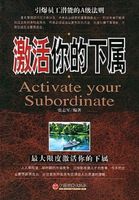转自《女子无殇》贴吧
看到留言,有续写的亲,大部分说米结局写的潦草,米留言解释过一次,结果留言莫名其妙的消失,先稍微解释一下
结局截然而止,首先是以为昊殇太炮灰忒惨了点,米不忍心写下去虐他了
其次,有些东西没必要写的太明显,比如洛施的结局,写不写都无关主线,米说过浞飏有多爱泫汶,萧楼对皇权就多执着,所以怪不得他,而以浞飏的性格,洛施死活都不重要了。
米本来在群里吼了一声,想写个番外来着,无奈就3个人响应米,着实把米的积极性打消了,现在,周一之前,如果能出现100个不同id的亲顶楼,米就写个番外,类似女子结局时候后补的喜剧番外
如果不到,就当米没说
Now,Start!
米大概构思了一下,会以一个孩子的角度来写之后的浞飏和泫汶,以及其他人
至于停更的问题,米不想多少,3个月后发结局这事也不是米规定的
字数不够,新文的楔子充个数
离开边城的那一日,身旁的人豪言壮志,要与我携手共展天下。其实他不知道,我要的并不是臣民叩拜,不是荣华富贵,而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一别多年,我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重回边城。
新皇登基三年,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年景是一年好过一年,边城的通商往来也是蒸蒸日上。
太平盛世,外敌不侵,百姓安居乐业,曾是那人心中的抱负。
我带着斗笠,黑纱长垂遮了面容,一身粗布青衣,怀里抱着圆滚滚的孩童。
毛毛在我怀里不安分的瞪着眼睛四处张望,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时不时的往我怀里蹭,小手抓着我的衣襟嚷,“娘,毛毛要那个。”
我一直觉得对不住这孩子,从落户我肚子的那天起,就是历经磨难,险些就重回了轮回路。好不容易出了肚子来到人世,便是跟着他这不成器的娘亲,东躲西藏,风餐露宿的过日子。
所以,但凡他不太过分的要求,我基本上都满足他。毛毛捧着拨浪鼓手里捏着小糖人,一会摇摇鼓一会舔舔糖人,自娱自乐的十分满足。
我看着他的笑容心头一酸。
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要了一间二楼的房间,吩咐小二哥送来了热水。
毛毛憋着嘴可怜巴巴的看着我,十分的不情愿。我冷了脸色,冲他挥挥手,“过来洗澡。”
洗完澡,毛毛脸色红润的睡下。我带上斗笠,关上房门在门上下了软骨散之后,匆匆走出客栈。
两年了,我从来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三个月,不敢在人前露出容貌,不敢去接触和过去有关的人,不敢……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若说这天地之间还有容得了我长久容身的地方,便是匈奴了。
纵然匈奴民风彪悍,纵然匈奴话饶舌难学,纵然匈奴万里隔壁黄沙滚滚,水资源稀缺,但是为了毛毛能够有个安稳的家,匈奴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
买了马匹和干粮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买了《三字经》、《论语》等比较易学的书,匈奴在文化方面发展甚是滞后,待毛毛识字之后还是要教他国学的。
路过钱庄的时候,恰好看到两名青衣男子下马,走进钱庄。虽然是身着平民百姓服饰,随身未带刀剑,但是单那一个下马的动作,我已经瞧出了不寻常。
我知道他一直在找我,各州各县贴满了寻我的告示,受日晒风吹却从未更改过,旧了字不清楚了,便会有人换上新的。赏金更是越加越大,到了平常百姓瞠目结舌,赞叹国库丰腴的地步。有一日,毛毛见了那画像,嚷道:“娘,那画的不是你吗?”
幸好那时候他还小,正在呀呀学语的时候,旁人听不大懂他说的是什么。
告示上的画像确实与我有九成九的相像,他少时才高,丹青出众,一只狼毫便能妙笔生花。只是不想他千金难求,从不示于人前的画作,居然千千万万张的张贴在神州各处,被市井之民随意的看上几眼。砸着嘴议论上几句,“宫里的娘娘这容貌也不顶尖呀。”
“听说是私逃出宫的,龙颜震怒,朝堂内外都放出话来,翻天覆地都得找到这位主子。”
这两年来,饶是日子再清贫,毛毛嚷着要吃肉的时候,我都不敢去钱庄提钱,李兴旺给我的印记能够在天下任何的钱庄支取现银,我自是知道,他又何尝不知道呢。
而刚才走进钱庄的百姓打扮的两名官差,是不是来寻我的。两年的东躲西藏,我不敢确定他们是不是他的亲卫军的人。
如今的我,犹如惊弓之鸟,已经冒不得一丝的险,加快了脚步赶回客栈,想着接了毛毛立刻启程,边城的确不是我久留之地。
客栈里并无异常,穿过厅堂,进了后院,院子里种了棵白杨树,百年的老木树干粗壮,枝叶茂盛,树下一片荫凉。白杨不似竹子娇贵,养于南方方能成活。便是那黄沙戈壁,白杨树也能够迎狂风黄沙,屹然而立。当年与匈奴和亲的宋家将军死于边城,引发了双发紧张的对吃,我曾混迹于军队中在那茫茫戈壁上,见过那一排排坚毅的白杨树,一路望不到尽头,与天际线相接了去。
此时,白杨树下站立着一个黑衣公子,那身形与记忆中的人太过相似,让我心头一紧。只是黑衣公子瘦削了许多,不似那个人的挺拔张扬。
想着毛毛这会应该睡醒了找娘亲了,抬步就往楼上走。
那黑衣公子却突然转过身来,将我深深一望。
这一眼,隔了近两年的时光悠悠,隔了痴缠的爱恨情仇,隔了夺子之恨,杀妻之仇,将我们不堪回首的往事望了出来。
他的眉眼之间千山万水,曾经灿若星辰的一双黑眸,竟是沉黯无光,失了生气一般衬得整个人越发的阴郁。
虽然心里明白他若是诚心寻我,即便我三个月一换住所,他也是能找到我的,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我却从来不曾做好过再见他的准备。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跑,以我的轻功,他若是没有在周围埋伏人手,还是有脱身的可能的。往西百里便是广袤的戈壁沙漠,穿过沙漠就是匈奴的王庭,离了他的势力范围或许真的可以此生再不相逢。
我本就打算去匈奴的,可是他本就善于攻心,对我更是了若指掌。如果当初我出逃之时便直奔匈奴而去,怕是路上便会被他的人拦截。所以这两年来,我将神州版图绕了大半圈,为的就是摆脱他的追踪,从边城入匈奴。却不想,仍是功亏一篑。
说到底,论起谋略,我始终输他一筹。
然而,毛毛仍睡在二楼的房间里,我要是逃了出去,毛毛定会落入他的手里,天大地大我便是再也逃不出去。
于是,我双膝一弯,俯身跪拜,行的是端端正正的宫廷礼仪。想起当年,教我礼仪的陈嬷嬷甚是严厉,柳木做的三尺手板,毫不留情的抽在我身上。在外面野了这么多年,虽说大伤小伤受过不少,然而有齐叔在这样的委屈我不曾受过。然而,当时全凭着对他的爱,咬着牙忍了过来。不曾想,物是人非之后,当日学的礼仪倒是还有用得上的一日。
我对着那青石板的地面重重的磕了个头,“参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话音未落,便见一双黑色衮金边的上等马靴落在了眼前,一只大手拽着我的胳膊,狠狠的拉起我与他对视。
我望进他的黑眸中,犹记得初见时他抬头对我微微一笑,一双晶亮的黑色眼眸里透着桀骜之气,那一份张狂掩住了他皇家之子的威仪之态,反透出丝丝凉意来。而如今,仍是这双眼睛,失了年少的轻狂肆意,掩不住的尽是一代君王睥睨天下的滔滔气势。
我皱着眉别过头,不愿意再看他。
他手死死的捏着我的胳膊,捏的我骨头生生的疼。他咬牙切齿的说:“你比我狠。”
两年的时间未曾说过话,头一句他说的便是这个,我忍不住想笑,想对着苍天大地笑一回荒唐,想对着红鸾凤烛笑一声冤枉。然而,我没有,我只是异常冷静的说:“承让。”
他定是气极了,全身都在微微的颤抖,连带着我也跟着他抖了一抖。
“成月落,你……”
他掐着我的胳膊,指着我鼻子,一个你字说了半天,却再说不出下文来了。
我心里惦记着毛毛,怕被他发现了,便真是逃不了了。
冷着声音只想尽快摆脱他,“陛下已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成月落这里再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还请陛下发发慈悲,放……”
我话没有说完,便被他一巴掌大力的扇了出去,跌倒在青石地上。
胳膊应该是磕破了,细微的疼痛,脸上火辣辣的疼,嘴角缓缓渗出血来。
他死死的盯着我,眼中的恨意缠得混沌,似天地洪荒万物未生,暗黑色的风浪汹涌而起,卷得天地为之失色。他声音暗哑,说得艰难,“成月落,你凭什么让朕放手,朕永远都不会……”
他没有说完,只因一声孩童的啼哭横空而出,生生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心迅速的沉了下去,只觉得绝望,死灰一般的绝望。命运与我开的玩笑,着实太过玩笑了。
毛毛穿着大红色的小马褂,脸上还有几分睡意,浑圆的脸上挂着眼泪和鼻涕,正站在二楼的楼梯口怯生生的看着楼梯不敢下来。
那人本是极为不耐的循声望去,这一望便怔住了。我自是知道为何。毛毛现在虽说是个粉嫩的滴出水来的孩童,看不出什么美丑,但只那一双眼睛,却是像足了眼前的人,黑色的光芒凌饶,说不出的风流神韵。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长了一双这样的眼睛,着实有点过了。
我现下的模样定是狼狈极了,毛毛因为先天不足,又是早产,身子弱不说胆子也很小,眼下竟然顾不得怕那高高的楼梯,咬着牙就要冲了下来。
我已经顾不得许多,急忙大叫:“毛毛,待着别动。”挣扎起来就要过去接住他,却有人先我一步蹿了过去,黑色的衣角在我眼前一闪,毛毛稳稳的被他抱入怀里。
气氛一瞬间有些诡异的安静,毛毛瞪大了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抱着他的人,拧起了秀气的眉毛,一口咬在那人的手臂上,他牙齿都还没长全咬人根本不疼,那人当年羽箭穿透胸膛也是一声不吭,此番却娇气的紧,眉头紧蹙,薄唇紧抿,表情颇为受伤的盯着毛毛。
毛毛颇有几分霸气的回瞪他,“让你欺负我娘。”
那人的身子一震,扭头来看我,那眼神复杂而深刻,嘴张了几张,勉强发出声音拼凑出几个字来,“月落,他……他叫**?”
所有的不情愿都赶在了今日一起来凑热闹,争前恐后,就怕上不得台面见不到正主,确实热闹的紧。
被他这一问,往事悠悠又溢出了几分,我想起了边城初见时他一身裘衣翩翩佳公子落难的模样,想起了落日余晖下他身着墨绿色捕快公服的落拓模样,想起了千军万马前他黑衣铠甲豪气干云的模样,想起了九重宫闱中他黄袍加身,受命天下的英武模样。
这一路走来,我看着他从边城走到帝都,从被动挨打走到运筹帷幄,从皇子走到君王,他走得是风生水起,终是得偿所愿。我却是走得一身伤痕,满心疲惫,满目狼藉,再也不想再与他纠缠下去了。
相识多年,我头一次向他服软,“秦昭,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