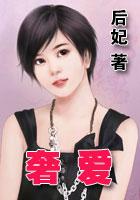“区区十三万兵马就想攻入王城,贼侯痴心妄想!”
……
“逆子忒也狡诈,用诡计攻破梁城,但他不要开心太早,覃城的北卫军会用手中的铁弩把他射成筛子!”
……
“不亏是吾国第一神将,横侯大破北卫军、前卫军,惊弦七英折了三人。”
……
“虎贲铁骑踏至王城脚下,禁军统领开门投诚,王城即将迎来他的新主人!”
……
“新王入主王宫,天降祥瑞,央国幸甚,万民幸甚,天下幸甚!”
……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
……
军士鱼贯而入,他们手中的火把将幽暗的大殿照得明亮起来。
冉天横背着手,抬首信步,打量着这座瑰丽的殿堂,好似是在打量着一位老朋友,久违了的感觉。
官员陆续被押送至殿前,不多时,便聚了百十来号,他们都是朝堂的命官,每一个都位高权重,但此时却官服不整,一个个垂头丧气——他们是在被窝里被拽走的。
当然他们也惊慌,但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不知道接下来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
一朝新王,一朝臣,即便不知道,倒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更何况今时这位新王,是个狠角色,是喜欢要人命的。
冉天横走下殿,在低头侍立的官员面前挨个走过,不时还帮某位整理一下衣襟,扥一扥衣摆。
受助者害怕得僵直了身子,连称“不敢当”。
“大半夜的,孤将你们叫醒,真是对不住你们啊。”
“不敢当,不敢当。”
“大殿阴冷,孤没有为你们摆些炭火,真是对不住你们啊。”
“不敢当,不敢当。”
“这几十日里,孤沿途而来,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真是对不住你们啊。”
“不敢当,不敢当。”
“你们辛苦了!”
“不敢当,不敢当。”
“来人,拉出去,都给我斩了!”
“不敢……”
官员们大惊,登时面如土色,就算心中有所准备,孰料还就真的发生了。
这位王真要命啊!
“侯爷我等可是王庭命官,您怎么……咯咯……”一位官员刚申辩了半句,便毫无征兆的突然喉咙一紧,一口血吐死当下。
噗通一声,几乎与那位官员倒地的声音同时,有一位官员跪了下去,五体投地。
“臣罪该万死,大王您一路颠簸,臣未能及时迎驾,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些许之后,这位跪下的官员喉咙还好好的。
不过,冉天横并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背着身子,舒扭着脖子。
官员眼珠快速转了一下,急忙接着说道:“臣不仅未能及时迎驾,还衣冠不整,有失体统,还唐突王驾,忘了尊卑,没有及时行礼……臣……是吃了猪油蒙了心!未能体会上意,何止罪该万死,简直永世不得超生!”
这时冉天横转过了身,目露一丝满意,说道:“廷杖一百,孤念你能知错认错,姑且饶你一命,拖下去!”
“臣谢恩!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是指路的明灯啊!”多少人心中唏嘘,“廷杖一百虽然疼了点,但命保住了呀!”立刻有模学模有样学样,纷纷跪倒在地,一时间大殿内尽是悔罪之声回荡。
果然,在明灯的指引下,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凡是拜倒在这位新王脚下的,新王都放过了。
冉天横很满意,但却不够满足,因为此刻殿前还站着一些官员,他们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表示,似乎也不想有任何行动,不想有任何表示。
明灯指路你不走,无亚于地狱无门你非要闯进去。
“哼!”冉天横用鼻息表示了最后的机会,军士身上已经散发出了杀气。
这时,站在最前的那位官员说话了。
“今王和王孙……如何了?”
冉天横虽然不爽,但发现这位官员还有点良心,有一点忠心,知道惦念他的旧主。
他仔细看了看那位官员,看官服认出来应该是尹士院的那位新太尹许守一,他新官上任不久,与他未曾打过多少交道,怪不得自己对他不熟。
尹士院助理朝政,太尹是尹士院之首,自然也就是朝官之首。
冉天横没想到这位不起眼的官员就是那位新晋天才,一位十八岁时成为了自在天,到如今也只不过才二十六岁。
“前夜他竟然没有对我动手……”
前夜里,当冉天横闯入王宫的那一刻,便遭到三百多位自在天的伏击,其中就有十几位尹士院的尹士。
他以为王城所有的自在天都参与了这次行动,没想到这位天才却躲在家里睡大觉。
颇感意外之时,他随即想起,阅过的密报里曾提起新太尹的性格十分固执,是个认死理的家伙。
“那他认的什么理?”
冉天横怎么也不会想到,许守一一开始也在行动计划之中,并且也答应了出手,只是他扬言冉天横一定会成功杀进王宫,任何阻拦都是徒劳的,且平白造成无谓的杀戮。
于是因言获罪,被先王责令在家面壁思过。
但无论怎样,冉天横此刻对他有了那么一丁点欣赏。
“王孙刺杀了先王,畏罪潜逃!”冉天横说出了真相,但他知道和说假相是一样的,没人会相信,即便眼前这位是个天才。
王孙是储君,怎么会刺杀先王?没有道理!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你骗人!”接着许守一愤怒的说出那些没有道理。
冉天横漠然的看着他,说道:“亏你身为太尹,却连这其中的弯弯绕都看不明白,王孙自然是要赶在孤赶来之前坐实了名分,在礼法上占得先机。”
“他本就有名有份,礼法占先,又何必画蛇添足?!”
“迂腐!和你说不明白,来人,拖下去廷杖八百!”
冉天横起了惜才之心,对方是个青年天才,性格虽顽执,但却也耿直,他欣赏耿直之人,否则若换做别人,早身首异处了。
但许守一不仅没有领会,反而更加愤怒起来,因为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他最为认可,也最相信的那一种。
“你杀了央王,还杀了王孙,弑父杀侄,如此禽兽行径,天理不容!怎能将王位交由你这般凶残之人手中?!”
前夜没有出手的许守一,此时却突然出手。
前来羁押他的军士并非易于之辈,但许守一抬手间就将他们屏退了三丈之远。
“想死?!”冉天横的脸瞬间阴云密布,一只大手抬了起来。
许守一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当今央国第一神将,亦知道自己毕竟年轻,就算自己也同为自在天,但积蕴自是无法与自在天成二百年,沙场驰骋千万回的第一神将可比。
于是他使出了最强的手段。
他一跃而起,左臂横出,如若羽翅,右臂竖起,形同利刃,在式成的刹那,一只羽鹤从九霄落下,水击三千,一柄长锋从九幽斩出,月落两畔。
两瓣罡风在身畔爆出,许守一好似攻城的石丸,顶着一道无坚不摧的寒锋,砸向了冉天横。
“江分两月,很好!”
分的不是月,是江水,江水上没有两月,是剑气,一剑江水断,月影分!
这仅仅是虚式,镜中花,水中月,自然是虚式,而实招是真的花,真的月。
就在二人接触的一瞬,寒锋之后竟又出现了一道月轮,月轮之盛,一切抵抗在它面前都是浮云。
许守一以身成锋,以身化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将最强最锋锐的剑气摧运而出。
这道剑气劈了下去,劈在了冉天横身上……
……至少,许守一是这样认为的。
而很快出现的结果,却让许守一的心凉成了三截。
冉天横仅仅是抬起了一只手,轻轻一捏,便捏断了那道许守一用尽浑身解数,使尽浑身力气打出的一招。
许守一落在地上,不能自已的跪了下去。
殿前的人们都惊呆了,官员也好,军士也罢,他们惊呆于这位太尹真是个呆子!
冉天横胜券已握,大势已成,这种情形之下,还敢对他动手?还有什么必要呢?是不是傻?
冉天横也觉得很可惜,觉得这位天才太尹在某些方面却是个傻子。
本来可以生,他却选择死。
就算有心留他,此刻百官众目睽睽之下,也是留不得了。
否则威信何在?!
冉天横抬起的手伸了出去……
忽然,好似有一道光晃动了一下,就有一个人从夜幕中走到了殿前。
他面若冠玉,却须发洁白,走到冉天横身前,举手微微作礼。
“恭喜新央王继位!可否看在老夫的面子,饶小徒一命?”
来人并没有说自己是谁,但冉天横却很清楚他是谁。他就是快哉山的左长老,鸣鹤三羽的白羽——陆曲。
快哉山的浩然剑宗是央国境内的一大势力,山在东境,但弟子满天下。
按说国境之内所有的势力都应属于央王,不属于的就不应存在。但快哉山之所以既不属于又能存在,是因为它从来都无意于政权,它只在乎快意江湖,从来都不问国政,只问恩仇。
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很强大,强大到堪比一国之力。
所以,即便强横如冉天横,也不得不考虑这个老头的请求。
但,很可惜,今夜是立威之夜,任何人,哪怕他是天府的大祭司,是魔国的魔王,是鸣鹤三羽,亦或是鸣鹤本人,亦或者是另外那些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无量极,都不得阻挡新王的决意。
王之所以为王,就是说一不二。
这一夜,或许就如许守一曾推定的那样,终究是一个无可改变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