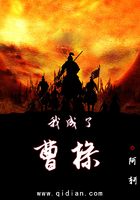且说,燕风推测惠广大势已去,思忖着后路。“碧眼金毛伽蓝镇中州”、“中剑”惠广竭尽全力,想要速战速决,痛下杀招,一剑使出三五招,双剑就是十来招,一道道剑光冷艳婆娑,寒森森如排山倒海。燕云顿感吃力,舞剑匆忙封迎躲闪,还是躲闪不及黑色英雄氅被他的剑削去一片,左肩膀头子也被划伤。惠广哪给他喘气的机会,急速使出看家路数“惊涛怒浪”,一剑奔他脖颈,一剑奔他前心,势如奔马快似闪电。燕云若想化解开不死即伤。惠广耗尽全部功力,这若招一击不中,离死就不远了。
燕风早想为燕云助战,只是等待燕云危机之时。见燕云危若朝露,运起不足的内径,疾步上前推开燕云,举起金蛇剑挡开惠广上一路的剑,说时迟那时快,眼看惠广奔前心的剑就到,仓猝偏身疾闪,“刺啦”前胸被惠广的剑划开一尺长两寸深的血口子。
燕云一阵惊恐,要不是燕风及时出手,自己离死不远了。这是他没想到的。燕风铤而走险,虽然受了伤,但他觉得值得
惠广用力过猛,收脚不住跌倒在地。爬起来,弱而示强,骂道:“燕风又是一个恩将仇报的畜生,要不是贫僧救你,你早就死在妙音殿了!两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来来,贫僧送你们再度轮回。”
燕风对燕云,道:“哥,休听他大话吓人,秃驴惠广现已是强弩之末了,来咱哥两一起剁了他的驴头。”
燕云看着鲜血直流的燕风,不知什么感觉,燕风其罪当死,现下又是他救了自己,还要与自己联手铲除罪魁妖僧惠广。眼下的形势容不得多加思索,抖擞精神,要与燕风双战惠广。
燕氏兄弟挺剑来战惠广。倏地“嗖”的一声从路边绝壁树林中一道光射入惠广的哽嗓咽喉。惠广大叫“啊”用力拔出咽喉的暗器,凝视着“花——花——”绝气倒地身亡。
燕云、燕风极速将目光投向绝壁树林,树梢微微摇晃,一点点、一点点极快消失在远方。二人寻思,那发射暗器之人武艺轻功绝对是一流中的一流。燕云从惠广手中拔出暗器在惠广身上擦了擦,一看原来是一支青竹簪子,揣入怀中。燕风见惠广身亡,心中暗喜,心想自己与惠广做下那万恶不赦之事再无人知晓;陪着笑脸,道:“哥!打虎亲兄弟,论起行侠仗义还得咱兄弟!“碧眼金毛伽蓝镇中州”、“中剑”惠广当初何等的不可一世,什么‘云里天尊’、‘吕洞宾’在江湖武林是何等响当当的名号,却伤不得惠广毫毛,结果还不是被咱哥俩给做了。”拱手“哥!咱们后会有期。”说罢要走。
燕云冷冷看着他,道:“燕风你还想走!”
燕风故作镇静,道:“哥!你在说疯话,兄弟不走,在这给秃驴惠广守灵不成?”
燕云道:“废话少说!你罪恶累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我要拿你见官。”
燕风故作惊讶,道:“拿我见官!你真是疯了,难道你这亲兄弟在你心中就是十恶不赦之徒,我无恶不作?西京十阎王穷凶极恶欺压良善嗜杀成性,西京白天街市无人如同鬼城,请问上至西京府乃至京都大大小小官吏,哪个敢管?下至江湖武林侠道的武天真、苗彦俊等等,哪个敢碰?他们惧怕十阎王的老子权势,怕惹火烧身、怕丢脑袋,我!我燕风不怕,十阎王我就棒杀了九个,一个时辰不到杀了十阎王的狗奴才八百八,是我燕风还西京百姓一方清平!请问有我燕风这样置生死度外剪恶除奸的十恶不赦之徒吗?”慷慨激昂,指天画地。
燕云一下被他说蒙了,冷静片刻,道:“不错,你是做了些善事,但这些就能将功废过吗?”
燕风道:“好好,咱们不谈那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们是亲兄弟,你知道血浓于水吗?你就甘心把你这一母同胞的兄弟送上断头台?我可不只一回救过你的命,远的不说,十几天前在长寿寺客堂前,若不是我在惠广面前为你求情,你就被惠广贼徒给撕碎了!你不是常说‘狗有湿草之恩马有垂缰之意’吗?今天怎么连狗马不如呢?”
燕云顿感羞愧,但并不糊涂,道:“既然你闭口不言公,咱们就谈谈私。七姑是咱的长辈,是咱武艺启蒙的师父,你——畜生不如的东西,怎么就下得了毒手!”
燕风道:“哥!兄弟我都是被妖僧惠广蛊惑,他暗里给我服下‘双石散’,使得我神思癫狂、心神错乱,不能自已,究竟自己做了什么,恍恍惚惚记不得了。哥,这笔账记在我的头上,公平吗!公道吗?”
燕云的江湖阅历也不少,对他所言的“双石散”有所耳闻,用量多的人精神亢奋癫狂,犹如狂醉之人,做下一些平常做不得的事情。惠广一死,死无对证。燕云也不会轻信,道:“说得好,你叫惠广开口为你作证吗?”
燕风道:“哥你咋就是不信呢?我对天发誓,不,对咱九泉之下的爹发誓:燕风如有半句假话,就被乱狼撕了!”
燕云道:“燕风畜生!你也有脸再提九泉之下的爹。你置杀父仇人靳铧绒于不顾,贪图富贵为贼为父,就凭这,我就能一剑把你给宰了。”
燕云嚎啕大哭,连喊“冤枉!冤枉!”
燕云喝道:“行了!别演戏了!”
燕风一脸冤枉,一把鼻涕一把泪擦着,道:“哥你、武天真、苗五叔、南衙,你们都把我看成与妖僧惠广是蛇鼠一窝一丘之貉,惠广众所周知神通极大,白道黑道人脉极广,朝中不少要员都是他的座上客,更兼有高深莫测邪魔武功,要想擒杀他比登天还难,愚弟我忍辱负重遭人唾骂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他交往,默默等待良机为民除害,今日终于如愿以偿。”咬牙切齿道“杀父仇人靳铧绒,我恨不得吃他肉喝他的血!凭我的武艺取他项上人头不难,可他是朝廷命官,咱们是平头小老百姓,打小爹娘教咱们遵守律法,不越雷池一步,咱们只能依照官法行事。我含垢忍辱、包羞忍耻、卑躬屈膝认贼作父,不就是暗察他罪证;岂不闻要离为了吴国安宁,断臂杀妻取得庆忌信任,最终刺杀庆忌。要离为国为民忍辱负重,何其壮哉!靳铧绒是什么人,刁滑奸诈无恶不作,要想与他交厚,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他那样的人。有朝一日将他的罪证暗查齐了,就击登闻鼓告御状,将靳铧绒绳之于法,一为爹报仇、二为国锄奸,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中不愧于祖宗牌位。哥,您是我的亲兄弟,今天不是逼到这份上,兄弟我不会给你讲这些,对别的人就更不会讲了;兄弟我如被老贼靳华绒察觉,我死事小,可前功尽弃了!”又是一番慷慨陈词。看着他将信将疑,道:“哥,我也知道目的虽然是好的,但以善随恶,不择手段,致使您不能理解,我也知道这样报仇,爹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心,兄弟我愧对于他老人家。所以在燕家庄外柳林坡为爹修建坟茔,碑文只留了‘子燕云泣立’,没敢留下自己的名字。”
燕云想起跟随赵光义征剿天狼山之后,和元达、马喑在柳林坡看到父亲规模气派的新坟,果然是燕风建造的,寻思:难道燕风真的为了报仇不择手段,这手段也太奸诈无人性,为了自己杀父之仇,杀仇人,把自己变成仇人一类的人,有多少无辜的人做代价。
燕风虽然侃侃而谈,但心急如焚,假如柳七娘等人杀到,自己休想活命;见犹豫不决的燕云,道:“燕云,你认为我这样报仇的手段不耻,是吧?好,你有种,你去手刃仇人靳铧绒。”
燕云一愣。
燕风道:“你怕是吧!你怕靳铧绒是朝廷命官,你怕惹火烧身,你怕毁了你的锦绣前程,你怕,就给我滚开!”起步要走。
燕云慢慢感觉他说的有一番道理,抢步挡住,不知该说啥,是为他送行,还是拦住他。
燕风道:“燕云你真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是吗?要做也行,让我看到靳铧绒人头落地,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推开他就走。
燕风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软硬兼施。把燕云说的时而清醒时而懵懂,惭愧至极,仔细品味他的每一句话,看着他背影,心想:但愿——不,燕风说的一定是真话。他坚信,世上哪有认杀父仇人为父的!
燕云割下妖僧惠广的人头,扯下惠广的僧袍把人头抱住扎紧。傻呆呆坐在地上,越想越愧疚,杀父之仇何时才报!若叫燕风知道自己不是燕伯正夫妇亲生之子,不知燕风会怎样奚落嘲讽自己;也许,不,肯定,今天自己放燕风一条生路是对的。两个人报仇,一明一暗,应该比一个人的希望、把握更大一些。主犯是惠广,走了燕风,南衙也不会太在意。
燕风撇下燕云,慌忙沿山路疾行,走了半里多路。突听,大喝一声“呔!燕风畜生纳命来!”燕风急忙看去:一人挡住去路,那人满头青丝,鹅蛋脸,丹凤眼喷射着怒火,粉腮红润,腰悬利剑,手持一枝荷花,花茎金丝软藤制作,长七尺,靠花盘三尺的花茎布满半寸长的倒须刺,花盘碗口大,花瓣由金银打制而成。燕风暗吸一口凉气,呀!“何仙姑”柳七娘,我命休矣!
“何仙姑”柳七娘紧握金丝软藤荷花如一条玉蟒,缠头裹脑奔燕风狂卷。燕风慌忙躲闪,持剑拆解。柳七娘一心要报仇,手舞金丝软藤荷花如片片雪花,铺天盖地朝燕风猛抽。若在以前,燕风二十几合完胜柳七娘不成问题,但现在可远远不是她的对手,七八个回合下来,浑身是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一招比一招慢。柳七娘瞅准时机,急速一招“西风卷地”“嗖”的奔他双腿而来。燕风躲闪不及,应声倒地。柳七娘疾步上前,一脚踢飞他手中金蛇金,“仓啷啷”抽出腰间利剑,抵住他的咽喉;道:“燕伯正大哥对不起您了!您的儿子燕风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他若不死不知有多少无辜良善死于其手,七妹一为民除害,二为燕家清理门户,给您送去了!”说吧持剑就刺。
燕风慌乱脖子一斜,命是暂时保住了,可脖子花开一道血口子,鲜血直流,哀嚎不绝“七姑饶命!七姑饶命!”柳七娘那容他分说,挥剑朝他脖子斩去。“铛”的一声一道寒光将柳七娘的剑隔开。柳七娘侧目看,原来是燕云手持青龙剑挡开了自己的利刃;道:“燕云你疯了!怎么还要救燕风这畜生?”
燕云道:“七姑住手。燕风也是受害之人,是妖僧惠广给他暗下‘双石散’,致使他变得亢奋狂暴神智错乱不能自已,才对七姑做下大逆不道的事情,七姑不能迁怒于燕风呀!”
柳七娘顿感燕云陌生,直愣愣瞅着他,道:“这是燕风给你说的?”
燕云道:“啊。”
柳七娘道:“你也信!”
燕云道:“要不他怎会变得六亲不认、残暴至极?”
柳七娘“呵呵”冷笑“那燕风认贼作父也是惠广给他下了药?”
燕云道:“那是燕风的苦肉计,效仿要离刺庆忌,暗查老贼靳华绒罪证,有朝一日击登闻鼓告御状,将靳铧绒送上断头台,为民除害,为父报仇。”
燕风大声道:“哥!你怎么心里就是存不住事儿?也好,既然纸里包不住火,已无秘密可言,老贼靳铧绒迟早会知道,我厚颜无耻苟延残喘,早已是不堪重负,忍够了,活够了!既然七姑不辨忠奸,就叫她来吧!正好叫我解脱,爹的仇,兄弟我只有来世再报。”
柳七娘狠狠瞪着燕风,道:“呸!燕风畜生好副伶牙俐齿,死到临头,还要花言巧语强词夺理。你以为燕云是三岁的孩子!”
燕云道:“七姑七姑,息怒息怒!您不要误会了,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
柳七娘没耐性给他分辩,怒道:“燕云你如认我这七姑,就给我闪开!”推开他,鼓剑奔燕风再次杀来。燕风筋疲力尽趴在地上,做出慷慨赴死的样子。燕云顾不得许多,急忙持剑挡开柳七娘的剑。柳七娘一顿狂舞,燕云左右遮挡,斗了三五回合。柳七娘道:“燕云!燕风这畜生怎么对待我的,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今天非要救这畜生,就先把我给宰了吧!”
燕云苦苦哀求道:“七姑七姑!您误会燕风了。”
柳七娘道:“燕云废话少说,没胆量杀我,就给我滚开!”
燕云挡住柳七娘,道:“七姑。燕云是他哥,如果燕风真的万恶不赦,燕云也难辞其咎,七姑!燕云情愿为弟弟受死。”
燕风声泪俱下,道:“哥,您不能死不能死呀!咱燕家的清白就指望你证明了。我是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一世是洗不白了,死了好,免得辱没了咱燕家清白。”转首对柳七娘“七姑来吧!侄儿燕风为报父仇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免不了涉及无辜之人受累,死有应得!只是死不瞑目,没有亲眼看到老贼靳铧绒人头落地。等我哥手刃老贼之时,靳铧绒人头落地之时,替侄儿燕风多看几眼,侄儿燕风这里拜托了!”拱手抱拳施礼。
柳七娘深感燕风说服力惊人,自己要手刃燕风,燕云怎可能会袖手旁观,不能再耗下去,想到这对燕云,道:“云儿,七姑是错怪你兄弟了。来咱们一起把你兄弟扶起来。”
燕云闻听心里高兴,寻思:七姑终于明白了燕风的一片苦心,这下燕风就不会死了。这一高兴,就放松了警惕。冷不防被柳七娘点住了穴位,动弹不得。
柳七娘提剑来到燕风身前,道:“燕风畜生,没想到你嘴皮子功夫绝不次于你拳脚功夫,燕云都被你说动了。可你七姑奶奶不是燕云,畜生拿命来!”奔燕风脖颈就砍。
燕云呼天抢地大叫不止“七姑!燕风冤枉冤枉!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柳七娘哪里管他,挥剑直取燕风脖颈。说时迟那时快。“铛”的一声火星四射,倏忽一柄落叶青锋剑挡开柳七娘手中的剑。震得柳七娘手腕一阵酸麻。柳七娘闪目观瞧,手持落叶青锋剑的人正是“吕洞宾”苗彦俊。
柳七娘柳眉倒竖,喝道:“苗彦俊!你也要救燕风这畜生?”
苗彦俊急道:“七妹!不是不是。这燕风事关重大。”
柳七娘道:“哦!你救这畜生,就拿‘事关重大’搪塞我!是不是!是不是!”
苗彦俊被逼无奈,道:“这燕风,是南衙严令要拿活的。”
柳七娘道:“你已经不端赵光义的碗,他的严令和你这平民百姓何干?”
苗彦俊支支吾吾,道:“不是——不是——”
柳七娘回忆着自苗彦俊等被赵光义逐出官府,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自感猜出八九分,道:“苗彦俊,当初赵光义将你等逐出官府,是遮人耳目,暗使你等与金枪会武天真联手除掉妖僧惠广,是不是?”
苗彦俊吞吞吐吐,道:“哦——哦。”
柳七娘伤心道:“你还是再为官府做事,苗彦俊好个读书人,真是滴水不漏,连我这与你出生入死的十几年的结义兄妹都要隐瞒。”
苗彦俊道:“七妹七妹。为剿灭锁龙山长寿寺妖僧惠广一伙,南衙用心良苦,南衙只将密令受给我,我哪敢将南衙密令外泄。”
柳七娘道:“别说了!燕风畜生是杀不得了?”
苗彦俊道:“燕风作恶多端多行不义,或杀或刮有南衙做主,燕风落到南衙手里绝不会有好下场。”
柳七娘一肚子气,不想叫苗彦俊为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道:“南衙会正法燕风吗?”
苗彦俊没有正面回答,道:“燕风畜生死有余辜!”
苗彦俊见柳七娘暂时收起了杀心,拿出绑绳把趴在地上的燕风捆个结结实实。
燕云闻听苗、柳二人对话,明白了苗彦俊暗奉南衙之命,联合被南衙驱逐的自己、元达、“瞑然”、“了然”等,在与武天真联手,共同剿除长寿寺一伙妖僧,南衙并没有把自己元达、“瞑然”、“了然”等真正驱逐。又喜又忧。被柳七娘点住的穴道有些时间,试着运起内功解开了穴道,道:“五叔!把燕风交给南衙,燕风还有命吗?”
柳七娘插话,道:“燕云你是被燕风畜生的‘豪言壮语’给糊弄了,还想着他不死!”
苗彦俊道:“这是怎么回事?”
柳七娘把刚才的经过叙述一番。苗彦俊恐怕夜长梦多,想早些拿燕风向赵光义交令,没精力再教导燕云,道:“燕风是死是活,南衙自有主张。”
燕云、柳七娘心都在悬着,一个想他活,一个想他死。谲诈多端的燕风,也是黔驴技穷,自感凶多吉少,面对苗彦俊、柳七娘饱经风霜的江湖老手,什么高谈雄辩都是徒劳的,只有听天由命吧。苗彦俊押着燕风,燕云、柳七娘随在身后,一行四人沿着“鼪愁径”山路迤逦而行。
当时,在西京府衙赵光义暗放“云里天尊”武天真,把罪责全都记在属下的头上,右巡军使苗彦俊、参军王显、“铁掌禅曾”瞑然、“瞻闻道客”了然道士、“飞燕”燕云、“双锏太保”元达、“铁拐梵客”达过,“双鹏、五鬼”“金毛鲲鹏”李重、“穿云抟鹏”杨炯、“催命鬼”崔阴鹏、“勾魂鬼”勾阴芳、“青面鬼”青阴刹、“无常鬼”吴阴钟、“白面鬼”(独臂鬼)白阴罗,被逐出府衙。赵光义暗里招来苗彦俊受以密令,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但招抚“黑煞天尊”张寿真在赵光义的计划之外,得到苗彦俊密报,随即将计就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