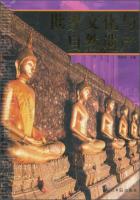经过繁琐、复杂的折叠后,把一张普普通通的白纸,变成美观的折纸工艺品,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简直就是在化腐朽为神奇,令我有些上瘾。
我折叠过很多种样式,不过并非每次都很顺利,预留的折痕比例、折痕的深浅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折出像样的东西出来,这需要具备一定经验才能提前做出正确预断。在折叠一架小提琴时,我反复尝试了数次,一直叠不出一个像样的成品,搞得我头脑烦闷,我放下手中的纸。讲台上数学老师正在讲一堆深奥的高数公式,我不想听,我怕我听后思绪会更烦闷,把高数课本直接撕毁,我便望向窗外,像往常一样,陷入彷徨状态,我也不清楚我具体在看些什么。
窗外的雪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三四天,没有风,安静的雪花下落的很认真,整整齐齐铺满了一切露天场所,洁白无瑕的景色绵延到视野尽头,外面的世界浑然成为一体。雪花集结成的积雪绵软厚实,给人一种寒冷的温暖感。
最终,我的目光锁定在一片簌簌飘落的雪花身上,一直顺着它飘落的轨迹注视着它。它似乎对我很感兴趣,借助空气浮力努力向窗户这边靠拢,越来越近,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这是我头一次如此专注的看一片雪花,我可以清晰地看见它突出的六个角,它并非简单的六角形,实际构造要很复杂,长有很多冰莹的突刺,突刺上又生突刺,很有规律,像那种色彩斑斓的毛毛虫长出的那种多刺的触角,不过雪花身上有六只“触角”,也许,这些是雪花感受世界的器官。
它异常精美,下落时像一个在空中旋转的舞者,仿若它真的会用自己的身体语言与周围的事物交流。它是如此坚韧,从万里高的天空一路舞到地面,毫发无损,与我相遇!它又是如此的微小柔弱,当越来越靠近我时,玻璃挡住了它的路径,很快化为水滴,消失在湿漉漉的玻璃上。
我忽然想起“恬小柔”这个名字,忽然想起那天撞见的那个女孩,如果她穿着当天的白色礼服,站在雪地中央拉小提琴,那一定美到无可挑剔,美到让我情难自已!就好像是宫崎骏的漫画里长大的女孩,忽然从漫画中蹦出来,来到人世间。
我突然很想再次遇见那个女孩,想拉住她问问那天为什么会把琴放心的交给我,她的答案不太重要,事实上这个问题本就毫无意义,那天也许仅仅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突发性建立起的一种信任,但我就是想问问,仅是想问问而已。
彷徨中,期待中,沉虑中,我仿佛都能看见一个女孩背着小提琴箱,双手插入上衣的口袋里,她把背影留给我,一个人在雪地里一深一浅独自行走,她的走姿轻松欢快,看来心情不错,不时抬头打量周围的环境,确定要走的路径……
我眨了眨干巴巴的眼睛,把思绪从彷徨中抽离,重新看了一眼窗外的世界——等等!刚才的画面并非出于我的幻想,雪地里真有一女孩,背着小提琴箱的一个女孩,在校园的雪地上快步漫行,我的天呐!
我的目光凝聚在她身上,越看越像她,但她始终未回头,所以我不确定是否真的是她。要真是她,我不知道是该兴奋还是该惊吓才对,我随便想想而已,她就忽然从天而降,她不会是妖怪变的吧!太不可思议了!
她还是不回头,哪怕给个侧脸也行,可偏偏没有,我恨不得从8楼教室跳下去追上她一探究竟,可我没有这么做,我会死掉。真气人,我以后见到岸本齐史时要拿把菜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说出“飞段”的忍术到底在哪学的,我也要学。我远远看着她越走越远,拐到一处教学楼后面,不见了。对真像的渴求像是一把撒进期待中的催化剂,把我的好奇心扩大了几十倍,不管她是否真的是她,我更加期待再一次与她相遇!
在这之后的几天、几个月里,我也时常坐在教室里望向窗外,甚至走在大街上,我都会留意那些带着乐器的人,不管是什么乐器,长笛也罢,小号也罢,反正都感觉这些乐器跟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天的那个背影,我有些失落,但也心存余温,因为说不定下一秒她就会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我心里一直这么想着……
如果她突然出现了,我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可能会不知所措,我可能会语无伦次,显得很失礼,那倒还不如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就静静的看着她好了。可我又不太甘心,那样她肯定会忘记我,就像每天遇见的无数个陌生人,我只是她遇见的所有陌生人中的一个,那也太凄惨了吧!我还是要努力说一些什么出来……我陷入深深的矛盾。
她就好像始终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中,我一直这样幻想有何意义,我不想深究,生活的意义本来就无法具体化,如果非要具体化,定一个具体的目标,那么当目标达成之后,接下来的生活将变得毫无意义,不是吗?
我不管想这些事情时是否在浪费时间,我只知道,我开始喜欢每周去教室里上那两节数学课,即使我看到黑板上密密麻麻的高数方程式仍旧感觉满眼昏花、脑浆骨折,快要七窍流血而死,我也愿意,说不定我探向窗外,恰巧再次看到她……
一想到这些,连我眼前的数学书都变得十分可爱!
很多时候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安静的我都以为自己是个哑巴,我不想说话,别人拿把撬棍也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偶尔站在一堆人里,为了不被人误以为我是空气,我多多少少也会在关键时刻说些关键话,不过这也得看心情。
我觉得我已经很不爱说话了,不过现在我眼前还有个比我更不爱说话的人,他是我目前为止见到过脱得最光的人,不仅衣服脱了,连全身的皮都给扒了,浑身上下露出鲜红的肌肉组织,肌肉纤维清晰可见,他就是我们生理实验室里泡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一具人体标本,通俗点说就是一个“死人”!
隔着玻璃,我离他不到10公分的距离,盯着他已经盯了快半小时,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这么长时间盯着一具扒了皮的尸体!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嘛?我一直在想:你可千万别说话,你要是敢对我说话,我立马昏死给你看!我对天发誓,我真不是闹着玩随便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