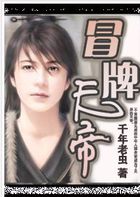“侯爷,您瞧这个。”莫枢东说着,就有人拎着一只退了毛正瑟瑟发抖的幼犬和一个酒坛进来。
见阮靖似有不解之意,莫枢东笑着解释道,“在下近日里想出了一个新菜式,这不赶紧来献给侯爷尝尝。”
安国侯阮靖静静地看着莫枢东青着眼眶指示下人动作,不自觉得笑了笑。
“这道醉骨香,先将选好的小犬活着去毛,然后刀砍其身上大小骨头,不要彻底砍断,在骨头上开个口子就好。再用细绳捆好了,免得它扑腾,泡在酒里入味,这期间可不能让这狗死了,否则这酒的味道就不能彻底进到骨子里。这小狗活着,血还流着,酒液才好顺着醉到骨子里。”莫枢东这边说得轻巧,那边的幼犬却是撕心裂肺地嚎叫着。
“然后再由无味楼的大厨……”
“大郎,你不觉得这般做法有些过于残忍吗?”阮靖话如此说,面上却是玩味多于不忍。
“牲畜罢了,生来就是给人吃的,不是吗?”
“可这声音着实令人心焦啊,大郎你就不怕吗。”阮靖仔细瞧着莫枢东,想瞧出什么来。
“那好办,割了它的舌就好。”莫枢东轻笑,扯到了嘴角的伤,一抖一抖的样子引得阮靖暗笑。
“呵,炮烙,车裂,凌迟,剥皮,抽肠,红绣鞋,从古至今这人对付人的法子可是要残忍多了,侯爷不说可怜可怜他们,怎么反倒怜惜上这牲畜了。侯爷,我说的可有理?”莫枢东说完就看向泡在酒里的哀嚎的幼犬,笑了起来,叫声愈惨,莫枢东笑得愈艳。
“你说的也是。”
莫枢东举起酒盅喝酒,听见那幼犬的哀嚎,握着酒盅的指尖不经意地抖了抖。抬头时正看到有人向自己的方向走来。
“你来做什么?”看见莫四的时候,莫大只觉似有雷劈了头顶,额上青筋直跳。
莫四也不理会莫大,径自走到与莫大同桌的那人身前,拱手行了个礼。
“在下莫权北,素来仰慕侯爷威名,今日有幸得以一见,此生无憾矣。”
莫权北抬头看那人,生得一副好相貌,说是清秀,眉目中却有几分英气,却又不显逼人,却由内至外散发着疏离之感。目似静湖,温柔又显深沉,半垂眸时睫扇微遮,就像漫天的星光皆映在了水里。发若泼墨,像是一副极好的水墨飞流披在肩上。这般样貌的人,就该立在春暖花开的地方,隔着雕栏,抬眸望向一江春水,感怀手中竹简上的诗词歌赋,任清风拂过发端,悠然闲适怡自得,羽化倏忽便成仙。百般磨炼不得改其本质,万千风云不敢扰其宁静。
可惜,从来人不可貌相。
“既已见过了,那你就回去吧,我与侯爷不需娇娘作陪。”莫四有貌羞百花之名,若生为女子便是倾国倾城,可生为男子多少显得有些女气,莫大这般说,话里就将莫四当做了女子。
“大郎说笑了,都传莫家四郎貌羞百花,今日一见果然惊艳,相由心生,想必四郎才德也似四郎相貌一般,可羞百花。”阮靖向莫权北还礼。
莫四也不管莫大的眼色,上前落座,与阮靖交谈。莫枢东面上再没说什么,外衫下的里衣已经全被冷汗浸湿。
所谓关心则乱。
再说唐宵,将树叶送给莫权北后就来寻老乞丐。
找了半日,在一棵古树的枝杈里找到猴一样蹲树上的老乞丐。唐宵怒了,自己刚刚在这棵树下走了有七八趟了,那个猴都没说叫住自己。
“嘿,那个猴,你蹲树上干嘛呢?怎么着,偷瞄哪家姑娘呢?”
老乞丐没想搭理他,可架不住某个奸商猴儿猴儿地叫起个没完,老乞丐烦躁,随手撸了一把树叶朝唐宵掷去,正好在唐宵的衣襟上开了个口子,这下唐宵是真的怒了。只见唐宵眯了眯眼,然后老乞丐就连同身下的树枝一起掉了下来。
老乞丐仍保持着刚刚的姿势蹲在同自己一起掉落下来的树杈上。
“今日我读了读前朝旧史,你说史书上的这些人,有多少遗臭万年是被冤枉的,又有多少流芳百世其实只是伪装得太好。”老乞丐两眼无神看向远方,像是看向好久之前。
“史书这种东西,列豪杰有功过,记奸佞唯劣迹,写小人只笑话,半真半假,何必计较呢?”
“你不曾被记在里面,你当然不计较了,真被记在史书里面的人,有哪一个不想只留下功劳,有哪一个想记下过错的,哪一个不想流芳百世,又有哪一个想遗臭万年的。”老乞丐回神看着唐宵,起了身。
“我记得你的名声可是不错啊,算得上山高水长了,前两天还听说书的讲你的故事呢。怎么?嫌他们夸得不够?”唐宵弯下腰,扭过身从下向上看老乞丐,笑眯了眼。
“惭愧啊,”老乞丐仰头喝一口酒,闷声道,“再过几日是他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