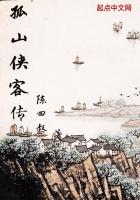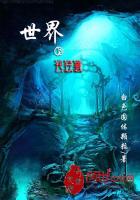上文说到,刘安安插在城中大宅中的守卫来报,那宅中又来了一伙形迹可疑的人马。这次这伙人牵马赶车好不嚣张,刘安听闻无名火气。天子脚下岂能让这伙贼人为所欲为?当即别过了马侍郎,请了兵符点了三四十个兵丁直往城中的大宅杀去。
不多时,刘安一行浩浩荡荡的杀到了这所宅子。一路上也顾不得被沿街的百姓看了,只管先拿了贼寇再说。这宅子外已有四五个兵丁把守,大门外有两三架马车,赶车的车夫一眼瞧过去也不像是作奸犯科之辈。刘安来不及细想,只管往大门里面走去。后面的兵马整整齐齐的跟着。在门口分了七八个兵丁往宅子四周查看把守去了。
来在了宅子中,只见一伙布衣百姓模样的人在一堆议论纷纷。四角有手持长枪的兵丁警备。那群人中,一个商客模样的肥胖老汉抓耳挠腮,不知所措。刘安见状心中已放了些心,只因这伙人全然不像是杀人放火的贼寇。只是眼下怎么跑到这是非之地来了?难道还不知这个中情形?
刘安上前喝道:“你们是哪里来的?怎么敢与贼寇同流?”
那肥胖的富商模样的老汉见状从人群中走出,弓着身子答道:“这位大人,小民是这宅子的户主,回这宅子只为收拾一番迁往外地。不知大人所说的贼寇是什么道理,难道我这宅子中出了什么事情不成?”
刘安稳了稳,说道:“这宅子果然是你的户主?怎么成了贼寇的巢穴?你难道全不知情?”
富商答道:“折杀小人了,这宅子的确是小人的户主,只是前年底小人去往外地做了些买卖,没什么人打理,后来差了我家中的长子打理,租给了一个城外的商人。这一年多小人也未曾回来。近日小人外地的买卖也有了起色,往后怕也少有机会再回这宅子,这才交与了钱庄的人打点,准备卖了房子,换些本钱。至于大人所说的什么贼寇,小人着实不知。”
刘安放下握刀的手,说道:“这么说,你这宅子租给了什么人,你也不知?全是你家长子的买卖?那你家中的长子如今何在?”
府上见惹出了祸事,怕是自家的长子也要受些牵连,赶忙说道:“大人息怒,我家孩儿年纪还小,结交的这宅子的租户也全不知那租户的来历。还请大人明察。若那租户真是贼人,又怎会告知我家孩儿实情?如今若惹下了什么祸害,小人愿代为受过。求大人不要责难于他。”
刘安铁着脸说道:“此事岂是你一个人能担当下来的。你且交出你家的公子,本官也不是什么以权谋私的赃官,只与他查问些口供而已。若你家公子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也不会难为于他。”
那富商面露难色,支支吾吾不知如何是好。刘安见他再没什么话说,便四下打量起这群人来。细看之下,这伙人果然如这富商所言,都是些平日里在寻常家中做些活路的人,不像是什么恶人。一个个苦巴巴的模样,有的人怯怯的拿眼角偷看刘安,有的垂下头不敢作声。看来都是些这富商府中的家丁答应。
只是在人群中,有两三个人侧着身子,最后一排像藏了个人一般。刘安有些好笑,说道:“后面所藏何人?是做贼心虚不成?还不出来!”
听了这话,那几个人更是像木头一般,身型僵硬,不敢动弹了。刘安向身旁的兵丁扬了下巴,那兵丁便与另外一个去拉那人群。那几个人被拉开,露出个身材矮小的男子来,只到一半人胸口高低。面目白皙,不像个日晒风吹的家丁模样。那两个兵丁拉了那矮子出来,带到了刘安跟前。刘安又打量了一番问道:“你便是这商户的长子吧?为何躲在人群中不敢出来?可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矮子诚惶诚恐支支吾吾的答道:“小人……小人未曾作奸犯科,只是见家中被……官兵包围……有些……胆怯……”
刘安两眼一瞪,喝道:“未作什么坏事你胆怯什么?还不从实招来!那租户到底是何人!”
那矮子吓得嘴唇也没了颜色,额头冒出冷汗,更不敢说话了。一旁的富商也急的满头大汗,手上搓着衣袖,像快被撕烂了一般。却又不敢插嘴,低着头憋着气,额头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刘安见这矮子分明有事不敢讲明,便差了身边的兵丁从屋中搬了个凳子出来,坐下来等这矮子富商两人答话。坐了下来,见还没答话,刘安有些恼了,沉着气说:“此事你若不说,到了兵部大牢就有好一顿打。本官先容你二人缓上一缓。若过了晌午还不肯说,你们就一同到大牢里和那刑具说去吧。”
那矮子腿软了七分,一把跪倒在地,磕头道:“大人别打,小人不敢隐瞒,着实说了便是……”
刘安往椅背上一靠,说道:“那便说,本官也不想牵扯无辜。”
那矮子抬起头说道:“这也是小人鬼迷了心窍,去贪那钱财。前年底小人受家父之命到城中寻那租户。不想一月有余也不见有人来租。只因这宅子着实大了些,没几个大家大户敢来租住。后来一个相熟的妓馆掌柜说有人来租,便与他约见,相谈租住之事。”
刘安笑道:“原来如此,再说。”
那矮子松了口气般再说道:“那妓馆的掌柜带了那租户过来,小人与他商量了租约钱财,便签了租约两相交接了。之后小人又来查看,不想这租户每次都不在宅中,只有一两个打点的下人在这宅中。”
刘安问道:“那租户的户主是什么长相?多少年纪?”
矮子答道:“是个三四十岁的精瘦汉子。衣着打扮也不起眼,只是一口气便付了两年的租金。当时小人有些纳闷,怎么如此大方,明明不像个大户人家的模样。后来拿了钱,有寻思可能是他们当家的官家,就没有过问了。”
刘安问道:“两年租金有多少钱财?”
矮子答道:“一千二百两白银……”
刘安皱眉说道:“出手如此阔绰,你这宅子也是租得划算。怪不得你也不问缘由。原来得了这般好处。”
矮子伏下身子,惊道:“小人着实不知此人是什么来路,只是与他做了这笔买卖而已。还望大人不要因他做下什么勾当牵连小人一家。”
刘安又问:“这些姑且不说,那妓馆的掌柜是什么来历?他是如何认识那租户的?”
矮子答道:“这个小人并不知情,只是看那掌柜的信誓旦旦,说是他一个相熟的好友便也没再细问。”
刘安道:“那掌柜是哪里的店家?眼下可在这城中?”
矮子似有为难,支吾了一晌答道:“日子久了,小人不敢确信他是否还在城中。只是那妓馆在城东街角,唤作‘春香阁’。大人可去那处查看。那掌柜姓方,年近五旬,一头灰发,倒也好认。”
刘安点头道:“既然如此,倒是算你立了一功。你且起来吧。”
那矮子战战兢兢的爬起身来,低着头不敢看向刘安,满脸的汗水再不敢作声。刘安倒是觉得这人虽然竹筒倒豆子一般说了个遍,但为何如此怯官,保不齐还有什么未曾交代。于是也不说放人,又四下打量了一番,站起身来。看了一圈,又问那矮子道:“你们一行几时进城?从哪个门进的城?”
那富商答道:“大人,我们清早进城,置办了车马才赶来这宅子。是从西门进的城。”
刘安又问:“你们来时可曾有什么可疑之人跟随?”
那富商又绷紧脸色,灰着脸答道:“未……未曾有什么人跟随我们……”
刘安四下又看了一看,沉默了片刻问道:“为何前几日后几日不来,偏偏在贼寇落网之后突然来城中收拾?可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
那富商吓了个半死,哭丧着脸要答,却说不出半个字来。他的大公子见状腿又软了半截,只差倒了下去。一旁的家丁搀扶之下,才没倒到地上。刘安着实的火起,大喝道:“还有何事你们有所隐瞒?难道不怕落个窝藏乱党的罪名不成?”
那矮子挣扎的站直了答道:“大人……不敢说是受人指使……小人一行怎么敢犯下这等天大的罪过。是上月底便有人来请,说不再续租。我父亲见常年留人在这边照应实在多出了许多开销,索性带了小人一起来收拾家产,寻买家卖屋。”
刘安听到又是上月的事,不觉有些惊讶,上月正是那伙贼人谋事之时。柳营儿,柳济子也是上月出了事故。想来这伙贼寇是打定主意要跑。劫了银两便要一走了之。想到这里,刘安又追问道:“那为何偏偏又是今日到了城中?前些日你们所在何处?”
那矮子答道:“前些日那租户只说还没搬走一些家用,不好交接。我们到城外寻了个驿站住了五六天。昨日那租户差了人来,说已经搬走,让我们一行到宅中收拾。”
刘安又问:“差来的人你可认识?什么样貌?”
矮子答道:“是个身高的瘦子。来的时候有些慌慌张张。只传了信便急匆匆的走了。”
刘安问:“是何时与你们联络?”
瘦子答:“是昨日戌时左右。来了便匆匆的走了。”
刘安一惊,心想戌时已是昨日拿了人到兵部之后了。今日便喊人到宅中收拾,难不成是为了试探?自己带人又来拿人岂不是中了圈套?现如今全城百姓都知道官兵到这宅中拿人,难道这四周还有贼人的探子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这正是巧留眼线唯恐漏网鱼,哪知早被算计差一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