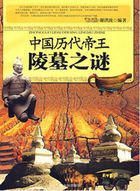郑员外的儿子乐呵呵地笑了笑,两只手一摊,然后说道:“那既然是他的一面之词,又怎能当证据呢!”
县太爷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场面,他原本想讨好陈智,为陈智主持这一回公道,可是,他这一回是立功心切,忽略了这个关键的问题,当下,向陈智看了看,见到陈智也无可奈何的样子,当下对陈智施了个为难的眼色,然后,思考了一下,说道:“嗯嗯嗯,是是是,如此看来,这也的确是他的一面之词,但整个事情前后发展像是你们父子俩预谋好的,哪有这么巧的,所以,在哪个彪形大汉没有落网之前,你们父子俩仍然逃脱不了嫌疑,本案还要接着往下审。”
郑员外父子俩听到这些话,知道这个县太爷也并没有完全偏向陈智一方,还是给他们讲理的机会,很是喜出望外,当下郑员外的儿子说道:“嗯,县老爷,您尽管查,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这个案子的真凶,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怕。”
县太爷一脸严肃地说道:“是不是,等审过了才知道,你现在说是没有用的,结果得我们接着审才能出来的。”
郑员外的儿子说道:“那好,那请您接着往下审吧。”
县太爷说道:“这个不用你说。”只见他对陈氏父子又笑了笑,说道:“小兄弟,不要怕,有本县在这,你有什么委屈自己说出来,本县替你做主,你们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证明他们父子俩在谋害你吗?”
陈父抢着说道:“昨天早上,发生那件事情后,我的儿子回到望湖酒楼后,因为心情激动,说不出话来,无法指证他们父子俩的恶行,当时我就不知道他们父子俩对我的儿子做了什么。因为不知道,我就把陈智安置在自己在酒楼的房间里,我出去叫酒楼的厨房做点压惊的东西,想给陈智吃点,压压惊,让他把早上出去所遭遇的事情说清楚。正当我下楼,为陈智准备压惊的东西时,我忽然感觉有点不对,于是,返回房间来。在返回房间的途中,我就听见陈智大喊一声,‘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知道陈智在房间里出事了,我立刻心急如焚,想快速回到房间里去,可是,郑员外找尽千般借口,就是不想让我快速回到房间里去,这时候,我越发地担心陈智在房间里又出了什么事情,进了房间,发现郑员外的儿子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的房间里来,他是没有跟我打过招呼,背着我,直接就进了我的房间,并且,他进了我的房间后,我回来就看见陈智在房间的窗户上,快要从窗户上掉下去,我来之后,把陈智从窗户上拉了下来,陈智从窗户上下来后,就指证郑员外的儿子在谋害他,先是早上在那个小巷子里,和那个彪形大汉一起抓住他;后是进了我的房间想要把陈智从窗户上推下去。县老爷,您说说,如果不是他们父子俩是这个案子的真凶的话,怎么前后会那么巧,像是安排好的一样。”
县太爷一边听着陈父的话,一边思考着,不久,就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但害怕又有什么没弄清楚,或这些供词会被郑员外父子俩又一次辩解掉,又会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地步,当下对郑员外父子俩说道:“那刚刚陈父所说的,你们作何解释啊!”
这时,郑员外的儿子双手向上扎开,磕了一个头,说道:“冤枉啊!县老爷,你且听我的解释。”
县太爷说道:“有话快说,本县可没有时间看你的表演。”
这时,郑员外的儿子从地上抬起头来,有条不紊地说道:“县老爷,您听我给您娓娓道来,是这样的,昨天早上,我们的确在那个小巷子里遇到一个来者不善的彪形大汉,遇到那个彪形大汉,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非常害怕,所以,都拔腿向回的地方跑了,陈智是最后一个回到望湖酒楼的,我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肯定的是他与这个彪形大汉进行了激烈的斗智斗勇,他虽然侥幸地从这场激烈的斗争中获胜了,可他当时也被吓坏了脑子,出现了短暂的意识不清醒,这一点你如果不信的话,您可以问一下与我一起来樊城的家长们。陈智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他父亲一起的反应,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说完这些话,郑员外的儿子还看了看其他的家长们。
县太爷听到这些话,立刻对其他在场作证的家长们问道:“你们在房间里有没有看到陈智言语或行为疯癫,有失常态啊!”
其他家长先后不一地说道:“是的,我们是看见陈智在昨天早上回来的时候,言语与行为疯癫。”
县太爷点了点头,有对陈父施了个为难的神色,接着指着郑员外的儿子,说道:“本县听你所说还有点道理,那你就继续说吧。”
郑员外的儿子见县太爷已经赞同他了,立刻喜形于色,说道:“是这样的,陈智回到房间以后,我想去看看他究竟怎么样了,所以,就去了他的房间,正好那时,陈父不在,接下来就发生您知道的这些事情了。您知道的,我去的时候,也正好赶上陈智还在疯癫的状态,他要从窗户上跳下去,我还拉他一把呢!后来,我的父亲和陈父一起来的时候,还听见我所说的那句话,‘陈智,不要跳下去,我来拉你了’。试问,我如果当时真的想蓄谋害他,又怎么会去救他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我所说的话,就是这么多了。还望县老明鉴。”
县太爷听完这些话,用手拖着自己的下巴,思考了半天,说道:“嗯,你说的也确实有理。”说完这句话,他向陈父双手一摊,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说道:“这个案子到了现在,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还有其他什么确凿的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