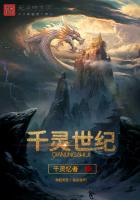恒城突然变得太冷了。
因为早上变天,急着出门的我争分夺秒地从衣橱里翻出冬天的厚实棉衣,却苦恼地发现衣服上有发霉和尘土的味道,并无法穿出门,不由得后悔没有在周末干洗一下。
无法可想,只能在风衣里套了一个针织开衫,结果本来就没有太多富余的袖子变得紧绷绷,像机器人一样锁上家门冲向公交车站。
幸亏我跑得快,还是照常赶上了七点半的一趟76路,车上并没有肉眼可见的空座,而站着的人也不多。我艰难地伸出被衣服束缚的右手去抓吊环,司机大爷就跟瞅准了我的动作一样配合地来了个急拐弯,我惊呼着往一旁摔去。
当然没有人伸出手抱住我,虽然到医院时没有迟到,但我还是未能参加交班,进病房后第一件事就是皱着眉头在护士站拿碘伏棉球给手掌上的擦伤消毒。擦伤不算严重,我也不在乎是否会留疤什么的,对于一个手术科室的小大夫来说没有伤到筋骨就是万幸。
最后一台手术不算顺利,患者糖尿病多年,玻切过程中眼底出血不止,无奈之下主任又上了激光,脱掉手术衣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手术室无门无窗,与世隔绝,走出医院大门我才发现天黑了,车流高峰,我退出了手机上久久无人接单的打车软件,叹着气走向公交站。
如果能修地铁就好了。出手术室的时候因为戴了一天帽子,所有头发都紧紧贴在头皮上,形状扭曲,实在羞于见人,于是我洗了澡。现在站在冷风里一吹,头发湿漉漉的,太阳穴隐隐约约感觉发胀。可是这风衣又没有帽子,我又后悔昨晚没有早点看天气预报找出棉衣。
正在站台瑟瑟发抖,我被拍了拍肩膀。回过头时先看到的是柔软的米黄色毛衣,向上是一张温柔注视着我的脸。
这是我的男朋友韦伊人,我在他充满爱意的眼神中腾地红了脸,不顾头发半干,扎进了他怀里,紧紧抱着他:“你怎么会来接我嗷?”
他用力地回抱着我,把手里的绒线帽子盖在我头上:“是啊,抓到你不吹干头发满地乱跑。”
我仰起头:“我错了,好冷啊,可以帮我暖暖手吗?”
他略松开了我,把我的双手捂进他的掌心,牵着我往前走。伊人的别克停的不远,拐过弯就在超市门前,他先拉着我坐进后座,被暖风包围的感觉真的太惬意了。看着从后备箱里拿出吹风机和毛巾,接在电盒上。我瞪大了眼睛:“这是你刚刚改装的吗?”伊人斜眼看我,我被他露出一丝丝邪气的笑容弄的心跳加速。乖乖地接受伊人边轻轻擦拭边轻柔地吹着我的头发。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我自己来吧,你开车?我们迟到挺久了。”
他不说话,只是低下头亲了亲我。
暴击!直到他把我弄干,我都没能再说出一句话,甚至想再弄湿头发吹一小时。到饭店的时候我脚下走路还在打飘,跟着伊人走进了包厢。
黄昭正在和服务生交代着菜谱,抬头看到我,只点了点头。杨拉登正在角落里蹲着给手机充电,一见到我们进门,眼睛一亮就冲了过来。我发誓我看到她背后是只大哈士奇的残影。
“羽安姐,听说现在学医要规陪?”杨拉登现在成熟了一些,见到人会寒暄了,不过她开口就提起了我刚刚忘记几分钟的头疼大事。
“哎,羽安姐,怎么还愁眉苦脸的!这是好事儿啊!你完全可以出国啊!”拉登寒暄的时候就完全不会察言观色,我恐怕去她会和刚刚离婚的刘缘信说“你老婆做的曲奇真好吃啊哈哈哈哈哈哈”只能板着一张脸继续和她聊。
韦伊人揉揉我头发,在我身边坐下,我一反常态地作出了虐狗的决定,往后一靠,韦伊人用胸膛牢牢接住了我,并且双手拢在我的身前,做出一个暧昧的保护性的姿态。
拉登跟没看到韦伊人一样,面不改色,我随意接口道:“出国?去哪里?”
拉登表现如此的正常,仿佛我身后没有韦伊人,就跟韦伊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世上从来没有韦伊人这个人一样:“德日法意,随你挑啊!”
其实这样斜着秀恩爱什么的我很不舒服,何况拉登这条单身狗也没被虐到,可是也不能立刻无情地甩开韦伊人,就只能就着这个难受的姿势聊下去,老腰酸痛:“那样的话语言不通啊。”
拉登一拍大腿:“嗨,当我没文化呢羽安姐,你们专业不都是通用英文吗?”
我说:“那生活用语呢?”
拉登两手一摊:“用肢体语言啊!”
我:......对面的杨拉登刀枪不入,让我感到很挫败。
韦伊人一定清楚我的心思,因为他忍笑忍到颤抖。我恼羞成怒:“别抖腿!”
这时候刘缘信从外头才进来,看见我和韦伊人,呆愣了半晌,突然掩面而泣。
这就是有意虐狗狗不哭,玻璃心的刘缘信又受到了刺激,直到上了汤才恢复战斗力。
但是到那时战场已经被我们打扫得差不多了,刘缘信一看只剩餐包,哆嗦着嘴唇又想哭,不过大家都面不改色毫无愧疚——我们不会为了任何掉队的战友停留。
看到刘缘信如此挫败我不是不心酸,他的前妻是我的高中同学,从小到大都是女神,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那种。大学毕业后,多年不联系的两人突然闪婚,并没有新娘怀孕之类的传闻。那时候刘缘信毕业后穷的叮当响,婚礼办得还不如乡村爱情故事体面,黄昭更是因仪式过于寒酸并没有参加,一众发小只有我去了。两人在司仪的吆喝声中交换戒指时,他媳妇看他的眼神,明明是有爱的。但现在看来也许只是一时迷恋于刘缘信的光鲜皮囊。
刘缘信进门后被我和韦伊人刺激了一把,但仍然很有风度地垂头丧气打招呼:“羽安,韦伊人来了啊。”我坐直了,和韦伊人稍稍拉开一点距离,可手还牵在一起。我说:“今天手术,来晚了些,一会我先喝一杯赔罪。”
刘缘信大度地摆摆手:“免了。”杨拉登眯缝着眼:“免个屁啊,羽安姐又不喝酒,她喝杯果粒橙赔罪你还不让吗?”
刘缘信下巴上胡茬泛青,但脸还是帅的,带着种颓废的美感,他懒得跟杨拉登再拌嘴,倒在沙发上眼神就开始发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