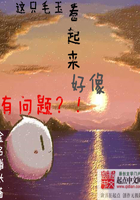“有事快说,我可没时间搭理你。”
“跟我摆架子是吧?那好,你有本事就找别人说。”
“这就生气了?我没骗你,今天医院真的人多。”
“和你有关系吗?人家内科外科的大夫忙也就算了,你一个精神科的心理医生,难道他们都排队找你看神经病啊?”
医院的走廊里,她盯着前一个病人走出去,慌慌张张进了精神科。毕竟看的是神经病,多多少少总会有些紧张。
“行,我错了,你快告诉我什么事啊?”
“没什么大事,就是下个月,校友想聚聚,大多数都是我们认识的,你也可以说,我们比较熟悉的,都在邀请名单上,而且……”
眼前的人坐在了她本该存在的病人座位上,双方的眼神都充满了震惊,只不过医生是惊吓,病人是惊喜,然而迟迟没有什么言语。电话的另一边还在继续诉说着他的事:“而且因为我是留校的老师,所以……他们都说让我去请。你说我该怎么办?……喂,你在听吗?”
“我还在上班呢!一会儿打给你。”不假思索的挂断,那边的人只能不爽地给了个白眼。医生拿出一份病历单:“上面有些内容需要你自己写,请。”
你相信命吗?反正我是信了,就像我今天能够遇见故人,这就是命。
我亲眼看见她把病历单填完还给我,始终保持着作为医生仅剩的一点职业素养对她微笑,我相信她知道此刻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蒋小姐,请问,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哦,我是指,你会经常胡思乱想,或者是晚上做什么很奇怪的梦,又或者在不经大脑思考的情况下就会有什么诡异的行为,有吗?”
“你还会想知道和我有关的事吗?……君然。”她那种自嘲的语气让我觉得有些陌生,不纯粹,可我知道那很真实。
不过她还是叫出了我的名字,不是我对她的暗示没有用,而是她真的逃不开过去,否则也不会想看心理医生,所以我还是选择相信她。
“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请你尊重我,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我不会把公事和私事混为一谈,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现在还肯坐在这里,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我是谁,也是因为我相信,蒋小姐是在不知道我在这里工作的情况下才会来找我看病的。退一步讲,不管我们的私交有多深,但是在这里,蒋小姐也应该把我当多陌生人,这样有利于我的诊断,有利于你的治疗。”
说完这段话,连我都觉得自己很有耐心,至少我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好,顾医生,我愿意配合你。你说的这些我都有过,而且,我经常会不安,会害怕……”
“害怕什么?”我紧盯着她的眼睛,那感觉就像是隔了一个世纪。
“害怕有人会恨我,害怕过去的回忆,如果可以回到一开始,我一定不会像以前一样去选择。”
“所以你的病因是,你在后悔你以前做过的事,能不能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以你的角度,包括细节,还有你当时的想法。”
其实,我才应该是她以前的罪孽,可是我不认她,也不恨她。因为我才是那个不称职的人,无论是作为儿子,作为哥哥,作为朋友,作为恋人,甚至作为医生,我都对不起自己的角色。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可以做别人局里的旁观者,却做不了她的局外人。她讲的故事我听过,同一个故事,无数个人给我讲过无数个版本,因为他们的压力,是我唯一能帮忙化解的事。
也许有一天,即使我无法以自己的角度,也应该结合所有人的想法,去对另一个心理医生,说起自己的故事。
此刻坐在我面前的女人叫蒋艾琳,她是我的前任,却不是那个故事里的女主角,只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我所处于的位置和她差不多,都是那种半核心的人物,只不过她的存在感比我更强烈。之前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姓阮,阮明澈,他才是男主角,存在感比我还薄弱的男一号,倒真是难为他了。据说当时挂断电话以后,他回了我们几个朋友合开的婉约咖啡厅,重点在于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而我和蒋艾琳,也在谈话过程中收到了写给我们的两张明信片,当然,一定不只是我们三个,可是内容却都一样:多年前有你们陪伴我度过危难,多年后我一定会做出让你们感叹的结果。开头是每个人的名字,署名却是空的,只有一个落款:海的问候。至于这些话的语气,也只有写的人最清楚了。
那个人并不是所谓的“海”,而是为海正名的人,内容也不难理解: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艾琳一定也猜到了,否则她也不会用颤抖的手释放出她的紧张。我还是心平气和地用医生的方式告诉她:“我想我们今天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你需要冷静一下,如果只是一张明信片就会把你吓成这样,那说明你的心结还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所以治疗也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今天,就不急在一时了。对了,她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一段真相,大不了给她就是了,我会尽力去劝她的,你不用太害怕。”她的眼神近乎绝望地看着我,想要试着缓和情绪,可是在我面前,她还是在尽量掩饰真实的自己,否则也不会急着拎起包落荒而逃。
关门的声音令我寒噤,艾琳给我讲的并不是那个故事的开头,因为那个开头出现的时候,我和她都不在,可是明澈还清清楚楚的记得一切,他对我说过:他想回去,回到过去。我又何尝不是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