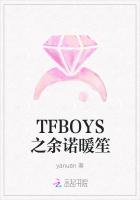作为一个农耕民族的后代,我见到土地就觉得亲切,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自己开块地种点什么东西,否则心里就难过。这种与土地的情节和在耶鲁开地种菜的大叔大婶一样,并不是什么使人羞耻的事情,相反我为此感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然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我如此固执地在每个夏季都要找个地种上几颗西瓜的行为。
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为自己的某些想法感到悲哀。我的父亲榨干了两只眼睛的期望,终日劳作,资我学业,期望也不苛刻,只是希望我走出农村,离开土地。而我偏偏没有因为农村的艰苦而对之滋生厌恶,相反却滋养了一颗陶渊明式的心,无甚大追求,希望得到的只是农妇一个,山泉一眼,薄田几亩,仅此便以足够。
某天,当我把这个想法和他说的时候,他喘着粗气,气得眼睛发蓝,问我是不是想去见马克思。其实那时想法已经够好了,他要是知道我现在在这所男生出双入对你侬我侬的大学呆久之后连农妇都快不想要了的想法,他估计得直接仰躺在地,泪流满面,手指抽搐,蹬脚归西。当然为了他的生命安全考虑,有些事情我还不能和他说。
种瓜的的习惯完全出于怀念。我永远无法忘记八岁那年夏天,我哥哥带着我走了五公里到县里去,闲逛了一天,然后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西瓜,比我三个头还大的那么一个西瓜。在回来的路上吃完后,两个人就把西瓜子埋在路边的土里,说,明年我们再来,它就结西瓜了,到时候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两个少年想着这便笑得合不拢嘴,那种快乐以后就很少再有了。当然,第二年的瓜最终没有吃上。我记得那年我和他吵了一架。那是一个美丽而忧郁的黄昏,我拿着几块黑得发光的煤炭团,瞄着他家里丢去,百发百中,全落碗里,可怜他做好的饭菜因此遭殃。他气我不过,拿着敲石头的大锤,追着我就来打,我跑进自家屋子,反锁屋门,图谋自保。哥哥气急败坏手起锤落,几下就把我家的屋门砸得稀巴烂。我们很生气,后果就很严重了。冷战开始,不相往来。
之后,我想起那西瓜,又厚着脸皮去找他,说我们去吃去年种下的瓜吧。出乎我的意料,他高兴地答应了,也许他也早就想和好了,只是不好意思说而以,幸亏我脸皮厚。最后,那瓜和小猫种鱼一样,没有出苗,吃瓜的愿望也就永久地飘在天上了。
然后呢,我就成了每年都要种瓜的大爷了。虽然每年种瓜都和当年一样,吃不上,但是还是坚持种着,毕竟这世上也并不是所有的瓜都会结果,很多事情心甘情愿,习惯了,就习惯了。
我应该知道,我照顾瓜苗的时候,好像在想念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