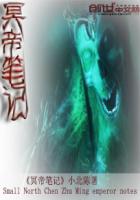死士营名数鹰扬卫编制,实则因死士营成员复杂性,一直以来被排除在鹰扬卫之外,单独设为一营,游离在编制外。鹰扬卫驻扎在刚被调防至潍城东南角,单独设立大营,而死士营便依附在鹰扬卫大营外。这是几个月以来的规矩。
倒也是因为距离不算远,死士营还受鹰扬卫的监管,几日来,死士营每天都会响起嘹亮的号子声,还伴随着北宫伯玉独特的、喋喋不休的骂人俚语。死士营奇怪的动作自然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但这种注意更多的时候是看热闹,就像看戏班子演戏一样。
被张曼成问及死士营的现状,亲卫也难以理解,断断续续的说道:“死士营的那些人……每天都在做奇怪的事儿,要么就是站得整齐伸脚,伸不对就挨揍,要么……”,亲卫用双臂作者上下撑起的动作,道:“要么就做这个,趴在地上做……想趴在娘们儿身上做那事儿似的。”
张曼成扭着眉毛,略一点头,大步流星的朝着死士营那边走去。栅栏相隔,他也能看得清楚。正如亲卫所言,死士营的人都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还有几个从外边股用来的木工给营地安置木头桩子,也不知道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杨伯长?靠山王世子!北宫伯玉?不!萧伯玉啊!单论身份而言,不说前者,只说后者,张曼成就知道自己这个鹰扬将军完全不够看,不为别的,因为人家是三朝或者说四朝天子的身边人,大太监萧无道的继孙,那老太监自身修为就强悍的很,更别提这些年受过他恩惠的人有多少了。
揉着眉心,张曼成暗暗摇头,心道:罢罢罢!爱咋折腾咋折腾吧!别出事儿、别闹出乱子就好。转念间,他又苦涩的摇头失笑:自己还真是自己找麻烦,明知道这两位爷身份不一般,还偏偏不去挑破,将烫手山芋麻利的扔掉给别人……
“淅沥沥……”
滴滴答答的雨静静的落在连日烈阳高照蒸的萎靡的叶子上,错落有致。天是灰的,却不阴霾,即使觉得似乎暗沉沉的,却又令人神清气爽。新年来的第一场雨,如此迫不及待的降落在交州的大地上,却也使人心头的烦躁慢慢的沉寂下来、平静下来。
“下雨啦!”,杨文仰面朝天,忍不住伸出舌头接雨水来喝,一双秀气的眸子眯成条缝儿。好久,他低下头,望了眼在雨水中一动不敢动的死士营士卒们,道:“洗个澡,挺好的,免得一身臭汗。黑头,出列!带几个人去买些酒肉回来,今儿给你们放半日假。”
“喏!”
黑头从队伍中走出来,接过杨文手里的银子,带上两个人一路小跑儿去。而其他人,依旧在雨中伫立,有如不会动的石像。哪怕听到杨文交代下午可以休息,这些人也不敢有丝毫高兴的表情,将近十日来的接触中,谁不知道眼前这两个少年是属狗脸的,说翻就翻?
北宫伯玉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偏着脑袋说道:“还别说,真有效果!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的懂得令则行、禁则止,再过些时日,或许就可以试试演练荆棘绞杀阵了。哎!愣什么身儿呢?你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哪来的?说说呗?我咋就没这脑子呢!”
杨文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接着叹了口气,蹙起眉头小声地说道:“时间紧迫,荆棘绞杀阵明日就要开始演练,日夜演练!只要不把人练死,那就狠狠的操练!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多了,你没感觉潍城这几日来有些情况不对吗?”
北宫伯玉眨了眨那双无神的死鱼眼,稍一思虑,讶然道:“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不说鹰扬卫,好像整个左右翊卫都进入了整军备战的状态,总督大将军昨日还亲自视察了番城防。你的意思是说……南蛮那群怪物又要来了?”
“嗯!我就是这个意思,南蛮又要来了。不止如此,你看没看到城北的百姓已经开始被强行的迁出潍城,去交州内地?再过几日,只怕潍城所有的百姓都会被送走,”,杨文脸上多有思虑,严肃的说道:“年前的那场大战,南蛮来了十余万人,也没见潍城这边如此紧张,这次……只怕不简单。否则,何以坚壁清野?”
北宫伯玉沉默下来,神情闪烁不停,他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人,对南疆战事的了解要多过于杨文。杨文的话他听懂了,坚壁清野是苦战、恶战的代名词,强行迁走潍城百姓,那更是说已经做好了城破的准备。左右翊卫兵团做好了如此准备,代表什么?贼势甚大啊!
总督大将军府。
帝国素来有“南总督”、“北君候”、“东文成”、“西靠山”之说。说的是帝国四大名将,真正意义上的名将,不是勇将、不是猛将、不是战将,是名将!“南总督”为总督大将军,总督的是帝国南疆战事,将军乃车骑大将军,是武官中仅次于虚名的大将军之位,与骠骑大将军同列的存在,二品,比三公。
总督大将军府本姓尉迟,祖上是那位“双锏打出唐天下、单鞭撑住李乾坤”的后者尉迟敬德。不过,这位总督大将军尉迟武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祖上还要厉害。时至“朝凤”元年,他作为左右翊卫大帅,全面主持南疆战事都有十年之久了,大小数千战,不说每战必胜,但也最起码保证了八成的胜率。以南疆如此频繁的战事而言,从有了交州后,还从未有任何一位主将可以像他这样出色,包括开辟了交州的杀神白起。因而,也有人赞叹他为“南天一柱,国之基石”。
尉迟武穆已不再年轻,他更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乡野老人,脸上是条条沟壑,身材瘦削且佝偻,好像是被重物压弯的一样。他的一只眼睛是瞎的,另外一只眼睛却总挂着不干净的眼屎,干瘪的嘴没有几颗牙齿,吃饭也只能喝些粥食。
中午时分,尉迟武穆正在吃午饭,一碗平淡无味的白米粥,一颗鲜鸭蛋,一叠小咸菜,再无其他。他时常笑着怀念,自己当年是庶子出身,还是个私生子,日子过得辛苦,刚刚参军的时候,背囊里放着那几颗母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咸鸭蛋不舍得吃,等到终于狠下心来时,已经臭了……
将蛋皮中的咸鸭蛋用筷子一点不剩的挖了干净,尉迟武穆手很稳的放下了筷子,擦了擦嘴,站起身走向窗口,望着外边的风风雨雨,声音干涩的说道:“李州牧身体可还好?我记得……他年纪好像也不小了吧?六十五?六十八?我有些记不清了。”
屋内有个人,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人,无论他站在哪里,仿佛都能融为一体似的。等真正看到这人时,却会让人恍然察觉,感叹好一位渊渟岳峙的先生。那人年约四十许岁,两鬓斑白,面容却丰神如玉,俊朗的很,颌下三寸短须修理的整整齐齐。
恭敬的施礼,那人笑道:“李州牧身体还不错,年底还娶了个小妾。”
“哈哈哈……”
老帅欣慰的大笑不已,接着骂道:“狗东西!风/流/成/性!”
那人莞尔一笑,并不恼怒,哪怕他是荆州牧李缺麾下最受信任的人。他只知晓,眼前这位别说与自家主公交情不菲,就是骂着玩儿的,自己也只能跟着笑,因为,他是这个帝国、乃至整个人族都应该崇敬的人。没有他铜墙铁壁一样的将南蛮封锁在国境线上十年之久,哪有交州乃至整个江南道的繁华昌盛?哪有人族万千子民的合家欢乐?
面色一变,尉迟武穆眉头紧蹙,道:“李皇叔是个明事理的人,所以这次派了你还有最得力的干将帮我,倒是蜀中那位,怨气颇大。唉!南蛮五十万,连久来不喜参与战争的象蛮人、龙蛮人都出动了。寻常的万余人马都接连天地般可怕,更何况是五十倍?交州无险可守,潍城,不容有失!”
那人拱手,肃声道:“大将军镇守边疆数十年,大小数千仗,什么风雨没见过?怎会露了怯?帝国四大名将,其他三位加起来也没您打的仗多啊!值此时局,谁能挽狂澜于既倒?谁能扶大厦于将倾?大将军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尉迟武穆抹了抹眼角,努力的让自己的一只眼睛睁的大一些,盯着那人道:“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决战于潍城,可也?”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答道:“先下手为强!”
尉迟武穆又问:“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我意于潍城东南、西南两地分兵,成策应之势,谁可担此重任?”
那人再次沉默,接着,答道:“五指相连是拳头。”
尉迟武穆再问:“分兵?不分兵?”
那人抿着嘴唇儿,好半天答道:“不分,守有余、进不足。分,险中求胜,一战吞之,从此南蛮无战事!”
尉迟武穆震撼当场,许久,长吐了口浊气,缓缓的躬身作揖:“请先生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