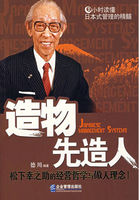午夜时分被雨声惊醒。盛夏的雨总是顷刻而至,大的让你措手不及。空气中浓浓的湿气在扩散,连那盏朦胧的夜灯越发看不清楚了。
桑儿出了一身细密的汗,寝衣浸透,蚀骨的冷顺着凉浸浸的汗象蛇一样一点点地爬了上来,所到之处肌肤上生出细小的麻栗。她用力抓紧盖在身上的锦被,力气大到指节泛白,仍然无济于事,天气并不冷,但她的冰冷似乎是从骨头里蔓延出来的。她知道,她的病根又犯了,当年的寒毒已经深入骨髓,每到雨雪之夜气温骤降就是她最难熬的日子,如同畏寒怕冷的扶桑花一样,她竟然变得只适合南方的气候,桑儿在心里苦苦地笑着:“娘亲,是不是您当年给我取错了名字呵。”
沉重压抑的气息声惊动了睡在纱帐外的十青,小丫头晚上不敢睡得太死,稍有声响就醒了。十青撩起纱帐,见桑儿脸色惨白,头上冷汗淋淋,连忙掌灯叫人,睡在外间的几个小丫头老妈子都起来伺候。桑儿闭着眼睛颤抖着身体,听着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倔强地咬着嘴唇,隐忍着不哼一声。很快窗外杂乱的人声中竟然传来杨政的声音,西厢房的动静立刻惊动殷殷关心的男人。他冷静地吩咐着丫头们取火盆炭火,烧热汤。在低沉醇厚的声音里桑儿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好像不是那么难熬了。
外面的男人久久没有离去,风有些凉,呜呜的吹,窗外树影晃动,大雨倾盆。他一直站在窗外,和她一起静静等待这一波折磨慢慢褪去。
更漏里的细沙一点点的流失,终于寒冷不再难以抵御,桑儿力气耗尽,沉沉睡去。老妈子禀报给王爷。男人如释重负,晨光中有沙沙的脚步声响起,很慢,越来越远。
偌大的宫殿里,漆黑的曜石地板铺就其间,衬托出殿宇的森严和冷漠,皇冠上明闪闪的珠子光亮剔透,带着刺目的光辉,垂在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旁。脸上有老而不昏的眼睛,洞悉一切。
“你说说吧。”皇帝缓缓说道。
杨政站在他身后,他知道几天前发生的驿道兵变,皇上虽然没有处罚任何人,但不可能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委。他低头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叙述给皇上听。皇上面无表情地倾听,心中默默地想:他们已经开始向政儿动手,不能再等了。要尽快扶杨政上来。事情禀告完毕,皇上转头对杨政说:”洛阳郡守方嗣业就要离京返程,你这几天陪同他在京城里看看,尽尽地主之谊。“语气干脆,不容推辞。
杨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没办法拒绝,只得应下来。
窗外阳光温暖,透过窗上的窗纸,洒下斑驳的光影。桑儿经过一夜的煎熬,又足足睡了大半日才醒来,觉得精神好了很多,看来病发和频繁熬夜不无关系。十青进来为桑儿洗漱,桑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昨夜辛苦你们了。”十青从心里喜欢这个坚强又和气的姑娘,笑着说:“姑娘别这么说,看着您那么痛苦,大伙儿心都揪起来了,尤其是王爷,昨晚一直守在外面,天亮才走的,没躺一会儿就上兵部去了。“桑儿没吭声儿,看看外面阳光大好,就同十青一起在院子里闲逛。
王府面积很大,十几个院落重重叠叠,自从桑儿住进内院以来,这里就成了禁地,只允许几个近身的婢女走动。诺大的内宅只有桑儿轮椅滚动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飞鸟叫声回荡。昨晚的雨很大,将树上的花砸落了一地,车痕压过,暗香浮动,偶尔有水滴从宽大厚重的梧桐叶上滚落,在地上积了小小的水坑。
前方一处安静的屋舍引起桑儿的兴趣,她指着那栋屋舍问十青:“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王爷的书房,”十青看了一眼,答道:“王爷不喜欢在兵部里待着,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办公,只有有事商议才会过去。”桑儿点点头。
逛了一个多时辰才回到西厢房,刚走近门廊,就看到许多匠人在忙碌着。桑儿奇道:“他们在干什么?”十青走过去询问,过了一会儿,乐颠颠地跑过来说:“王爷吩咐的,等姑娘睡醒了,才准许他们开工,马上就好了。”说话间匠人们完工收拾好东西,跟桑儿行礼安安静静地退下。十青推着桑儿过去,发现房屋外墙用粘土拌了羊桃藤汁将每一条砖缝都填得密密实实。门框窗缝上包了一层厚厚的牛皮,皮质的一面还涂上了黑色的焦油,也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竟是一点异味也没有。桑儿知道这些都是防潮的措施。回到房中,发现房中间还竖着四丈高的熏笼,三足青铜鎏金,十分华贵,并且有良好的通风管道。熏笼旁边码着整面墙最上等的红罗炭。这种炭是贡物,因为产量少,白霜无烟,难燃难熄,热力持久,尤其珍贵,连宫里的定制也不能保证满足,黑市上的价格令人乍舌,有人甚至用它贿赂官员。整面墙的红罗炭不仅可以用来吸潮也可以用来取暖。
十青欣喜地看着,高兴地说:“这下姑娘再也不用怕冷了。”
这时候外面传来脚步声,十青探头一看,轻快地叫着:“王爷回来了!”杨政一边走进来一边脱下外袍,随手交给十青,眼睛到处审视改造工程的情况,点点头:“嗯,应该会有些效果。”扫视一周,目光落在桑儿身上。女子素颜如雪,黑眸如星,好似婉约的水莲,却又隐隐透着几分英气。
桑儿依旧是淡淡的模样:“王爷何必这么客气,我不过是暂时落脚,过两天就要动身了。”
杨政见她毫不领情,仍是冷淡疏离,沉默了片刻,低声说道:“这段时间雨水多潮气大,你身体不好,总要小心一些才好。”
桑儿轻轻一笑没有说话。杨政挥手让十青下去,停了停,又说:“你一个人在京城太危险了,你要去哪里,可有想好?”桑儿眉梢一挑,直视着他说:“王爷,如果你不打算抓这个乱臣贼子的话,她的行踪何须知道?”
男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后退了两步,转身走了出去。
看着他的身影渐渐隐在层层花树后,她凉凉的在心里一笑:难道不是吗?我们注定是迎面的箭簇,八年前的杀戮,已经拨动了我们的弓弦,开弓难返,不管多久总要碰撞在一起的。
夜晚,大雨滂沱而至,桑儿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没有睡着,应该是白天睡太久了,她想。
窗棂上不知何时出现了男人的身影,背脊挺拔,静静聆听,他终究还是放心不下,不愿打扰她,以至于安静的连十青和其它外间的丫头都不知道。
冷风凄凄,树木婆娑,雨滴形成潺潺水流的夜晚,预期中的寒毒并没有发作,倒有点滴暖意,好似从另一个世界缓缓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