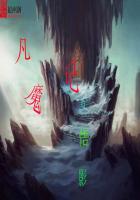轻纱软帐罗。
夜色渐深,里里外外的宫灯已然掌起,照得整个院落明亮一片。
“姑娘,吃饭了。”一个蓝衣侍女挑帘入内,对着床榻上背对着她的女子柔声唤道。
“相爷说,姑娘多日调理不周,身弱体虚,要奴婢好生照应着。”不经意瞥见初染腕上的勒痕,她心中又是一叹。听说,她被绑了整整五日,白嫩的皮肉早被粗糙磨破,梗起几圈青紫和肿胀,更甚,这绳子还被打了死结。她稍稍一动,她便痛得不行,后来,还是用的剪子。
初染昏昏沉沉地闭着眼,长时间的疲惫使得她倦意颇深,头也沉甸甸的,那女子的话更是听得模糊,实在觉得烦了,才哑声道:“我不想吃。”
蓝衣侍女见她开口,心中一喜,于是婉言又劝:“姑娘只当是当心自个儿的身子,多少用一些吧,若是觉得不合胃口,奴婢可以去换。”但这回任凭她好说歹说,初染都没再支声。
复而看了她几眼,见实在没法子,蓝衣侍女也只好转了身。“相......”她刚要开口请安,却被秋慕云一个手势止住,会意地将饭菜端过,她行了一个福礼,便带着众人退下。偌大的屋子,只剩下秋慕云和初染两个。
她半睡半醒,他则是坐在床沿,不说话也没动作。
翻了个身,眼皮开开阖阖间,初染隐约瞥见一角白衫,下意识往上看,却是秋慕云淡笑的脸。“是你。”初染皱眉。
“听说你没吃东西。”
秋慕云驴唇不对马嘴地说了一句,却引来初染一声轻笑:“秋相,何时这样关心我了?”她记得前几日同样的情景,他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怎么唱白脸的是他,唱红脸的还是他?“秋相,您这演的哪一出,我都糊涂了。”
“今时不同往日。”秋慕云端过食盒,取出饭菜和碗筷,“这些都是清淡的,也是你喜欢的。”
“我喜欢的?”初染一听,笑意更深,她费力地支着身子坐起,刚要调侃,却在看到面前的东西时,蓦的愣住:鱼香茄子、水煮鳕鱼、素食豆腐......
看出她的疑惑,秋慕云笑着递过筷子:“在栖梧,经常看到慕容萧让厨子做这些。只是不知,这里比那里如何?”
初染心中一动,果真每样都试了试。
秋慕云在一旁看着,但笑不语,见她吃得差不多,这才问:“怎样,合不合口味?”
初染没有回答,只径自靠在榻上闭起了眼睛,许久,才缓缓开口:“如果没有毒,我想,这里比那里好。”
秋慕云一惊,霎时没有说出话来,摇了摇头,他轻声道:“既然知道,那你还吃?因为自信你可以解么?”
“不是。”初染否认,“我顺从,只是因为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即便现在我不吃,你也会用别的法子,与其让你用强,倒不如还是这样好,至少不难吃。”
看着她平淡无波的脸,秋慕云笑了:“果真是行家。虽然之前就知道瞒不过你,但还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直接。”
“这不是什么独门偏方。”初染撇撇嘴,“比不上秋相神不知鬼不觉的功夫。”
“风姑娘可是在损我?”秋慕云淡笑。
“秋相误会了,这是货真价实的夸奖。”初染道,“能从慕容萧手底下把人带出来,只这一点我便钦佩不已了。”他究竟怎么做到的,刚才她躺着想了半天还是存有疑虑。那**遭人偷袭,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醒来,就已在秋慕云的马车上了。若仅是如此,以慕容萧的聪明,不可能没有怀疑,为何迟迟也没有动作?怪,真是怪!
“哪里,我不过是运气好,有贵人相助罢了。”秋慕云顺手拿过一个靠枕,塞在初染背后,“另外,我与纳兰煌打了个赌。”
“赌?”
“我说,若他提前一天启程,慕容萧定会疑心,但是我这般做就不会。”秋慕云笑道,“现在看来,是他输了。”
“赌约是什么?”初染问。
“千两黄金。”
“呵呵,千两黄金换一场好戏,的确很值。”初染嗤道,“看来,有钱也是一桩好事。”打从一开始,纳兰煌便知道秋慕云的心思吧,他虽张狂自傲,却也心思缜密,恐怕慕容萧的一举一动,他早了若指掌,否则,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赌约,他才没那个兴趣。
“秋某无意难为风姑娘,只要毓缡退兵,我马上可以给你解药。当然——”秋慕云补充,“我也知道,以姑娘的能耐,要在毒深之前配一副解药并非难事。所以,为防有变,我买断了解毒所需的全部药材。——姑娘深谙药理,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真不愧是秋慕云,滴水不漏,连她最后的退路也通通斩断。初染看着面前的男人,忽的勾起了嘴角:“秋相想得如此周到,还怕万一么?不过,不过谨慎本来就是你的优点。”
闻言,秋慕云没有说话。
“但是有一点,秋相还是失算了。”初染把目光挪向外头,那层层软纱遮了她的视线,让她看不甚分明,“我是个一只脚踩在棺材里的人,而今放进一双,也未尝不可。你说是不是?”说着,她忽的笑了一笑,苍白的脸,恍若昙花初绽。
秋慕云愣了一愣:“风姑娘年纪轻轻,怎么也说些丧气话,人生在世,没有一个不贪心。——只要你不乱来,不会有性命之忧,我说过的话,是算的。”
“是吗?秋相既无意难为我,却又为何对他苦苦相逼?”是因为那个荒诞的皇帝,还是因为,你也和慕容萧一样,放不下手里的权?!
秋慕云看着她,沉默许久方道:“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故事?初染讶然。
“很久以前,一对男女相爱。女人对男人说: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而男人也曾立誓:等我做了皇帝,我便娶你。”不理会初染,秋慕云径自说起来,“后来,男人做了皇帝,皇后却不是她。”
“皇帝的故事么,很俗。”初染皱眉。
“来年,那个女人有孕,生了一个男孩。她以为,皇帝会来看她,所以天天在门口等。”
“那皇帝去了么?”
“没有。”秋慕云摇头,“一次也没有去,就好像,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女人。直到有一年,男孩病了,女人迫不得已跑去找他,在寝宫前冒雨站了半宿。很晚很晚的时候,有个宫女出来传话,说皇帝和她们娘娘忙着呢,哪个孩子没个小毛小病的,少见多怪。”
“后来呢?”初染支着额头,顶住晕眩问道。
“后来女人走了,出宫门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她一定会回来,她要所有人都为此付出代价。”
“嗯......”初染迷迷糊糊应了一声,眼皮止不住往下垂。
秋慕云扶她躺下,为她掖好被褥。“那时候,人们都只当是一个笑话。没有人知道他们母子去了哪里,之后......”
“之后......”初染闭着眼睛喃喃,“她回来了吗......”
“她没回来,但是她的儿子回来了。知道么,这忆晴居的主人,她叫毓晚晴......”看着已然酣睡的女子,秋慕云微微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