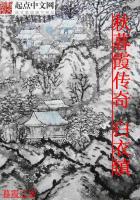说老实话,江湖上对方国珍这种反了降,降了又反的做法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识时务,有人说是朝三暮四,还有人说当初被招安其实就是方国珍使的缓兵之计。
但是,对方国珍的做法李思齐自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方国珍的做法不失为一个枭雄之才,英雄与枭雄虽只一字之差,但行事规则却有天壤之别。
英雄经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枭雄则见事不可为便及早抽身,别说祸及己身,就是池鱼之灾亦是不肯沾染;英雄所为一切都是“义”字当先,而枭雄则是把“利”字放到了前面。
像方国珍这种人,当初造反也是被逼无奈方铤而走险,待到实力壮大起来,他的伙伴们沾沾自喜于辉煌的成就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开始绸缪着下一步,思索着把自己处于何种位置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即使就在他与朵儿只班开战前,他就想好了将要进行的每一步。
甚至李思齐都能预感到,方国珍这种反复无常的把戏绝不会只玩儿这一次,在足够的利益面前,方国珍之类是不会在乎立场的。
出乎李思齐意料的是他与方国珍仅见过一面,可看方国珍现在热切得稍显过分的表现,几可令人感觉到他们二人乃是经历了前世今生的有缘人。
面对着方国珍的热情,李思齐很快地越过了开始的不适,很配合地堆上了满脸的笑意,双手一拱:“谷珍兄,别来无恙啊,上次一别,可真真想煞愚弟了。”
二人哈哈大笑着,把臂而行,一同迈进了那同样笑口大开的乌漆大门。
来至客厅,二人分宾主落座,在方国珍的另一边也就是李思齐的对面,还坐下了三个汉子,方国瑛也在其中,看年龄相貌,李思齐便知道这就是“方家五虎”了,而那三人只有一人看起来要比方国珍年龄大一些,只不过不知是方国珍的大哥还是二哥。
果然,方国珍为李思齐介绍他的几位兄弟,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是他的二哥方国璋,最末首那个也就二十来岁却英气逼人的就是方国珍最小的弟弟方国珉。
几人见完礼,李思齐问道:“谷珍兄,为何不见大兄当面?”
“唉!”方国珍见提起老大方国馨,不由重重打了个唉声:“我大兄当初与那温家争斗,被温家老大打成重伤,虽几经辗转求得名医,但也只是捡回一条命而已,落下了一身的隐疾,根本无法长途跋涉,所以大兄一直就是为我们留守家中。”
见提到温家时李思齐的目光转向自己,老四方国瑛朗声接口道:“方才李大哥见我欺负温家叔侄,切不可误以为我方老四是那跋扈之人,实是那温家所为令人不齿。”
当下方国瑛又向方国珍说了刚才酒楼中的情形,方国珍看向李思齐:“世贤兄,实不相瞒,愚弟当初扯旗就是因为那温家……”
温家在浙东乃是百十年传承下来的名门望族,几代人的经营,使得温家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江湖上都有了一定的人脉,是以就有了一些嚣张之辈,跋扈之徒,温家老大,也就是温荣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说起来方家与温家地位相差悬殊,本无任何交集,但温老大偏偏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别人哪怕有一丝他所不及,他便如鲠在喉。方家五虎在浙东一带主要的市场基本上集中在中下层,很得人心,温老大看在眼中便有些不忿,总觉得卧榻之侧沉睡着一只猛虎。
于是,温老大很及时地抓住了蔡乱头这个契机,广泛散布谣言,终于惊动官府,在抓捕方家五虎那天,他还自告奋勇地前往协助,而方国馨就在逃亡的路上被温老大打成重伤。
讲述完与温家的纠葛,方国珍朗声笑道:“不过那温老大也没捞着好,咱们啸聚海上的时候,我就带着人把他做了,他还有个儿子在鞑子朝廷做个什么……忠武校尉,屁!也没什么**用,现在更是得乖乖地看着,听咱们摆布。”
听他话中有话,李思齐又联想到酒楼中的一幕,温家虽不是什么名动一方的纯粹的武林世家,可也不可能是一个谁逮到谁都能捏一把的软柿子,怎么对着方家的一个小辈咄咄逼人的气势竟绵软至此,不禁大是好奇,笑问道:“可是那温家有什么痛处攥在谷珍兄手里吗?”
方国珍一拍大腿:“着啊,世贤兄的脑子果是伶俐,兄弟此番二次扯旗,实是出乎那一干人的预料,还没来得及做出防备就被我得手了,那温家的家产和家人都落到我的手里,不过大丈夫行事,罪不及家人,兄弟我对他们可仁义得紧,天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并无半分薄待,怎么样世贤兄,兄弟这一手可还说得过去?”
“谷珍兄大仁大义,愚弟佩服。”李思齐赶忙拱手致意,心下却暗自腹诽:说得好听,在酒楼上分明听到方老四逼着温家叔侄赶快送银子,大概就是一大家子的“生活费”了吧,还罪不及家人,玩儿去吧,这特么跟土匪绑票有什么两样。
心里是这么想的,可脸上还是露出一副钦佩的样子,看得方国珍心中大是得意。
说完温家,李思齐将话头拉了回来:“谷珍兄,现在这个非常时期,贤昆仲还这样招摇于街市之上,若是让官府……”
话未说完,方国珍一摆手:“世贤兄多虑了,这些鞑子可也没看在兄弟的眼里,这不是郭淮西的五十大寿将至,同为武林一脉,说不得要来恭贺一番,讨一杯寿酒喝了。”
李思齐实在是再也没有闲心与这表面粗豪,内心里九曲十八弯的“海贼”兜圈子了,他轻笑一声,看向方国珍:“谷珍兄,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此行恐怕不止是讨杯寿酒那么简单吧?”
见被人识穿老底,方国珍黢黑的老脸难得的“紫”了一下,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嘿嘿,世贤兄快人快语,兄弟也不瞒你了,反正现在江湖上都传遍了。这不,兄弟刚刚起事,千头万绪都落到了一个“钱”字上,就想着借着这杯寿酒,看看能不能在郭淮西这里求告得一些头寸,一缓燃眉之急呀。”
李思齐轻轻点点头:“这倒是谷珍兄的实话,不瞒你说,兄弟也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是郭淮西手里寄存着白莲义军的十万两军饷,可我就纳闷了,这可能吗?旁的咱先不说,就说哪一家有如此雄厚的财力轻易地就将十万两黄金寄存在他人之处?再一个,谁人不是想法让钱生钱,别人不说,就说兄弟我若是有这十万两黄金,早就拿出来设法生息,岂肯让它变成死钱呢?”
听了李思齐的分析,方国珍一下怔住了,他此前********想着能从郭斗南手里挖出来多少,压根没有去想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也可能是他心里想钱想疯了,心底的潜意识本能地就抗拒他去否定这个消息。
想了想,方国珍慢吞吞地道:“空穴来风岂能无因,据说是十几年前周王的军饷,袁州兵败,彭大师便将军饷送到郭淮西哪里寄存。”
李思齐马上接口道:“既然是当初周王留下的军饷,为什么周王的旧部不去讨要,非要弄到现在这个沸沸扬扬的场面?”
“也可能……或许……”方国珍想说也可能周王旧部已死绝了,可他立刻自己就否定了这个想法,想当初周王部下遍布各地,信徒多达数十万,袁州被剿灭的也仅有不到两万人,故此周王旧部现在肯定还有不少存在于世,是啊,为什么他们不去讨要呢?
方国珍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一旁坐着的方家三兄弟一直未插言,见场面有些静默,年龄最小的方国珉略有些腼腆地笑了笑,开口道:“李大哥,三哥,咱们也不必为这些事烦忧,本来咱们也是为了给郭淮西拜寿来的,人到礼到,咱们可也没丢了礼数,至于说军饷,不管有没有,和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三哥,咱们不就是找郭淮西老前辈来求帮告借来了吗,对江湖前辈来说借了是他高义,不借呐也是人家的本分,至于咱们,三哥,咱们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啊。”
闻听此言李思齐立刻将一双眼睛盯向了方国珉,而方国珉依旧是那副略显腼腆的样子,不由心下对方家这个最小的弟弟有了一分新的认识,当即朗声笑道:“哈哈……,谷珍兄,饶是咱们枉称在江湖行走多年,倒不如小弟的见识,是啊,本就是为了祝寿而来,至于别的事,不过是顺手为之,倒也无须太过于纠结了。”
也许是方国珉的话解开了心结,也许是李思齐的夸赞令他很有面子,方国珍的脸上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意,看向李思齐:“是啊,还是小五看得开,倒是我过于纠结了,哈哈……见笑了世贤兄。”接着话风一转,问李思齐:“对了,世贤兄,说了半天你也是去郭淮西那里吗?”
“正是。”李思齐便把要到郭家庄祝寿,在酒楼打尖偶然听说温家叔侄欲对郭家庄不利直到遇到方国瑛之事简略地说了一遍。
听说温家叔侄要对郭家庄不利,方国珍不屑地撇了撇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凭他们叔侄竟敢打郭淮西的主意,真真可笑至极。”
方国瑛接口道:“倒也不可大意,听说温老三在他们家中功夫最是了得,一手暗器防不胜防,要是明里出手尚可,可要是背地里抽冷子给你一下,倒也是麻烦得紧啊。”
听到四弟的话,方国珍点点头:“老四说得对,虽说温老三与他的兄弟们不同,一心向武,对他的兄弟们的做派也不大认同,所以独自一人流连在外,但毕竟是自家人栽在别人手里,想那温老三也是不能坐视,世贤兄,咱们还是赶紧到郭家庄去给郭淮西送个信吧,小心无大错不是。”
李思齐闻言点点头:“好吧,那就等到了郭家庄兄弟再与谷珍兄盘桓。”
几人都是江湖汉子,说动身便立刻起身,收拾停当,早有人将马匹备好,几人翻身上马,一溜烟也似赶赴郭家庄。
虽然李思齐、方国珍等人行动比较迅速,并未耽搁,可就在他们赶到郭家庄的时候,还是慢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