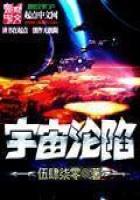听了李静博士的话我似乎懂了一点,那如果球状闪电承载了另外一些东西呢?比如一些巨大的食肉性恐龙,像霸王龙这样的,一旦来到现在这个社会,很难想象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破坏。
“李姐,这球状闪电到底是什么物质组成的?被它烧成灰烬的人还能活过来吗?”
“球状闪电……有很多种!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特性,有的就跟平常的闪电一样,很普通,除了形状不同,其他的物理特性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有一些却完全不一样,它们似乎是有意识的,好像是另一种形态的生物体!这也是它无法参透的原因所在!”
“你听过量子计算机吗?”
“那是什么东西?”
“那只手,就是一个量子水平上的存储器!是可以承载灵魂的!”李静博士指向窗外的闪电。
“灵魂是什么?”
“有人说灵魂是过去一切的记忆,或者说是意识体、大脑的思维电波。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这些念头在大脑里就是一种生物电,神经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温蒂之所以这样,是受到了翼龙生物电的慢性电击!”
“生物电有这么强吗?那我体内的生物电我怎么感受不到呢?”
“之前你握着温蒂的手时,有没有感觉到有人在给你挠痒痒,但是却不知道身体的哪个部位在痒?”李静博士端着咖啡说道。
“是啊,那是怎么回事?挺邪门的!”
“那是灵魂的碰撞!”
“灵魂?”
“奥,我的说法可能不太科学。就用生物电来代替这个让人非议的词语吧。翼龙的生物电刺激了你体内的生物电,相互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碰撞,你会在那么一刻感受到一点点翼龙的记忆,看到一亿多年前的景象,当然这个是很微弱的,一秒之间就忽闪而过,一般你是不会觉察到的。”
“温蒂为什么哭?”
“这个你要问她啦!”
“好啦,现在是不是心里晴朗了不少?不会那么迷惑了吧?”
“我……”
“关于你姐的事情,我的猜测是,球状闪电与她的身体发生了共振,构成她身体的原子全部被球状闪电击散,只剩下一些无机盐,也就是你看到的灰烬!那些击散的原子也可能散落在空中,最后流入了这个物质世界里,也许在你喝的水里就有一个原子,曾经来自你姐的身体!”
此时我正端着一杯水,在昏暗的实验室里,我认真地看着这杯水,它好像有了生命。此刻我的眼睛湿润了,生命原来这样伟大!
“不过……”李静博士又说道,“也可能她的原子体混入了球状闪电里,里面承载着你姐的生命蓝图,说不定以后还会见到她呢!”
我笑了笑,感觉她是在安慰我。
温蒂靠在我的肩膀边,居然睡着了,安静地呼吸着。我看了看她,然后说道:“温蒂也是军人?”
“当然了!她不但是军人,还是杨团长的兵!”
我想起了老兵们说的,能当上杨团长的兵是莫大的荣耀。
“温蒂的母亲是美国人,我们曾经是同学、同事,一起在美国的国家生物实验室工作过,只不过后来……算了,这些让温蒂告诉你吧!”
“我还有一些问题,为什么这里出现了这么多球状闪电,还有这里的地层,怎么会有这么多恐龙的化石呢?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既然球状闪电能够承载恐龙的生命蓝图,那这种闪电又是怎么产生的,它又从何而来?难道真像民间一些老人说的,它们是鬼打的灯?现在我倒觉得它们就是鬼魂!外面那个也许就是恐龙的魂魄!”我指了指窗外。
“它们只是一种奇怪的物质,一种用特别的粒子组成的类似闪电的东西。”李静博士说道,好像还有话要说,但是停了下来,“不要想那么多了,这个世界可理解之处在于它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还是好好生活,到了什么年纪就做该做的事。”李静博士看着我,“小张,该找个女朋友了,今年多大了?”
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的,我的底细她肯定都知道。“二十了。曾经发誓要查出我姐的死因,这件事困扰了我十六年了。可是现在看来,好像已经知道了,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李姐,你能告诉我,我姐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有,我不想要模棱两可的答案,您也不用安慰我,我能挺得住,十六年都过来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呵呵!”她放下手中的咖啡,看着我,眼睛反射着立体影像的蓝色光芒,有一种惊悚的妩媚,又可怕又迷人!“死亡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丢掉了时间这个包袱!小张,你早晚会明白的。”
天不早了,我把温蒂轻轻地抱了起来,放到了那边的床上。刚才我和李静博士的谈话不知道她听到没有,这次被生物电的电击,让温蒂温柔了不少,整个人突然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难道灵魂的碰撞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是一男一女,进行这种生物电的碰撞,那会是什么感觉?
我正准备走,李静博士叫住了我,让我拿出那个蓝冰石给她看一看。我问她这是不是陨石,她笑而不答,端详了好一会儿,才说道:“也许吧。这里的地下埋藏了一块直径很大的陨石,密度很大,有一块地层的重力是倾斜的!”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在地层里水平的走路,居然到最后走出了地表,而且还从很高的悬崖下摔下去,这一切都是因为在那个洞里,重力是倾斜的!我们在地层里爬的第二个洞,并不是水平的,它一定是斜向上的。
由于第二个洞是斜向上的,那里的重力是倾斜的,而且倾斜的角度一定和洞的斜度是一样的,所以我和温蒂在里面走的时候感觉就跟水平的洞没什么区别。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密度的陨石,据我推测,如果画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话,它应该就在直角的顶点处。
可是就算是这样,我们走的路程也不可能这么远啊,我们可是直接闯进了外蒙古,而且还有一条大河横在山的中间。我和温蒂回来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这些又该怎么解释?
我回去睡觉了,跟大鹏讲了一些在地层里的经历,还没讲完,他就呼呼睡着了。夜里,我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花瓣型闪电发射器旁,巨大的发射器此刻像一个从地里冒出来的大手,掌心里正握着一个小太阳。我突然想起一个人,乌兰跑哪去了?昨天我们是一块回来的,之后就不见她的踪影了。
突然有人在外面使劲敲着铁门,我赶紧去开门。开门后一看,一个小姑娘满脸是血,吓得浑身哆嗦,手里拿着马鞭子,但是马却不见了。她正是乌兰,一定是昨晚跑出去的。
“怎么了?你的马呢?”我紧张地问道,然后赶紧关上了铁门。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摸着她的小脸,问她哪里受伤了,怎么流了这么多的血。
乌兰瘫坐在地上,牙齿打颤地说道:“马被吃了!马被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