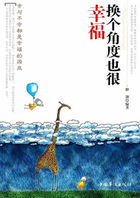活闪婆王定六看牛二终于答应出城了,不由心里一喜,手腕轻轻抖了一下,刀尖稍稍离开了梁光喉间半寸,不想被城下的小黄忠梁鹏瞅得真切,弯弓如满月,一箭如流星,正中活闪婆王定六手中的尖刀。
只听“当啷!”一声,尖刀坠地。活闪婆王定六还想再动,小黄忠梁鹏又是一箭,正中王定六左臂,就这么一眨眼工夫,那些亲卫已经将梁光护住。
“快追,莫让走了贼人牛二!”
梁光脱得身来,紧跨两步,一踩城楼上的机关,只听一声巨响,精铁铸造的千斤闸轰然落下。
此时此刻,牛二刚刚策马驰入城门洞中,正在感怀活闪婆王定六的义气,根本没提防头顶会有千斤闸落下来。
坐在他身后的双尾蝎解宝却看得真切,这千斤闸落下来,就是没砸着牛二,也必将那匹白马拦腰砸断,那样被隔在城内的牛二就只有束手就擒了。
按理说,解宝应当高兴才是,因为这一次建康府之行,宋江的命令就是要他取了牛二之命,可不知为什么,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千钧一发之际,双尾蝎解宝却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只是把手中的莲花铁镋一举,以举火烧天之势顶向了千斤闸。
这个双尾蝎解宝的气力非同小可,纵是比之花和尚鲁智深、打虎武松等人也是不逞多让,要不,根本对不起“腾天倒地、拔树摇山”这八个字的评语。
但那千斤闸何止千斤,解宝只觉得双手好像被撕裂一般疼痛,眼看是顶不住了,幸得那柄莲花铁镋把长,他与牛二运气又好,鹅卵粗细的铁镋卡在千斤闸下面,为白马赢得了一眨眼的功夫。
那匹白马何等神骏,一眨眼的工夫对于它来说已经足够。白驹过隙,又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白驹过隙!
白马驮着牛二与解宝一闪而过,跃出城去。当他二人再回首看时,却见那一柄莲花铁镋已经被千斤闸压得不成样子了。
牛二扭头望了望解宝,就像没有想到素不相识的活闪婆王定六会出手相助那样,他也没有想到解宝会出手相救。
从最初的设计陷害到此时的舍命相救,谁也不知道这个外表豪爽的年轻人,为何发生了如此巨变?
却说城楼上,梁光的亲卫一个个紧握器械,一步步向活闪婆王定六逼了过来。
王定六右臂中了小黄忠梁鹏一箭,已无再战之力,他情知自己如果落在梁光手里,定要受那厮羞辱,生不如死,便把心一横,一纵身,从垛口处跳了下来。
建康府乃是军事重镇,城墙少说也有五米多高,活闪婆王定六虽说身轻如燕,但是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不被摔成肉饼就已经是幸运了。
这个时候,牛二和解宝二人刚刚出了城门,还没来得及抬头看。
而先出城的浪里白条张顺却是看得明明白白,情急之下,忙将渔网抛出,正好把王定六兜在网里,然后用尽吃奶的力气往后猛地一拉。
幸亏王定六瘦小,张顺又是打惯了鱼的,一网下去百十斤重的鱼还是难不倒他的。
但那王定六下坠速度极快,连带着张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两个人一个在网里,一个在网外,都是标准的屁股朝下平沙落雁式。
牛二大惊失色,急忙飞身下马去救,这时,城上垛口处已经探出两三个脑袋来,两三张硬弓已经搭上了雕翎箭,拉得半开。
城下的双尾蝎解宝觑得真切,拿起弓来,连射了三箭,正中那三个弓手的咽喉。
众官兵知道厉害,统统把头缩了回去,任凭梁光如何叫骂,并无人再敢偷施冷箭。
却说牛二扶起了张顺与王定六二人,上下一打量,幸好并无大碍,便在解宝的掩护下,往扬子江边而去。
等梁光让人升起了千斤闸,督促小黄忠梁鹏纠集人马追出城外时,已经不见了牛二等人的身影。
梁鹏也是识趣之人,知道牛二等人厉害,便装模作样地追赶了一阵,在江边捉了几个不相干的渔民,只说是梁山贼寇的奸细,就回城向知府相公复命去了。
而牛二、张顺、解宝、安道全、王定六等人,从芦苇荡里拽出了截江鬼张旺、油里鳅孙五留下的船只,由张顺、解宝摇着撸,早就离得江岸远了。
神医安道全随身带有药箱,看了看活闪婆王定六臂上的箭伤,所幸没伤着骨头,敷了一些药,包扎好了。
“神医安道全,果然名不虚传也!”
牛二见安道全手法熟练,比后世那些外科医师还要强上几分,不由暗地里赞了一句,一抱拳道:“都是小可莽撞,连累了安先生,还望莫要见怪!”
安道全昨夜在西瓦子巷李巧奴的热被窝里睡得正香,不想被不解风情的双尾蝎解宝揪了出来,真是受尽了惊吓,要说心中没有怨气是不可能的。
安道全知道经牛二等人这么一闹,自己则背上了私通贼寇的罪名,只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建康府是回不去了,西瓦子巷也去不了,魂牵梦绕的美人李巧奴更是是见不着了。
但安道全是聪明人,更清楚自己今后的命运将与眼前这个后生紧紧绑在一起了,便笑道:“牛观察说哪里话来?牛观察年纪轻轻便名满天下,能为你效力,着实是老朽的荣幸。”
牛二见安道全甚是知趣,就知道事情好办多了。
当下笑道:“安先生,久闻您医术高明,向有神医之称,不但尽得祖传内科外科之术,而且对解毒也有涉猎,俺在这方面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安道全笑道:“牛观察有话只管问,老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牛二寻思片刻,方才道:“俺以前在开封府时,听说过西夏人常在兵器上用毒,一旦中了毒,面色紫黑,呼吸急促,不久就窒息,必死无疑。不知这是什么**?”
“牛观察莫不是记错了?”安道全满脸惊愕,捋了捋胡须道:“这十有八九是箭毒木,南方蛮人常用,西夏人如何用的这种毒?”
牛二做了数年捕快,不知办了多少案子,游历甚广,自是听说过箭毒木,见安道全一猜击中,不由暗暗佩服,随之又道:“哦,原来是箭毒木,俺原先只是听别人说过,想必是记错了。”
牛二说着,话锋突然一转,道:“对了,俺常见有人被涂了毒的兵器砍中,手脚麻木无力,浑身浮肿,呼吸急促却不至于马上窒息,却容易神志昏迷,安先生可知这是什么毒?”
安道全淡淡一笑道:“这种毒很常见,应该是乌头之毒。”
牛二暗暗一笑,又问道:“俺却不知,那乌头之毒如何涂在兵器上呢?”
安道全道:“牛观察未在军中效力,是以有所不知,从乌头汁中可提炼出膏,叫做射罔膏,军中的弩箭一般凃抹射罔膏,可用甘草解毒。”
“那射罔膏一般从哪里能得到呢?”
安道全慢条斯理地说道:“有些东西是**也是良药,譬如砒霜,就看你怎么用了。射罔膏和乌头一样,是治中风的良药,乌头是煎服,射罔是外凃,一般大的药铺都会有卖。”
说话间,解宝已经在船头温了一大壶酒,端了过来,牛二劈手接过,给安道全斟了满满一杯,“安先生,吃杯水酒,暖暖身子。”
安道全也不客气,与牛二一起连吃了几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