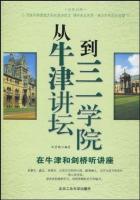为将大量的铀元素拦为己用,普路同的目标不只局限于沙漠,陆地,而转向了海洋。不甘示弱的尼普顿也绝不允许弟弟超过自己,尽管他得到大西洲的大片海域,但还是未能满足他的野心。
双方势力互不相让,他们似乎要进行一场能源争夺的持久战。一方尼普顿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策略,率众进攻敌方的薄弱环节,在其战船的狂轰乱炸之下对方节节败退,其延伸的范围也逐渐缩小。另一方塔那托斯则采取相对措施,他故作逃亡,引君入沟,将对方引入沙漠地带。果以为然他的计划成功了,他深知敌人不适应沙漠作战,诱逼敌人拉长战线,使之深入到自己的腹部,然后再一举歼灭。
尼普顿不计其数的战舰驶上撒哈拉沙漠,海陆两栖式舰艇轻松穿越浩瀚的沙漠,向塔那托斯的领地乌干玛逼近。另外他的空中部队椭圆形的普罗米级飞艇也缓缓逼近敌方的要塞,其艇上装载的飞弹可远距离精确打击地对目标,还可投掷核基弹轰炸敌方范围1000平方公里之内坚固的建筑群。该飞艇大小相当于十来个鲸鱼,其优越的隐身性能,使得它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袭敌方的要塞而不至于被敌人发现,若是空中停满10多艘普罗米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它的武器系统能够瞬间摧毁地面所有的目标,犹如末日审判一般。
他们还有一种称之为开拓者的海陆两栖式的登入舰,它浮起时可以轻松穿越浩瀚无边的海洋和沙漠,装在开拓者号的上的武器系统也堪称一绝,是所有已知种类中最为奇特的,它的武器是高压水枪和海浪式冲击波,一旦喷射即刻穿透十多米厚的钢板,假如打在敌方的小型作战单位上,可将其瞬间击飞。
该登入舰里里外外被一层薄膜保护,尽管只有拇指般厚度的透明粘合物,但千万别小瞧它,必要时它可以吸收敌方激光炮所发出的能量,将其转换成能量供飞船作为动力之用。多余的能量则保存起来,必要时提供给大型的战舰。如此即使战线拉得再长,也不会失去主动权。采集敌方的能源为己用,取之于敌,用之于敌,无往而不胜。
两支大军在距撒哈拉沙漠北面的地中海不期而遇。双方不约而同的相互较量,海岸线上沙尘飞扬,尼普顿一排排小型舰艇快速驶来,在它们强大火力的掩护之下,开拓者号顺顺当当、陆陆续续越过敌方的警戒线,强行登入。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之势向敌人的要塞驶去,雨点般的光束打在开拓者的保护膜上,只会为它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已,不会对它造成任何损坏。塔纳托斯的死亡军团—突击者不停的盲目扫射,惊恐万分。他们不敢相信敌方的登入舰为何能安然无恙,继续前进。难道是自己的武器失灵,又或者是敌方的防护罩太过先进?塔纳托斯作为这次战役的主帅,他焦急的在塔楼指挥舱内飞来飞去,不时地观察远处的作战情况,眼看敌人的大批部队逼进,似乎形势已不容乐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过不了二个时辰,敌方便可以将他的要塞踏为平地。
“我该如何是好呢?”塔纳托斯抽出手中的光剑,敲打着。本来想诱敌深入,现在却弄巧成拙,反而让敌人有机可乘。“为什么我的计划失败了?我该怎样向主人(普路同)交待呀?”
“大人,不好了,尼普顿亲自率大军攻过来了。”说话有点像乌鸦的叫声,塔纳托斯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只见他一巴掌打在那个倒霉的传话筒嘴上,本来挺好看的一个钩形鸟嘴竟然歪成曲状,那个倒霉的家伙伤心的抓着自己的嘴,大哭起来。
他的哭声并未博得主帅的同情,反而激怒了火冒三丈的塔纳托斯,愤怒中的他对准那个倒霉蛋的胸部猛踹一脚,同时抓起光剑向他头部砍下去,顿时鲜血飞溅喷得他满脸都是。面对部下血如泉涌,疯狂的塔纳托斯不但未停手,还继续挥舞着手中的光剑,其嘴里还发出阴森的笑声。一阵舒心过后,他又恢复了原先的状态,诚惶诚恐望着远处的敌人已经来到他的指挥塔下方。
“塔纳托斯,滚出来,你的部下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了,快快受死吧。”尼普顿握着发出蓝色光芒的鱼叉对着塔顶大声喧哗。
塔纳托斯身为死神应该让对手感到恐惧,现在可好完全颠倒过来,他全身上下颤抖着,只因他见到了一生中最忌讳的武器——三叉戟。作为上古五大神器之一它可以召唤水元素供其驱使,三叉戟发出的致命冲击波能够瞬间摧毁一座城市。
“你的末日到了,塔纳托斯,感受死亡的恐惧吧。”尼普顿挑起三叉戟,以极快的速度攀附到塔顶。站在顶处的塔纳托斯往下一看,立马举起光剑正要刺入趴在塔外的尼普顿,不巧被三叉戟挡了回去,随即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掀翻在地,使他半天都爬不起来。他挣扎着口中喷出黑色液体,吃力地挪动着僵硬的四肢,他身体不停地抽蓄着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滋味。过去无数的生命临死前向他求饶,他都会不屑一顾。绝无怜悯之心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同情,他没有感情只有憎恶。每当听到那些家伙奄奄一息,苦苦哀求,那种懦弱、渴望的眼神,只会另他反感。现在他自己面对死亡,是否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手下留情呢?是否觉得自己太过残忍,杀戮太多而最终难逃恶果呢?没有,他大概不知道害怕,致死还摆出临危不乱的架子,大笑起来似乎在嘲笑对手。他的行为和笑声激怒了尼普顿,二话没说就将他的脑袋搬了家。
尼普顿得意洋洋地高举三叉戟上的猎物,对部下炫耀不已,舞动着翅膀,摆动着身后那条长长的尾巴,站在锥形结构的建筑物上,眺望着自己新占的领地。远处海面波涛汹涌,浪花一层高过一层,似乎在预示着一场恶战才刚刚开始。
公元前12000年尼普顿成功击败普路同的死亡军团,全线摧毁乌干玛,奠定了其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
相反,普路同兵败如山倒,其残余势力架船逃亡到塔拉干沙漠的黄金之国,他们打开那里的传送门返回纳托报告。这是他们唯一设置在地球秘密的传输通道,就连狡诈的尼普顿也不为所知。
当普路同的残余势力一回到纳托,其行踪就被星际议会的长老们所察觉,他们暗中调查,大量收集证据,准备弹劾首席执政官普路同。根据星际议会的法律:未经获准不得擅自到外星球开采能源;不得在其他星球私自开发、建造武器;不得破坏原始星球的生态环境,随意采集基因样本,不得无故扰乱和侵害那里的原住居民;不得在其他星球恣意妄为,发动战争,波及那里的任何生物。如有触犯,哪怕是其中一条罪名成立,都要被判处死刑。
受到弹劾的普路同将面临数项罪名,只要有其中一项成立,他未来的春秋大梦就要破灭,而他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兄长尼普顿坐享渔翁之利。凭普路同的性格会这么轻易的将到手的江山拱手相让吗?
当然不会。为挽回自己的声誉和权力,他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哥哥尼普顿,由他来接受审判,承担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站在纳托星际议会的广场中央,又一次慷慨激昂发表着精彩的演说:
“各位,我本不想推托自己所犯下的罪责,我承认在地球发动战争,但那是逼必不得已,原本我为了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成为千古罪人,也不愿拖累他。”
“他是谁?”有人问道。
“当我看到他暴行的时候,痛苦万分。他毫不留情地残害那些比自己更为弱小的生物,肆无忌待地挖掘地球的铀元素(用来制造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器——被列为禁品的核基弹,其放射物会导致使用者受到辐射伤害,而最终毙命),当时我的部下塔纳托斯曾多次好言相劝,都被他一一驳回,最后还招徕杀生之祸。他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恶行,非法霸占了我们的要塞,抢夺当地原住民的资源。出于无奈塔纳托斯在印度洋沿岸和他发生冲突,我们的战士死伤无数,塔纳托斯也在那场战役中不幸牺牲。为了纳托,为了宇宙的和平他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说到这里,普路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故作姿态。
全场的议员被他的言辞所感动,纷纷落泪。他们同情普路同的遭遇,更同情为国捐躯的塔纳托斯,他们憎恨水之星系的尼普顿,不达目的善不罢休。他恣意妄为,竟然不惜牺牲无辜者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后果已严重违反了星际条约,按照星际议会的法律他必须在20天内亲赴纳托的星际法庭接受审判,如到时未参加,纳托则有权派遣军队包围甚至攻打水之星系。不过议会长老们考虑尽量要在不发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逮捕尼普顿,为此他们再三思量最后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阿塔斯的领袖宙斯,由他全全负责此案。
一接到法令,宙斯深感肩负重任,一方面是自己的兄长,一方面是自己的权位,他应该如何选择?何去何从,他的思绪犹如阿塔斯的天空般模糊不清。怎么办?他思绪烦乱在水晶打造的宫殿中,不停地扇动着翅膀飞来复去。不经意中已飞到天台,他伸长脖子抬头仰望天空,雾气沉沉的天色里,周遭的一切令人郁闷压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
“父亲,在想什么呢?”雅典娜飞上天台,眼神透出些许忧伤。
“啊……是你,我的孩子,恩……没什么?”宙斯看着幼小的女儿,断断续续的说道。他说话的声音有点激动,平时一见到女儿,他立刻会上去拥抱她,有时将她搂在怀中,有时将她高高举在头顶,欢呼雀跃。对他来说雅典娜好比他的开心果,只要一见到她,宙斯的心情便会感到无比舒畅。
今**两眼呆呆地看着女儿,半饷只吐出那么一句,不知道该不该说,她幼小的心灵能否承受得住,再过不久她的母亲墨提斯也会深受其害。星际议会已经下了最后通牒,若是找不到尼普顿,必定封锁水之星系,如果那样战争将不可避免的爆发,到那时你的母亲也会迫不得已为国而战,万一那时真的到来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帮谁才好呢?
“去做您认为正确的事,我的父亲。您不是说过我们应该为和平而战吗?哪怕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为了不让更多的人深受其害,该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雅典娜咿呀咿呀地说了一大堆。
宙斯又一次抱起了她,开心地笑了起来,“好啊!小家伙刚才是不是运用心灵感应,否则你怎会知道我的想法呢?”
“对不起,父亲。您曾教导我不能随便运用心灵的力量来窥视他人,可是当我看到父亲这些天来一直茶饭不思,所以不得已……。”
“我没怪你小家伙。你善解人意,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的。”宙斯欣喜若狂,终于他知道应该怎样面对。
多愁善感对某个人来说或许算不上什么缺点,然而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却是非常致命的弱点。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