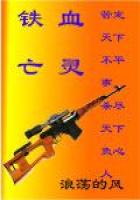确信不能再自欺欺人的时候,叶林选择在电话的另一头保持缄默。无条件的谦卑受教,且毅然保持鼻息如常。他强压抑住满腔自责与愤懑交织的心情,任由它们像火山喷发般在心底反复激荡。他竭力咬紧上唇的剧烈酸痛,已经快要催引出热泪直下。他方今年迈多病的父母,又一次不能免俗地在电话那端,半带哀叹的提到了丢人的字眼。这个简洁的不能再简洁的,虽可以断定是善意的讥讽,却再一次像利刃一般刺穿他震颤多时的心。哪怕是在挂断电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几天,他都久久不能平复这内心的愧疚与惶然。他臆想着是不是该走另外一条幡然悔悟的路,一条改由恶灵支配的肉身去尝试的不再安分守己不再循规蹈矩的,为达目的便可以不惜一切的新路。那迫人心胆犹如囚徒一般的困境,鞭笞着他敏感与犹疑的神经。是否该果断舍弃他一直信守的执念,笃信不已的法国人维克多·雨果的说教--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是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他早已觉悟,繁复迷醉的周折,谓之为现实的生活。一个囿于万千纷扰中的凡夫俗子,又该要怎么有头有脸的过活,这反复拷问着他……
暮秋,大武汉。凌晨一点将近的时候,大汉酒吧内渐渐人影稀疏。迷离的蓝色背景光已经被人逐级调暗,鲁多维科·艾奥迪低沉的钢琴曲《游走》,在几近凝固的空气中一阵阵回旋。角落处几位身着紫红色工装的服务员,面面相觑已经多时了。他们面无表情,打着背手站姿直挺。强忍住如潮水般涌来的哈欠,并尽力睁大着肿胀的眼睛。坚守在果盘操作间门口多时的领班汪伟,低头扫了一眼自己闪亮的黄色皮质腕表,交叉的双臂不紧不慢的从胸前移开。他总算挪动起来了。慢悠悠的走过十余米的弯廊,煞有介事的巡视四周,觉察再无异象后,便给吧台里气定神闲的调酒师叶林使了一个眼色。是的,已没有客人再需要伺候,伙计们终于可以准备打烊了。叶林和其他人一样,立马打起了万分精神,迅疾地做完日盘点并记好了账目。等所有的灯火熄灭,大家一个个换好便装,神情愉悦的聚拢在门口,小声私语着。待殿后的领班拍掌三声示意后,众人簇拥着鱼贯而出。
“哦……好大的风!”第一个走出门的王玲玲,像是遭到什么东西迎头一击,踉跄着急速回身闪避。她披肩的乌黑长发被吹散得群魔乱舞一般,随之发出惊声一呼。这是二零一零年十月的一天,鲜见的寒潮,劲烈的狂风,把亭亭玉立的美人惊吓的花容失色。她顶风强撑着,一只手攥着红色小手包,一只手把米色风衣的领子弹起,顺势将头半缩了进去。
“坐我的车吧?这么大的风,骑车回去太不安全了”,叶林凝视着两米开外,对瞬间冻得瑟瑟发抖的王玲玲说。他觉到唐突,心跳有点轻微的加速。感觉是迸发了很大的勇气才开的口,因为他不确信这是否算一个与其交好的天赐良机。他犹疑着。只是话音刚落,叶林就被身后的一个短发女孩给顶撞了一下。
“嘿,单就送她一个人啊,动机似乎有点不单纯哦。月黑风高孤男寡女,是不是想趁机做坏事啦。那话咋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王玲玲最要好的朋友何丽娜,趁势奚落了起来。一旁的玲玲则像个乖巧的小女生,只是浅笑却不予置评。
叶林机警的瞄了一下四周,发觉同事们都早已走开,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站在酒吧外面的大门口。“好吧,那小生就一不做二不休。你们两个,我打包带走。”叶林手指一晃,颇有点难为情。“两位,这边请。”说完大家相视而笑,一起走向几十米开外的露天停车场。
大风肆意狂掠,吹起地上的细小砂石,击打着停车场里的数十辆汽车。一浪接过一浪的防盗报警器的声音,尖利刺耳。以往早就进入梦乡的夜班保安,这回也像幽灵般悄然离开岗亭。手拿电筒和警棍,一本正经的尾随着他们三个人。叶林警惕地回头瞅了瞅,昏暗的光线让他无法辨别来者的意图。他迅速的掏出钥匙,面色从容的坐进了车里。此刻伫立在车旁的保安,将手电正对着坐满人的车内。白茫茫分外刺眼的强光,像X光机一样匀速扫描了一遍。不出意外的,光线最后聚焦在王玲玲秀丽卓然的脸上。玲玲面露不快,小脸旋即侧向一边。叶林感到难堪至极,他咬牙切齿但直摁着怒火隐忍不发。尽管看不清保安的那张脸,但他可以想见那个不礼貌举动下的眼神,会有多么龌龊不堪。叶林已经怒不可遏,在按响两声喇叭,并朝保安竖了一个击发状的中指后,以烧胎的节奏闪电般驶离。叶林觉得歉疚,他为此直觉得丢脸。深以为钟情的女人遭到羞辱却没有挺身而出,他感到自己不像个有血有肉的大丈夫。他早应该下车,果敢的去和那个猥琐的保安来一场文明人应有的道德理论,抑或谈崩后以拳头论大小之类的贴身肉搏。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这让他焦躁不安。“都消消气哈。那保安,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又像是天蓬大元帅下凡。猪鼻子插大葱,急着装象呢!”何丽娜有意圆起了场子,三人淡然一笑。
叶林所拥有的那台,叫老爷车也不为过。那是两年前他路过一个汽车修理店买的一台二手美国商务车,准确的说那是一辆别人开过六年,又突然发生严重事故急着脱手的问题车。惊悚的一幕,原车主被突如其来的惨象吓得魂飞魄散。车在花了保险赔付两万多修复后,不假思索,便以修车价转手卖给了叶林。
“哥,啥时候换台观感好点的车啊。这车座椅响,窗户响,发动机更响。再加上你这乌鸦**一般的喇叭响,齐活了--“联响(想)”。留着短发的女人,貌似真不是温柔的化身。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坐叶林的车了,但何丽娜每次都想找点新的笑点絮叨一番。也或者她没话找话说,只是想和这个亲切叫着哥的人,多套几句近乎而已。
“我想啊。改天再去路边的修车店碰碰运气,看还有没有出事吓得尿裤子的大款呗。”叶林撇着嘴,回应道。
“哥,做调酒师屈才了您。干脆炒我们老板鱿鱼得了,豁出去自己做。修车铺旁边开家二手店,专收四个轮的破烂。低买高卖,躺着数钱如何?”何丽娜轻轻拍了一下叶林的座椅后背,不依不饶的说。“痴心妄想的阿甘做了接盘侠,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真的傻。这捡来的新欢,照旧是别人扔掉的破鞋。”
“哼,在高速上被两个玩命超载的大货车前呼后拥的强吻,鬼门关前着实的走了一遭,还奇迹般的没死。你回头看看后面追尾的大货车司机,挂在车头被撞的稀烂的驾驶室里,血肉模糊没有一点气息。你自己呢,被卡在车门不能打开的铁盒子里,四肢瘫软动弹不得。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巴巴的只能等着120和119派来的天使救兵,是个人心都要蹦出千百遍了。外面烟雨朦胧,你却没了看风景的心情。不可能想当然的跑车后去放什么危险警示牌了,你满脑子的都在想象着后面还会不会有车接着连环追尾,别人的车和自己的车会不会发生漏油起火甚至……旁边传来阵阵啪啪作响的电火花声音,和那立马就可以闻到的浓重汽油味。说吧,这要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余生又要留下多久的后遗症啊?”叶林开着车,说的神情兼备。“车子筋骨够结实,人才大乱不死的。他一个四十五岁的大男人,堂堂七尺男儿,活大半辈子了。掏心掏肺,毫无顾忌地给我讲完这些。然后把车便宜作价干脆利落的卖给我,这不是什么面子,这是缘份。”
“缘份,那值几个钱。有钱是缘份,没钱是缘分。”何丽娜头耷拉着,故作深沉道。“再说啦,哥,七尺男儿,哪到底有多高啊?”
叶林默不作声,这倒不是无言以对。他想他暂时钟情于调酒师这个昼伏夜出的工作,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的睡眠都极度糟糕。错乱的生物钟,又不愿意借助安眠药的麻醉。早已习惯了在别人沉睡时自己安心工作,在别人投入工作时自己努力沉睡。安于现状不是他的本意,好高骛远更不是他的方向。当然,他没法娓娓道来一般去和别人解释这个,尤其是眼下正在和他言辞交锋的这位。
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不想再继续言语了。透过内后视镜,他瞅望着后排的玲玲,那表情平复安祥。车厢哐哐作响的纷扰,抵不过夜深时分的窘困。她闭目养神,秀发半遮面。亦或者,她本就清醒,只是在假装着没有听见,刚才他自以为是的有意显摆。他越琢磨越有点后悔,开始担心起言多必失了。可很快又转念一想,如果深信沉默是金,别人又如何真正了解他这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