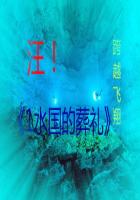前往省城之前,我去了一趟当初火化方天琪的殡仪馆。在那里,我确实查到了方天琪的一些相关资料,可是当时负责这件事情的员工,已经辞职离开了。
打听此人辞职的情况,他同事表现平淡,只说这样的单位人来人往,尤其那种年轻小伙子,凭着一时激情进来,支撑不了多久就逃命似的离开的,其实大有人在,不足为奇。
我问这些年殡仪馆里有没有出现意外,比如送来的遗体未被真正拿去火化,而是贩卖做人体器官的什么的。
或许我这问题问得太白痴吧,他们没有人再理我,各忙各的去了。
不过,这毕竟是个线索,现在只等方岳与方天琪相认,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下手,顺藤摸瓜,将王权贵那老狐狸给揪出来。
可是,那毕竟是一只老狐狸,这点线索真的足够对付得了他吗?
当时刚好放个小长假,我和代苑带着方天琪前往省城。
将她二人安排好以后,已是下午七点多钟。我直接去了方岳的家,那栋熟悉的教师小楼。
敲门以后没有应,我只好去楼下等。大约八点多钟,方岳的车回来了。我正打算走上前去,却见车上下来了一名女子,紧接着,方岳也从车上下来。
两人神态非常亲密,看起来关系很不一般。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莫非,方天琪的母亲回来了?
可是再一细看,那女子长得非常年轻,根本不可能是方天琪不知去向的母亲。两个人下了车以后,就几乎是相拥着走上楼去。
我当时觉得有些尴尬,也就不好意思再上前去与方岳说话,何况这事,有外人毕竟不好开口,只好继续等在楼下。
可是一直等到夜里十点多钟,方家熄了灯,那女子也没有下楼来。没有办法,我只好先回了宾馆。
第二天,我直接去了方岳的学校,想能不能在学校里碰见他,或者哪怕先要一个他的电话号码,也好约他单独见面。
可是在他学校里听到的一个消息,却让我大吃一惊。
打听方岳电话号码时,他学校里一位节假日值班的老同事告诉我,方岳因为之前受了不小的刺激,后来一直生病,有时意识错乱,没办法再继续上课。学校只好给他办了病休的手续,现在一直在家养病。
那老教师问我是方岳什么人,我忙说我是方老师以前的学生。那老师“哦”了一下,然后悄声告诉我,如果要拜见方老师,可以直接去他的家里。
不过他现在由一位他曾经的学生在看护,那学生名叫童珊珊,好像对方岳仰慕已久,整个学院都知道。现在方岳生了病,而她也已经毕业后留校做了辅导员,不再有什么师生顾虑,两个人也就住在了一起。
童珊珊甚至表示,一旦方岳病情减轻,他二人就会举行婚礼,结为真正的夫妻。
老教师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神情间没有露出一丝一毫对于师生相恋的不满和鄙夷,相反却流露出对于这位女学生对自己仰慕对象不离不弃的赞许之情,当然更多的则是对于方岳的同情之意。
这让我心里感到非常惶惑。我犹豫片刻,还是小心翼翼的问道:“方岳老师,他……真的病得很重么?”
那老教师长叹了口气,“起先一直卧床不起,几乎就要半身不遂了。后来好在小童的悉心照料,他现在已经可以下床,虽说行动还有许多不便,但至少不用在床上过小半辈子了……”
我心里一凉,忽然想起前一晚在小楼下,远远的见到两人相拥着上楼的情景。原来当时他们并非浓情蜜意以致难舍难分,而根本就是互相搀扶着走上楼去的。
那老教师又接着说道:“可怜了这老方啊,他腿脚是能走动了,可意识还是糊糊涂涂的,我们去看望他,他竟然谁也认不出。满心满眼的,只有那个一直伺候在他身旁的小童,别的任何人,他都视而不见了……”
老教师的这句话,再次让我心里凉了半截。不止因为方岳的境况,远比自己现象的还要糟糕得多,同时也因为方岳的失忆,让他们父女相认的情况,也变得更加渺茫。如果,方岳真的对自己女儿已经全无印象,而方天琪也对自己父亲全无记忆了,这该怎么办?
作别老教师之后,我心下一片茫然,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方岳与方天琪都丧失了记忆,而在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可怜无辜的童珊珊。如果我将方天琪贸然送还,即使她能接受,那么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要同时承担起两个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这让她怎么扛得住?
如果她承担不了,一走了之,于情于理并不为过。可是这样一来,不仅方天琪无法生活,甚至连方岳也再无人看管,以后这对父女,又该怎么办?
我在省城那些曾经熟悉的大街小巷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如何回去对代苑,尤其是方天琪做出交待。
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我鬼使神差的又走到了方家小楼之下。方岳车子停在下面,房间里亮着灯。
我却无论如何都迈不出脚步走上去。我不知道上去了,我能得到一个什么结果,我能为方天琪争取到什么。
或许我这样贸然的动作,只会打破一个原本已经非常凄凉的小家庭的平静与温暖。此外,别无所得。
然而,就在我左右踌躇着,不知如何进退的时候,我眼前忽然浮现出那年送方天琪回家时,她躲在我身后,显出一副惊慌失措的可怜模样。
那神情让我感到心酸,同时也让我心底一亮。
对了,还有那位方老太太!
方天琪的奶奶,她现在是唯一能认出方天琪的亲人了。
想到这一次,我很快离开了方家小楼,前往方老太太的住所。
虽然我头脑里依然一片混乱,不知道这样一位年迈的老人,面对自己完全失忆的孙女,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同时我也难以想象,如果将此时的方天琪交给方老太太,那该让这样一对祖孙,如何生活下去?
可是,即便方天琪不会留在方老太太处,我依然还是有责任让方老太太知道,她满心牵挂,满心歉疚的孙女,其实还在人世。
我应该仔细琢磨的只是,如何委婉的跟方老太太慢慢的讲述这件事情,不至于忽然之间,惊吓到她老人家。
可是,当我走到方老太太居住的那栋很陈旧的小楼上时,我见到的却是一道紧缩的房门,以及房间里的黑灯瞎火,漆黑一片。
那道紧缩的房门上面,甚至已经落满灰尘,布满蛛丝,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打开过了。
我心里一阵慌乱,所有残存的温度,都在这一刹那间烟消云散。尽管当时已近深夜,我还是发了疯似的,开始猛敲方老太太的房门,同时也发了疯似的开始乱敲左邻右舍的房门。
几个房间里都走出了人,他们吃惊的看着我,问我是什么人,做什么。
我语无伦次的说,我说方老太太孙女的朋友,是方岳老师的朋友,我找方老太太有要紧事。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走过来,神色凝重的告诉我,方老太太早在半年前就去世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早已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答案,可原本就已经并不清晰的头脑,再次变得更加混乱。
我嘴巴里喃喃自语着,“怎么……怎么会这样……”
那老头叹了口气,“年轻人,想开点吧。你看,他儿子方岳就是一时想不开,气得一病不起,差点把小命都给搭上了……”
我茫然的看着那老人,“你是说……你是说方岳老师他……他就是因为自己母亲的去世,受到的打击,才变成了现在这样?”
那老人点点头,同时唉声叹气的道:“其实,何止这一重打击。女儿刚走,老母亲也紧接着就走了,换谁谁都受不了啊!”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年轻时,老婆又莫名其妙的离开了,你说这老方,他到底是……唉!”
老人一面说着,向我摆摆手,自己回家去了。
我愣怔在楼道里,听不清那些邻居都跟我说了些什么,然后一个个走回家去,我却如同陷在一片黑暗之中,无边无际,想伸出手抓住点什么,却最终什么也握不到,只是独自漂浮在一片巨大的虚空之中,漫无边际。
代苑打了无数个电话之后,我终于清醒过来,接通了电话。
代苑在那边语气焦急,“刘宇,你怎么回事啊?电话也不接!你现在在哪?”
我有气无力的问:“方天琪,她没事吧?”
“没事啊,”代苑不快的说道,“你现在到底在干嘛?方岳那边联系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回来再给你讲吧!”说完,我挂了电话。
一个人走出回宾馆的时候,我买了一瓶又一瓶的啤酒,往肚子里灌。
我想起仿佛已是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当我从废园中见过唱戏鬼回来的路上,则在暴风雨中,被藏匿在这座城市钢筋水泥中的各种冤鬼吓得魂不附体;可是这一刻,面对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城市,我却再次被一种事物恐吓到失魂落魄。只是这一次吓到我的,不是鬼事,而是人事。
可知人生在世,可将自己惊吓到魂不附体,压抑到喘息不过来的,又何止上山野之间那些神出鬼没的鬼火幽灵,更多的是这人生原本的无常,它们有时更令人生惧,也更令人绝望,尤其令人无可奈何,只能束手就擒。
我扬起头,目光穿越城市迷离的灯光,穿越那些或厚或薄的云层,任灵魂漂浮在那片寂静的苍穹之上。
那一刻,我很想知道造物使人生于这茫茫天地之间,究竟所为何来?
常言造化弄人,莫非仅仅为了用这一切有如酷刑般的生爱别离,戏弄众生,以求取坐望之快感?
又或者,天地原本无情,而造化原本无物。多情的只是这可笑的芸芸众生,在一场貌似庄严的人间悲剧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绎着一出又一出荒凉的悲剧,恰似那年在废园见到的那一片红红翠翠,五色杂陈的梨园众生。
那天夜里回到宾馆前,我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无论如何,我要让方岳与方天琪见上一面。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亲生父女,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阻止他们见面。
只是,面见方岳之前,我需要先见一个人。那就是目前正在悉心照料着方岳的那位年轻女子,童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