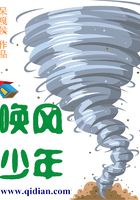有时候我情愿面对一条发疯的狗,也不想应付生活形色的情绪和苍白。
相对于被生活毫无知觉地强奸,我宁可被狗撕下一块肉然后痛嚎。这时我想起小时候遇见的那条沉默的好狗,若非遇到汪卫国和莉莉,不知道之后的我会不会比现在的我少一块肉。
我躺在床上发信息给沈默默说今天真累,大概是真的累了,发完信息之后马上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正好接到徐锦打进来的电话。
“林早宇,我的礼物你拆了吗?”电话里徐锦问我。
“都没有拆,回来之后我就睡了,现在才醒。”我打着哈欠回答。
“啊,不好意思吵醒你了。”徐锦的语气显得有些忙乱。
“没事,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醒了。”我接口说道,同时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六点四十。
“啊,那我就放心了。”电话里头徐锦明显呼了一口气。“那我不耽误你拆礼物了,拜拜。”话音刚落就挂了。
我有些哑然,从没想象过这样风风火火的徐锦。
结束通话后手机上显示着五条未读短信。
沈默默一共发了四封。
生。
日。
快。
乐。
还有一条是张小超发来的,夹在生日与快乐之间:“我们的礼物怎么样,不错吧?”
我忽然想到,拆礼物也算是过生日的一道步骤。
第一个拆开的是徐锦送的精致小盒子,里面装着一件盆栽,我有些意外,浅口白瓷陶盆里铺了沙土,一个洋葱状的鳞茎半没进土里,顶端冒出一片半截手指长的柔嫩小芽,我辨不出是什么品种,用手逗弄了几下,便放在桌上摆着。
张小超和周小碟的礼物是一把木吉他和一首曲子的简谱以及一张便条。简谱是周小碟手抄的,整体看起来十分舒适,便条上是张小超的留言,上面写着:以后学。
在我立志找个姑娘之前,我一直说给张小超听的愿望是学吉他。每次张小超都以悲悯的目光看着我,然后拿起我的手不无惋惜地说道:“手指太短。”
所有的礼物摊在灯光下,有弗兰克尔写的《追寻生命的意义》,有肖像素描画,有林肯公园乐队的专辑唱片,还有中华牌的墨汁……
晚上临睡前我回了沈默默短信:当然。
生日快乐。
当然。
虽然这么说,内心却无法真正认同,总觉得因为少点什么而郁郁寡欢。
对于每一个在校的学生而言,自己的学校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发白的毛边旗帜,擦不净污渍的窗户玻璃,掉灰的泛黄墙壁,杂乱的篮球场,缺一笔画的铁艺校训大字,角落里丛生的野草。
像一座废弃的古堡,没人知道它的故事。
李刚辍学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记忆瞬间回到李刚在所有人面前醉酒大哭的场景,原来那是场别离,李刚和他自己的别离。
辍学这种事情在我就读的学校并不少见,大多数志不在读书或自觉高考无望的学生都会选择结束学业生涯,也有一小部分因为家庭原因辍学。
辍学之后基本有两个选择,读技校和打工。我不知道李刚的选择,正如我不知道他离开并且去了哪里一样。
这时陡然又想起李刚给我的那张纸条,现在还放在兜里,我紧忙拿了出来,上面记着一个号码和一个地址。
我按照上面的数字拨了过去,接通电话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没说几句就挂断了。
我看了看手中的纸条,这算是李刚的礼物么。
突然有些寂寞。
那种感觉就像突然被狗亲了一口之后,失怔地想着为什么不是一个漂亮姑娘而是一条狗。
徐锦的家和我家离得不远,只隔着上次我们走过的那条街,我在街的这头,她家在尽头。
我去找徐锦问她送的盆栽是什么品种。
“等开花就知道了。”她这样说道。
“会开花吗?”我反应过来,有些惊讶。
“不知道。”徐锦语气不明地嘟囔着,“如果开不出来再告诉你。”随即转身回去了,既没有让我留下,也没有让我回去。
回到家里,我愣愣地看着桌子上的盆栽,仿佛要看着它最后长成我认识的模样。后来从老妈那里了解到是风信子,我恍然大悟,虽然没见过风信子,但是不止一次听说过,这个名字很好听,符合我的气质。
老妈问是哪来的,我说是朋友送的。
她嘀咕着不知道最后是什么颜色的花,然后就下楼了。
晚自习上跟沈默默聊天。
“默知道风信子长什么样子吗?”我问沈默默。
“不知道。”
“那你应该养一株看看,简直跟洋葱一样。”
沈默默说她不喜欢洋葱,然后又问开花是什么样子。
我愣住了。
那得等开花了才知道,时间大概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