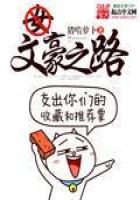第三节、
她不知为什么,今天哭出了声。那多少天来终于压抑不住的悲伤、怨屈、和痛苦,一下子暴发出来。
泪水就象伤口止不住的鲜血那样涌流出来。
她就这样一直哭,一直哭。哭得没有了一点气力,她靠在大石头上,一手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伤腿,一手托着被泪水浸湿的小脸蛋,思念着姥姥,回想以前跟姥姥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姥姥可疼爱她了,白天坐在小马扎上把她揽在怀里,摇晃着身子,嘴里有唠叨不完的话跟她说,有许多故事讲给她听;晚上把她搂在被窝里,有时哼着小曲,象蜜蜂在花丛中缭绕发出的那种声音,如春雨淅沥,悦耳动听;又如潺潺流水注入心田。
她用小手摸着姥姥那松瘪的***柔软温热。她有时候把耳朵贴在姥姥的胸口,聆听从那里发出的均匀而节奏的心声。在这里有她无限的乐趣,这种乐趣就在于,她能从中幻想出极其丰富多采的景象:老人那不厌其烦的唠叨在她听来,却如隐约可闻的春雷,夜半淅沥的露雨。
她记得姥姥去西天之前得了一场大病。是舅舅用拖拉机把她送去医院的。姥姥住院的那一天,小春一个人睡在家里,她好长时间不能入睡,因为她每天习惯了把身子依偎在姥姥的怀里,必须得用小手摸着姥姥的**才能睡得着觉。她好几次在蒙胧中伸出小手去触摸本应是姥姥躺在那里的地方,但那里却冰冷得让她感到恐惧和失望。
一连几天,她想念姥姥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她决定要舅舅带她去看姥姥。但她不敢让舅妈知道,因为舅妈那张脸拉得跟后妈一样即长又可怕。
吃过了早饭,舅舅在院子里摇拖拉机的发动把手。舅舅使出全身的力气,从慢到快,转转转,猛然一提。拖拉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冒出一阵刺鼻的浓烟,嘣嘣嘣嘣地叫起来。
小春悄悄溜到舅舅身边,眼睛瞅着屋里,小声说:“舅舅,带我去看姥姥好吗?我听话,我不给你乱要东西。我能给姥姥端水,倒尿盆……我还能……”
“去吧,回屋多穿上点衣服。”舅舅拍拍本没有什么尘土的大手,喘着粗气说。
“噢——要去看姥姥啦!”高兴得小春忘乎所以了,飞也似地往屋里跑,差点儿一头撞到舅妈的腿上,心想:这下坏了,八成去不了了。她低下头等着挨训。
“疯啦!死妮子。还不快去把你哥的袜子洗出来去!”
小春小声说:“舅妈,我想去看看……”
“哪里也不准去!”
舅舅小心翼翼地说:“咱娘说要见见小春……”
舅妈用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算是恩准了。
小春慢慢转过身子,在避开舅妈的身影以后,象只小燕子一样飞快地跑到自己的床上,扯起一件上衣就跑出来了。
小春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但她却被姥姥那副苍老干瘦的面孔惊呆了。才几天没见到姥姥,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暗淡无光的眼睛深陷下去了许多,脸上象核桃的皮一样皱起纵横交错的沟壑,样子显得即陌生又可怕。在确认了这就是姥姥之后,小春一下子扑到老人的脸旁,眼里落下泪来。
姥姥不断地咳嗽,伸出干枯得象树枝一样的手无力地握住她的小手,眼睛闪动了一下,几滴浑浊的泪水滚了下来。她的薄薄的嘴唇抽搐着、颤抖着,却没有说出话来。
“姥姥。”小春带着哭声叫道。“你怎么病了?为什么还没好?你啥时候回家呀?”
“春儿……”老人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她知道自己患了晚期肺癌,于愈是无望了。但是她并非是为自己的即将归去而伤感。她已经七十多岁了,苦她也吃够了,福她也享足了。使她唯一搁舍不下的是这个没了亲娘的孩子。由于小春从小就生了一头难愈的黄水疮,人人都讨厌她,嫌她窝囊。这使姥姥对她更有一种加倍的爱怜。可是她很难想象在没有姥姥的日子里小春会是个什么样子。
小春没有觉察到姥姥内心的伤感,她发现了高高挂起的吊针瓶子。她隐约记得她曾经也打过这样的吊针,一条长长的细管从吊瓶上通下来,前边一个针头扎进皮肤里。她想起来了,可疼哩。现在她又看见它,心里一阵打怵。
现在姥姥也病了,姥姥又要忍受那种可怕的疼痛了,她心里感到难受。她想安慰姥姥几句,说:“姥姥,打针就会好的,你别怕疼。我以前就打过针的,你不是说过打了针就会好起来的吗?听话就是好孩子。”
姥姥嘴角动了一下,吃力地笑笑,但她觉得她的心却在流血,流泪。
小春又悄悄凑到姥姥耳边小声撒娇地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么,我要你早一点好起来,要你回家……我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姥姥鼻子一酸,她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她现在所能做到的只能是热泪盈眶。她胸中的悲伤使她感到心脏也在疼痛了。天真可爱的孩子,还在对她的回家抱以多么大的企盼呀。然而这种久久的渴望一旦落空,她那幼小的心灵将会承受多大的伤痛呀!
这几天以来,在姥姥脑子里出现的都是小春那无依无靠的孤独身影,都是小春那可怜的小猫一样卷曲在冰冷的被窝里,抽泣着抹着泪水的样子。再也不会有人给她洗头涂药了,夜里再也没有人给她端上尿盆让她不用下床就可以撒尿了。她也许会一头扎下来的,或者一脚踩翻了尿盆摔倒在地的。
“春儿……”姥姥想把那个迟早要来临的不幸告诉给她,至少透露一点使她能感到的预兆,让她有点心理上的准备而不至于使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幸,如雷轰顶般的猛然呈现在她的眼前,使她弱小的心灵承受不住那样重大的打击,但却找不到表达这种预兆的适当的词句。
“什么事,姥姥?你要喝水吗?还是想撒尿?你告诉我,我什么都会做的。”
她拿好了架子,只等一声吩咐了。她那眨着的一对有神的眼睛里,闪出在她这种年龄里却是令人辛酸的过早成熟。这使姥姥更感到一种撕心裂肺般的伤痛。